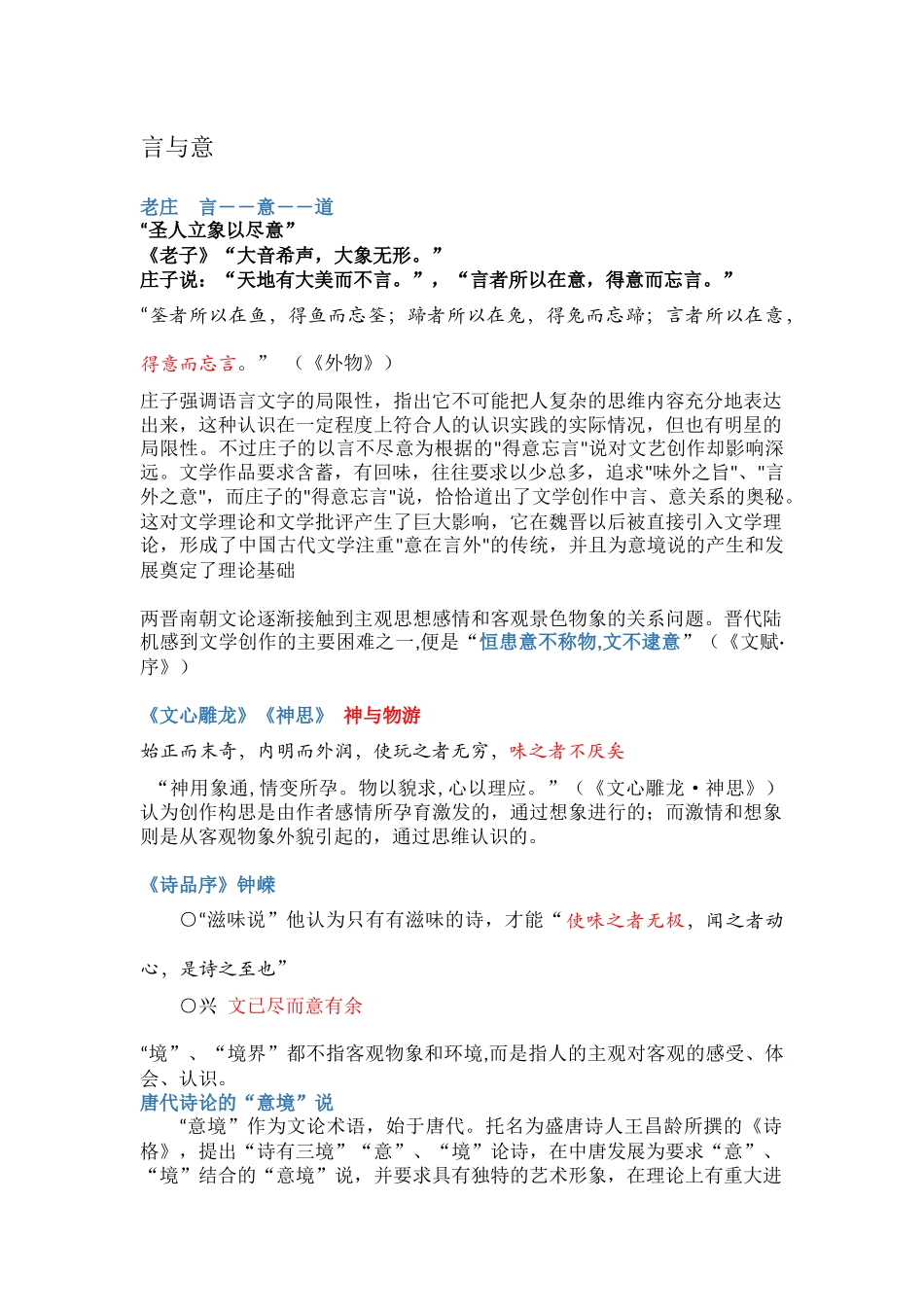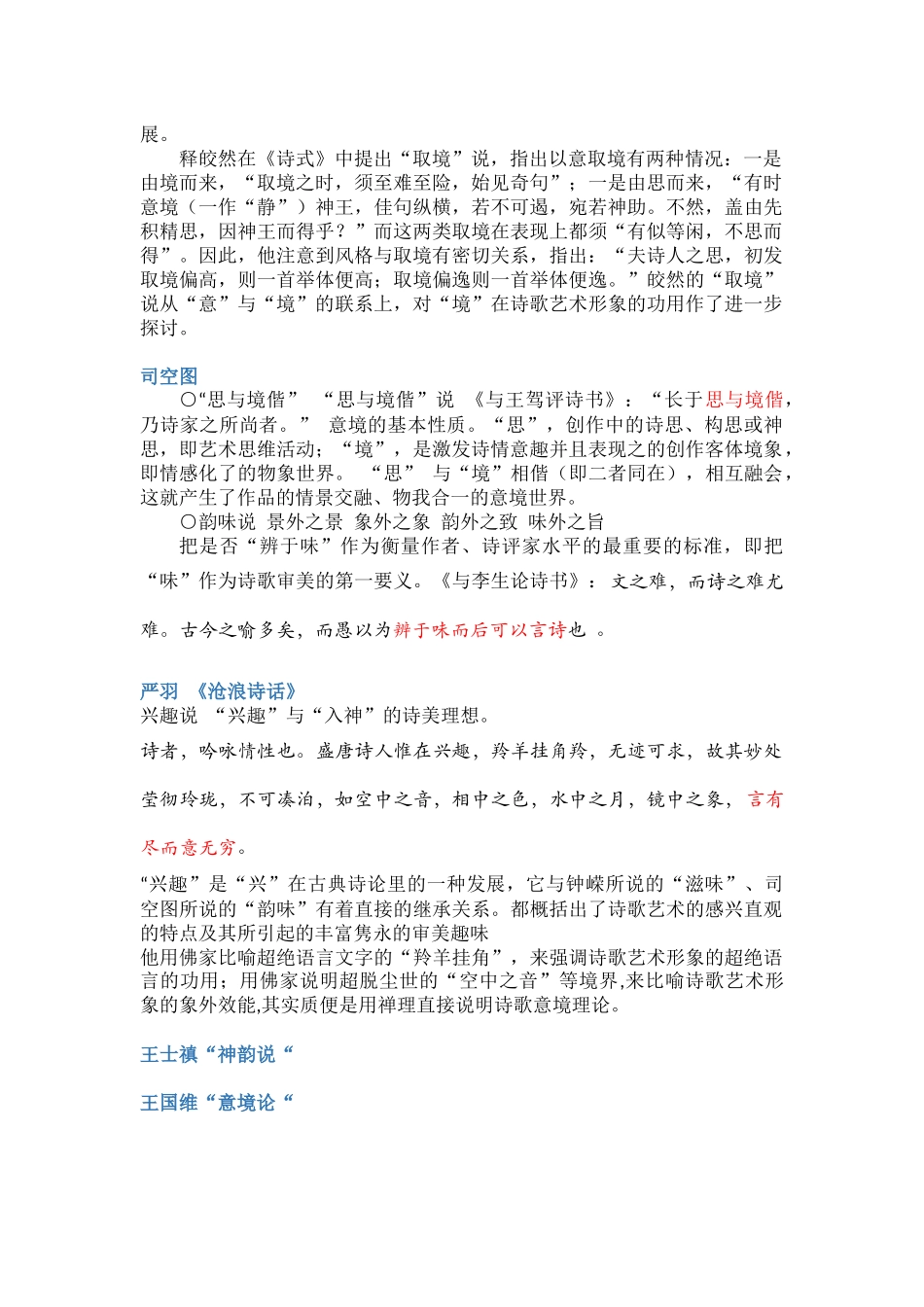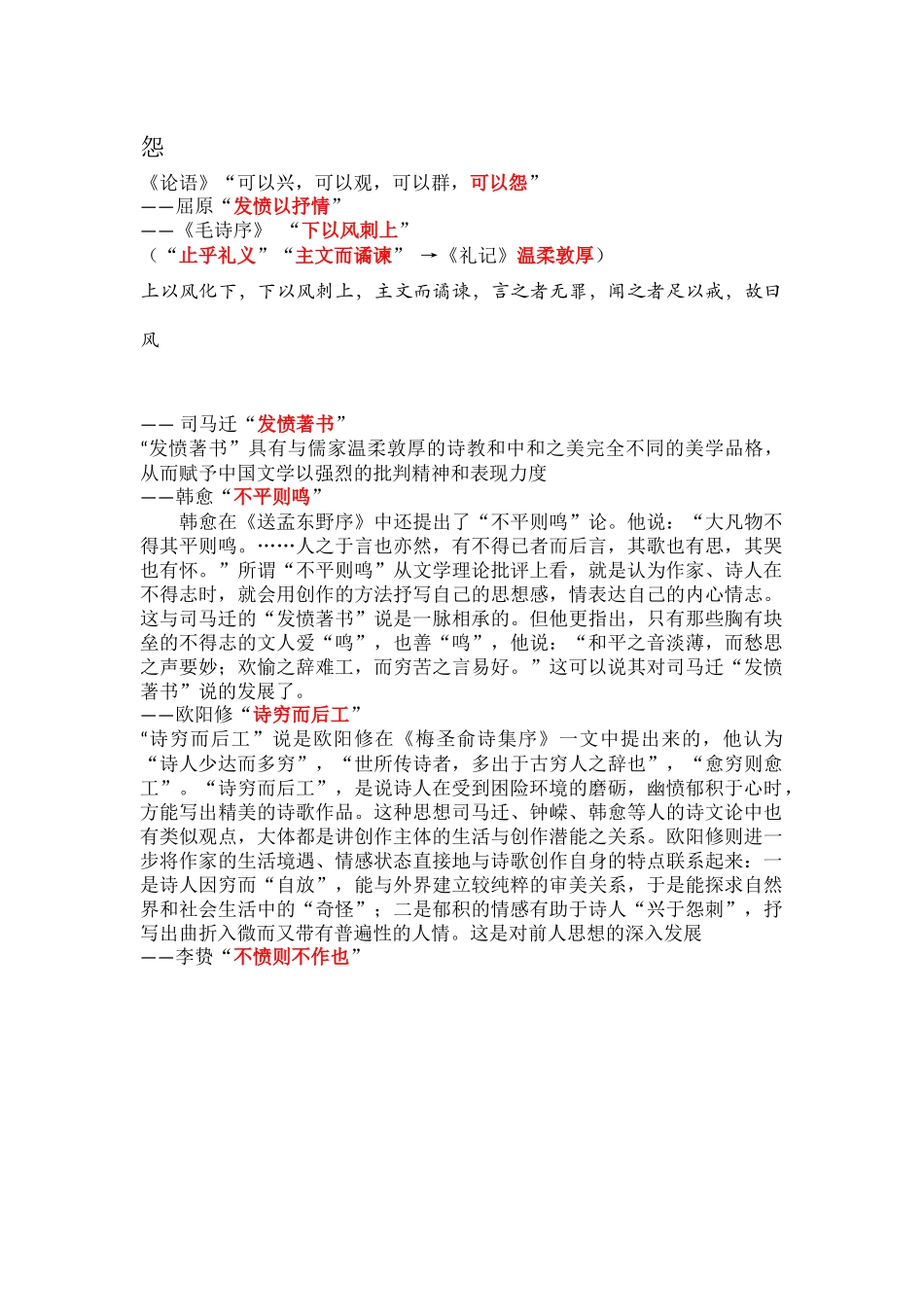言与意老庄言――意――道“圣人立象以尽意”《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两晋南朝文论逐渐接触到主观思想感情和客观景色物象的关系问题。晋代陆机感到文学创作的主要困难之一,便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序》)《文心雕龙》《神思》神与物游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认为创作构思是由作者感情所孕育激发的,通过想象进行的;而激情和想象则是从客观物象外貌引起的,通过思维认识的。《诗品序》钟嵘○“滋味说”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兴文已尽而意有余“境”、“境界”都不指客观物象和环境,而是指人的主观对客观的感受、体会、认识。唐代诗论的“意境”说“意境”作为文论术语,始于唐代。托名为盛唐诗人王昌龄所撰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意”、“境”论诗,在中唐发展为要求“意”、“境”结合的“意境”说,并要求具有独特的艺术形象,在理论上有重大进展。释皎然在《诗式》中提出“取境”说,指出以意取境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境而来,“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一是由思而来,“有时意境(一作“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而这两类取境在表现上都须“有似等闲,不思而得”。因此,他注意到风格与取境有密切关系,指出:“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皎然的“取境”说从“意”与“境”的联系上,对“境”在诗歌艺术形象的功用作了进一步探讨。司空图○“思与境偕”“思与境偕”说《与王驾评诗书》:“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意境的基本性质。“思”,创作中的诗思、构思或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境”,是激发诗情意趣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即情感化了的物象世界。“思”与“境”相偕(即二者同在),相互融会,这就产生了作品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世界。○韵味说景外之景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把是否“辨于味”作为衡量作者、诗评家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即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严羽《沧浪诗话》兴趣说“兴趣”与“入神”的诗美理想。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羚,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了诗歌艺术的感兴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他用佛家比喻超绝语言文字的“羚羊挂角”,来强调诗歌艺术形象的超绝语言的功用;用佛家说明超脱尘世的“空中之音”等境界,来比喻诗歌艺术形象的象外效能,其实质便是用禅理直接说明诗歌意境理论。王士禛“神韵说“王国维“意境论“怨《论语》“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毛诗序》“下以风刺上”(“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礼记》温柔敦厚)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司马迁“发愤著书”“发愤著书”具有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