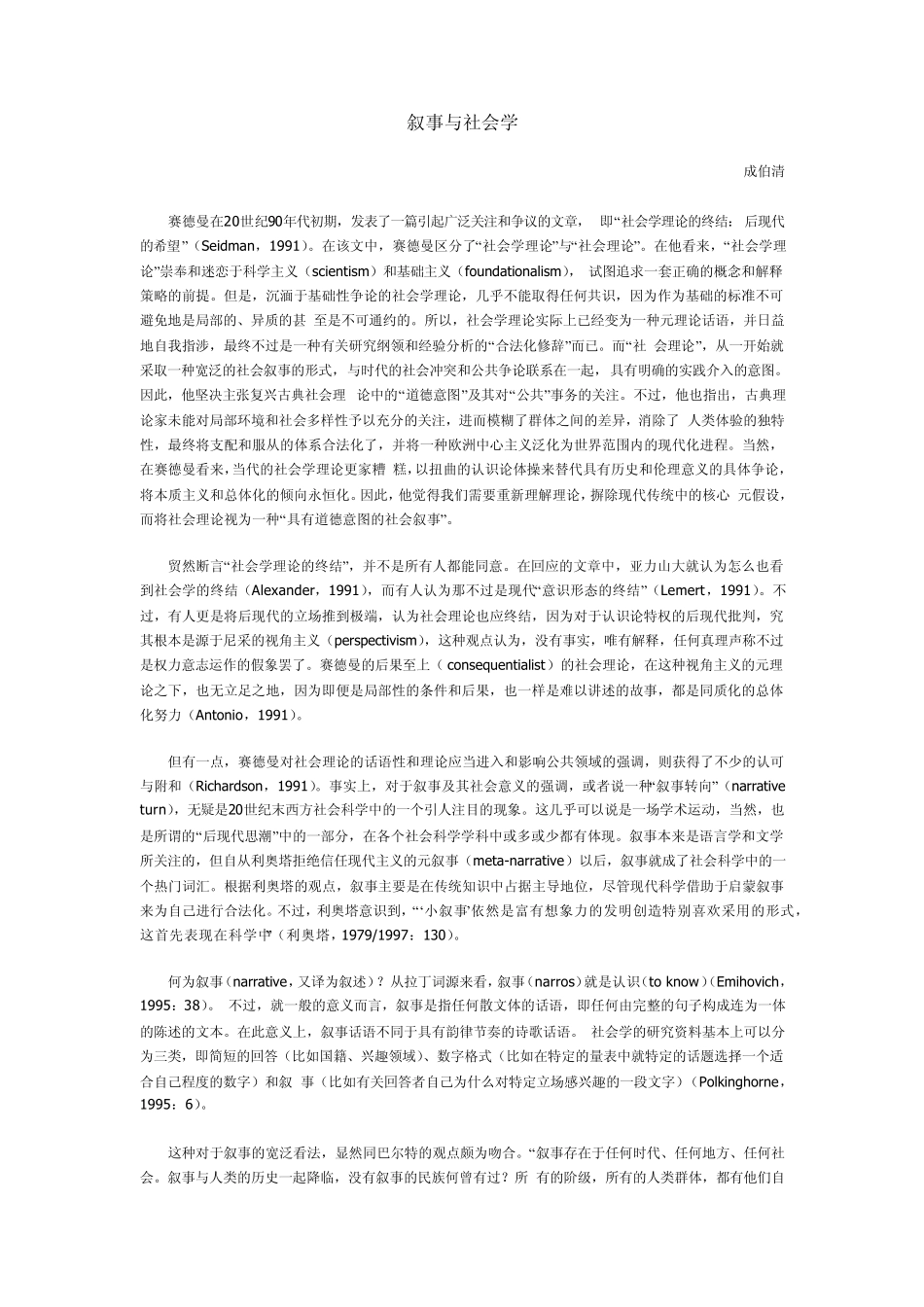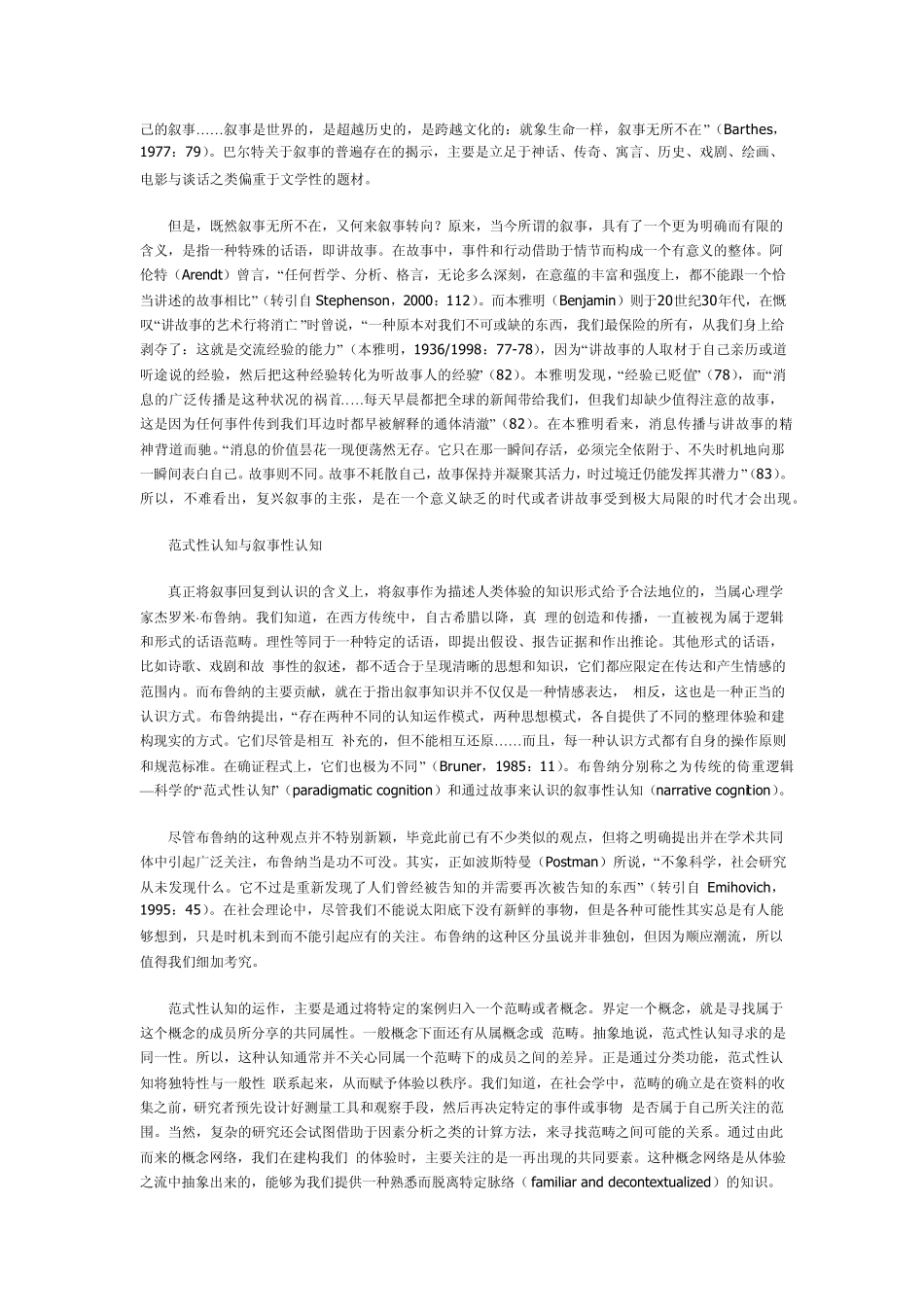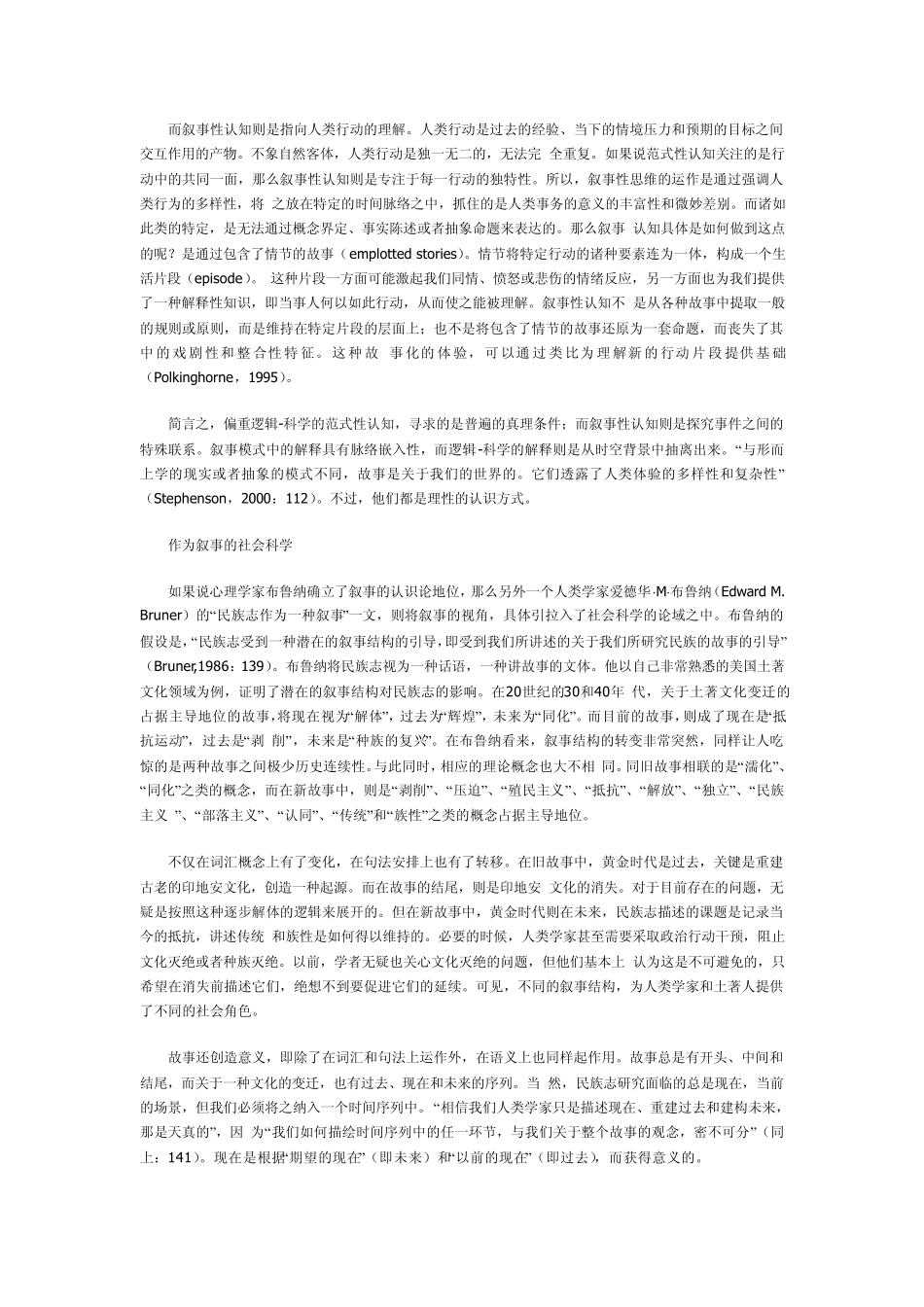叙事与社会学 成伯清 赛德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文章,即“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后现代的希望”(Seidman,1991)。在该文中,赛德曼区分了“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在他看来,“社会学理论”崇奉和迷恋于科学主义(scientism)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试图追求一套正确的概念和解释策略的前提。但是,沉湎于基础性争论的社会学理论,几乎不能取得任何共识,因为作为基础的标准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异质的甚 至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元理论话语,并日益地自我指涉,最终不过是一种有关研究纲领和经验分析的“合法化修辞”而已。而“社 会理论”,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宽泛的社会叙事的形式,与时代的社会冲突和公共争论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的实践介入的意图。因此,他坚决主张复兴古典社会理 论中的“道德意图”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不过,他也指出,古典理论家未能对局部环境和社会多样性予以充分的关注,进而模糊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消除了 人类体验的独特性,最终将支配和服从的体系合法化了,并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泛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当然,在赛德曼看来,当代的社会学理论更家糟 糕,以扭曲的认识论体操来替代具有历史和伦理意义的具体争论,将本质主义和总体化的倾向永恒化。因此,他觉得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理论,摒除现代传统中的核心 元假设,而将社会理论视为一种“具有道德意图的社会叙事”。 贸然断言“社会学理论的终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在回应的文章中,亚力山大就认为怎么也看到社会学的终结(Alexander,1991),而有人认为那不过是现代“意识形态的终结”(Lemert,1991)。不过,有人更是将后现代的立场推到极端,认为社会理论也应终结,因为对于认识论特权的后现代批判,究其根本是源于尼采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这种观点认为,没有事实,唯有解释,任何真理声称不过是权力意志运作的假象罢了。赛德曼的后果至上(consequentialist)的社会理论,在这种视角主义的元理论之下,也无立足之地,因为即便是局部性的条件和后果,也一样是难以讲述的故事,都是同质化的总体化努力(Antonio,1991)。 但有一点,赛德曼对社会理论的话语性和理论应当进入和影响公共领域的强调,则获得了不少的认可与附和(Richardson,1991)。事实上,对于叙事及其社会意义的强调,或者说一种“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