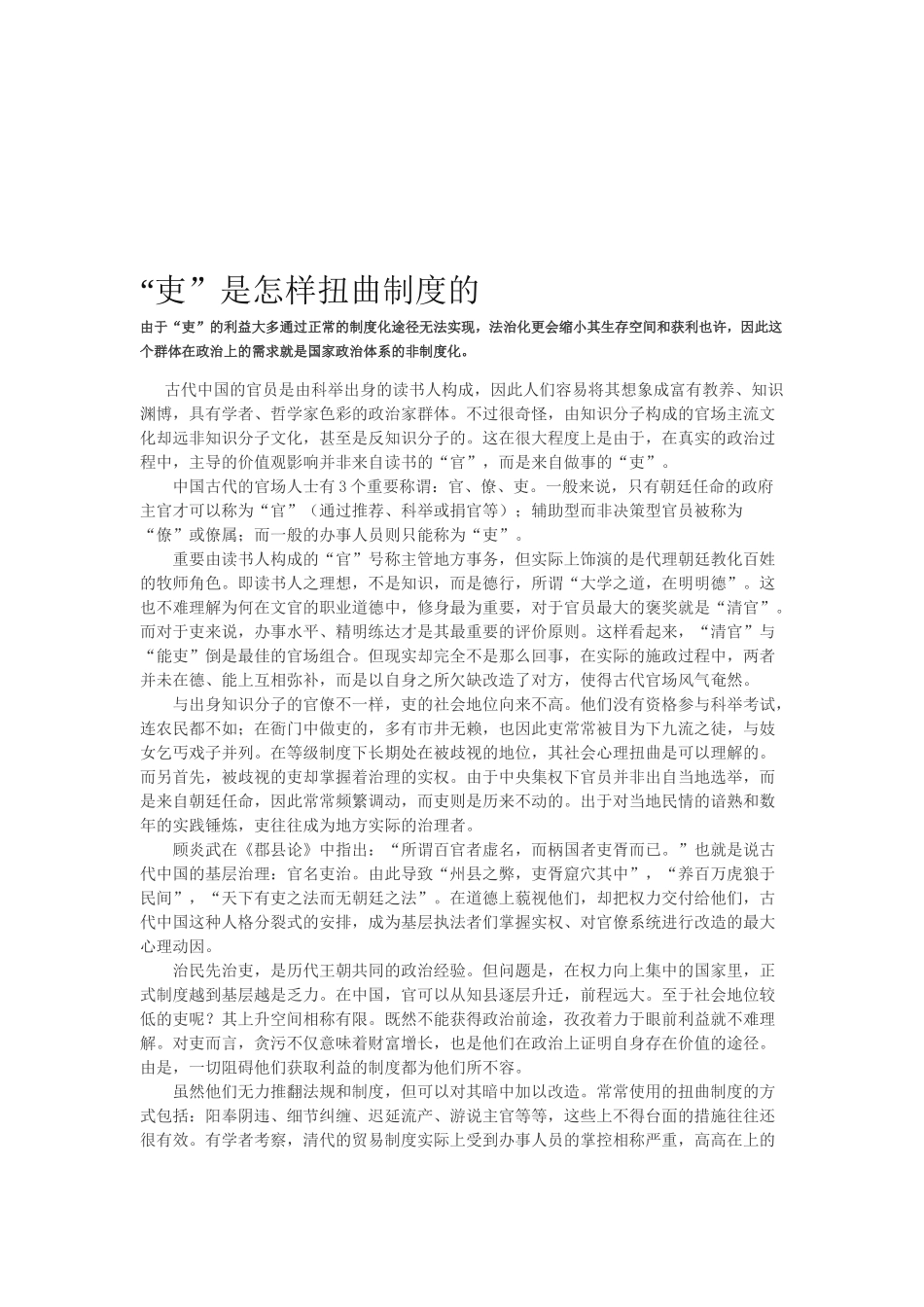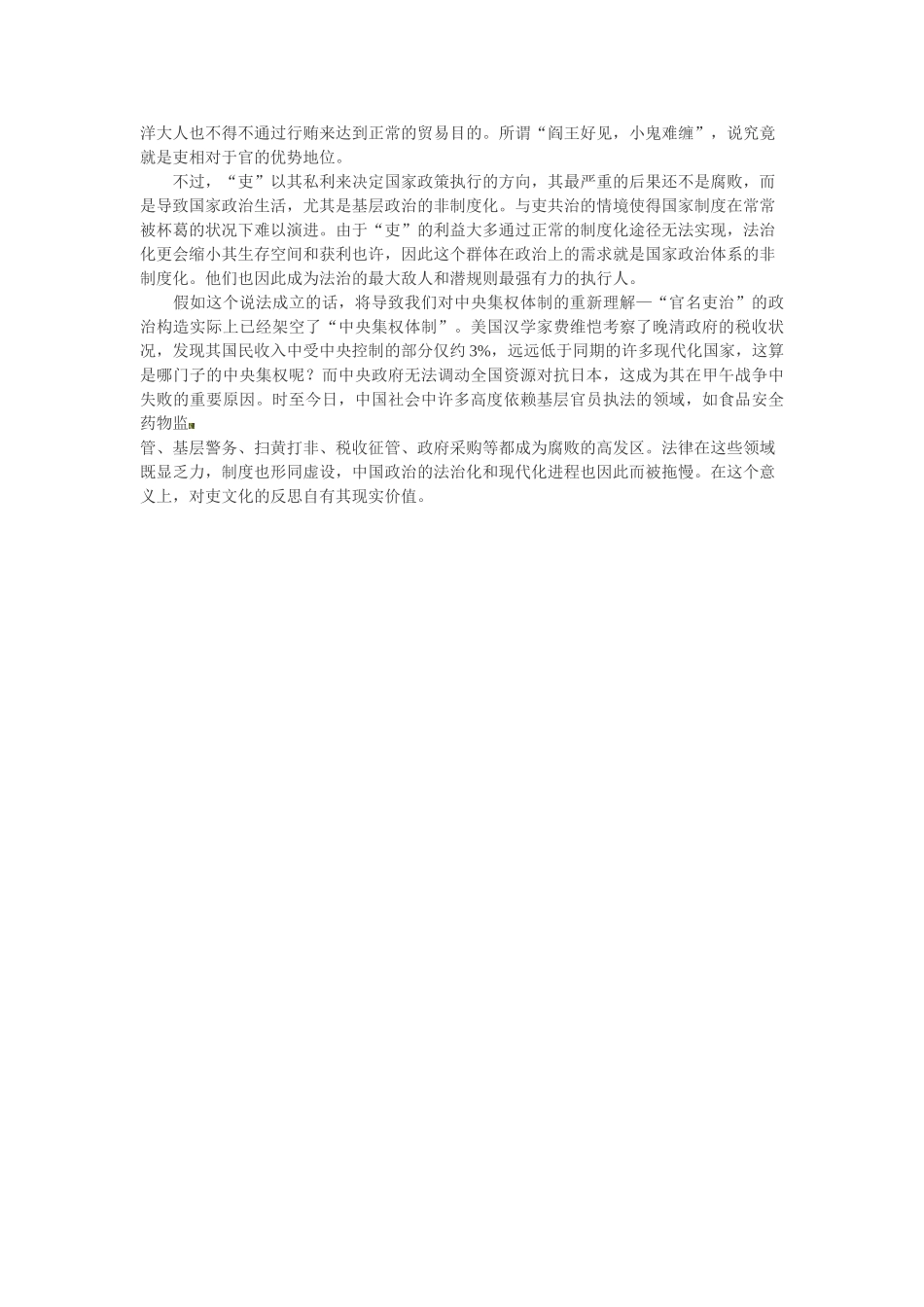“吏”是怎样扭曲制度的由于“吏”的利益大多通过正常的制度化途径无法实现,法治化更会缩小其生存空间和获利也许,因此这个群体在政治上的需求就是国家政治体系的非制度化。 古代中国的官员是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构成,因此人们容易将其想象成富有教养、知识渊博,具有学者、哲学家色彩的政治家群体。不过很奇怪,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官场主流文化却远非知识分子文化,甚至是反知识分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真实的政治过程中,主导的价值观影响并非来自读书的“官”,而是来自做事的“吏”。 中国古代的官场人士有 3 个重要称谓:官、僚、吏。一般来说,只有朝廷任命的政府主官才可以称为“官”(通过推荐、科举或捐官等);辅助型而非决策型官员被称为“僚”或僚属;而一般的办事人员则只能称为“吏”。 重要由读书人构成的“官”号称主管地方事务,但实际上饰演的是代理朝廷教化百姓的牧师角色。即读书人之理想,不是知识,而是德行,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文官的职业道德中,修身最为重要,对于官员最大的褒奖就是“清官”。而对于吏来说,办事水平、精明练达才是其最重要的评价原则。这样看起来,“清官”与“能吏”倒是最佳的官场组合。但现实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实际的施政过程中,两者并未在德、能上互相弥补,而是以自身之所欠缺改造了对方,使得古代官场风气奄然。 与出身知识分子的官僚不一样,吏的社会地位向来不高。他们没有资格参与科举考试,连农民都不如;在衙门中做吏的,多有市井无赖,也因此吏常常被目为下九流之徒,与妓女乞丐戏子并列。在等级制度下长期处在被歧视的地位,其社会心理扭曲是可以理解的。而另首先,被歧视的吏却掌握着治理的实权。由于中央集权下官员并非出自当地选举,而是来自朝廷任命,因此常常频繁调动,而吏则是历来不动的。出于对当地民情的谙熟和数年的实践锤炼,吏往往成为地方实际的治理者。 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指出:“所谓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基层治理:官名吏治。由此导致“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天下有吏之法而无朝廷之法”。在道德上藐视他们,却把权力交付给他们,古代中国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安排,成为基层执法者们掌握实权、对官僚系统进行改造的最大心理动因。 治民先治吏,是历代王朝共同的政治经验。但问题是,在权力向上集中的国家里,正式制度越到基层越是乏力。在中国,官可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