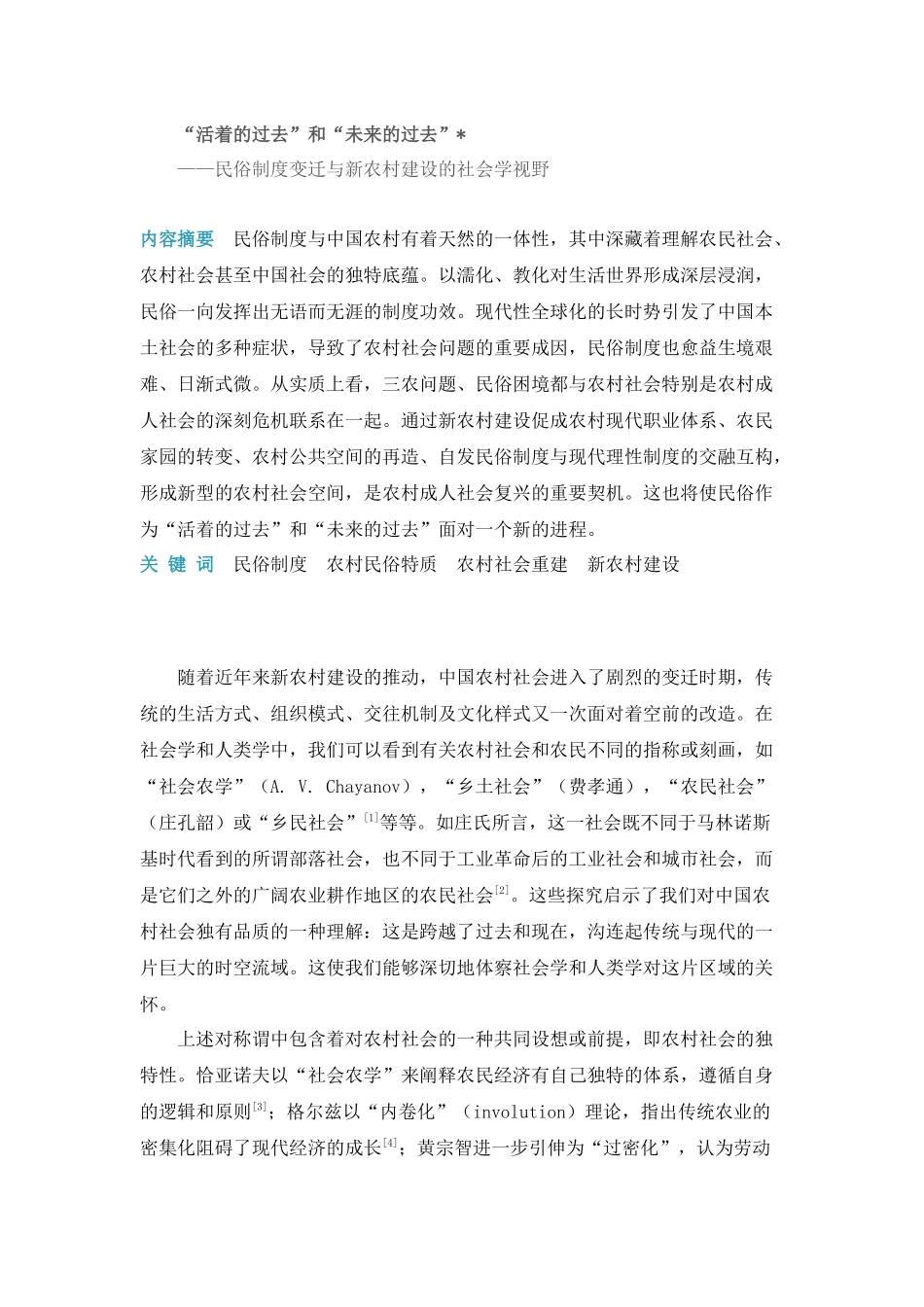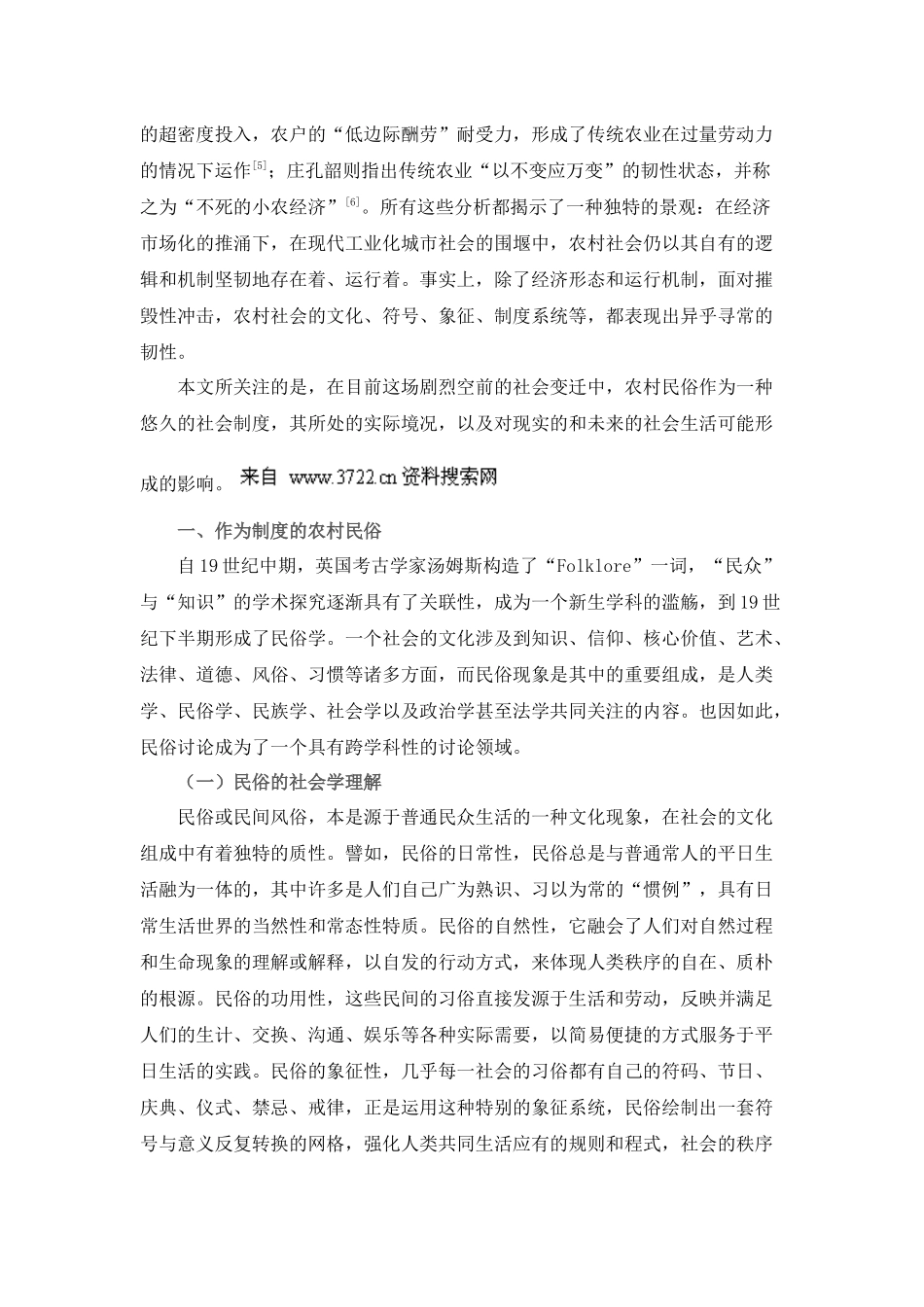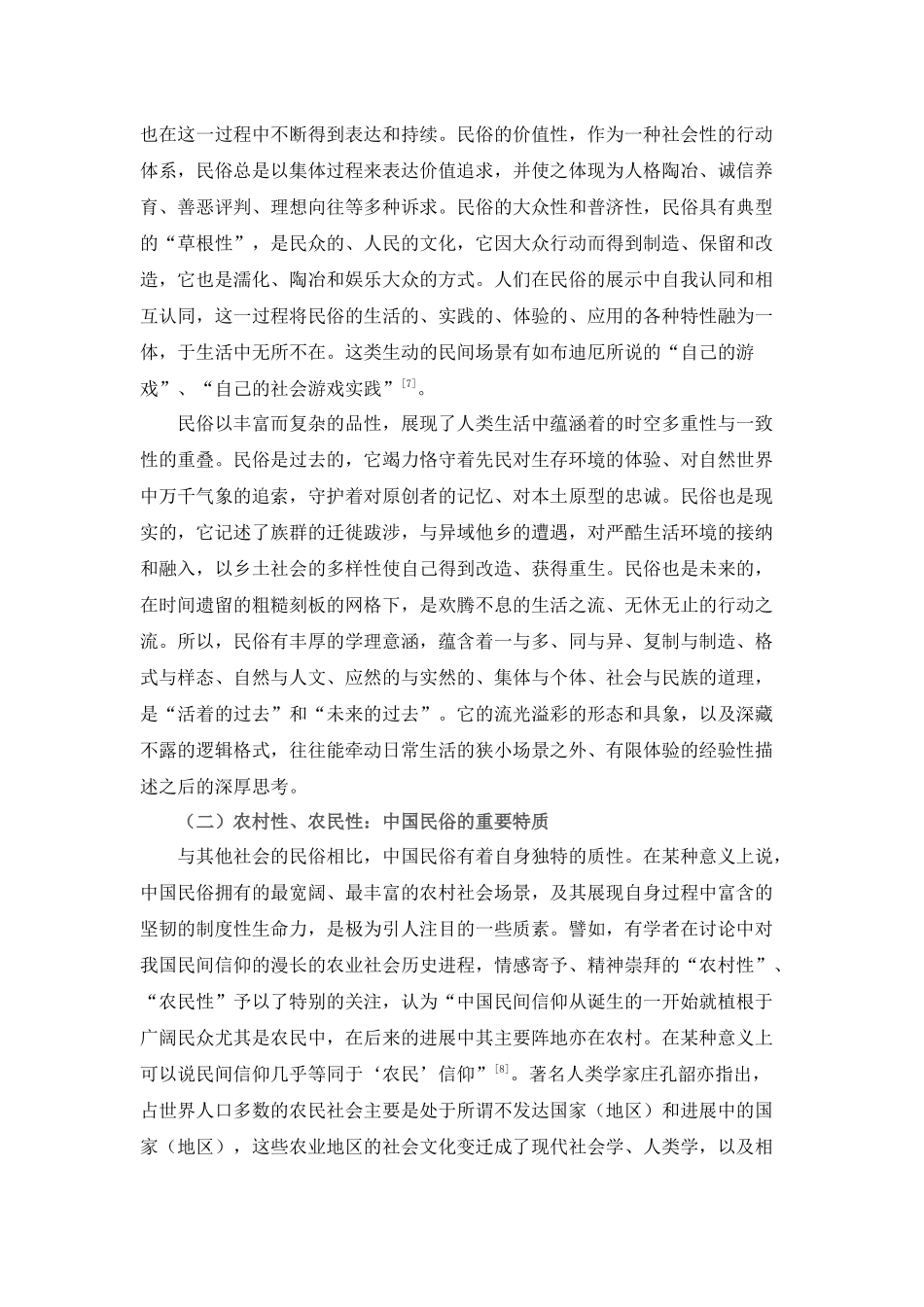“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 ——民俗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 内容摘要 民俗制度与中国农村有着天然的一体性,其中深藏着理解农民社会、农村社会甚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底蕴。以濡化、教化对生活世界形成深层浸润,民俗一向发挥出无语而无涯的制度功效。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时势引发了中国本土社会的多种症状,导致了农村社会问题的重要成因,民俗制度也愈益生境艰难、日渐式微。从实质上看,三农问题、民俗困境都与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村成人社会的深刻危机联系在一起。通过新农村建设促成农村现代职业体系、农民家园的转变、农村公共空间的再造、自发民俗制度与现代理性制度的交融互构,形成新型的农村社会空间,是农村成人社会复兴的重要契机。这也将使民俗作为“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面对一个新的进程。 关 键 词 民俗制度 农村民俗特质 农村社会重建 新农村建设 随着近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中国农村社会进入了剧烈的变迁时期,传统的生活方式、组织模式、交往机制及文化样式又一次面对着空前的改造。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农村社会和农民不同的指称或刻画,如“社会农学”(A. V. Chayanov),“乡土社会”(费孝通),“农民社会”(庄孔韶)或“乡民社会”[1]等等。如庄氏所言,这一社会既不同于马林诺斯基时代看到的所谓部落社会,也不同于工业革命后的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而是它们之外的广阔农业耕作地区的农民社会[2]。这些探究启示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社会独有品质的一种理解:这是跨越了过去和现在,沟连起传统与现代的一片巨大的时空流域。这使我们能够深切地体察社会学和人类学对这片区域的关怀。 上述对称谓中包含着对农村社会的一种共同设想或前提,即农村社会的独特性。恰亚诺夫以“社会农学”来阐释农民经济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遵循自身的逻辑和原则[3];格尔兹以“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指出传统农业的密集化阻碍了现代经济的成长[4];黄宗智进一步引伸为“过密化”,认为劳动的超密度投入,农户的“低边际酬劳”耐受力,形成了传统农业在过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运作[5];庄孔韶则指出传统农业“以不变应万变”的韧性状态,并称之为“不死的小农经济”[6]。所有这些分析都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在经济市场化的推涌下,在现代工业化城市社会的围堰中,农村社会仍以其自有的逻辑和机制坚韧地存在着、运行着。事实上,除了经济形态和运行机制,面对摧毁性冲击,农村社会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