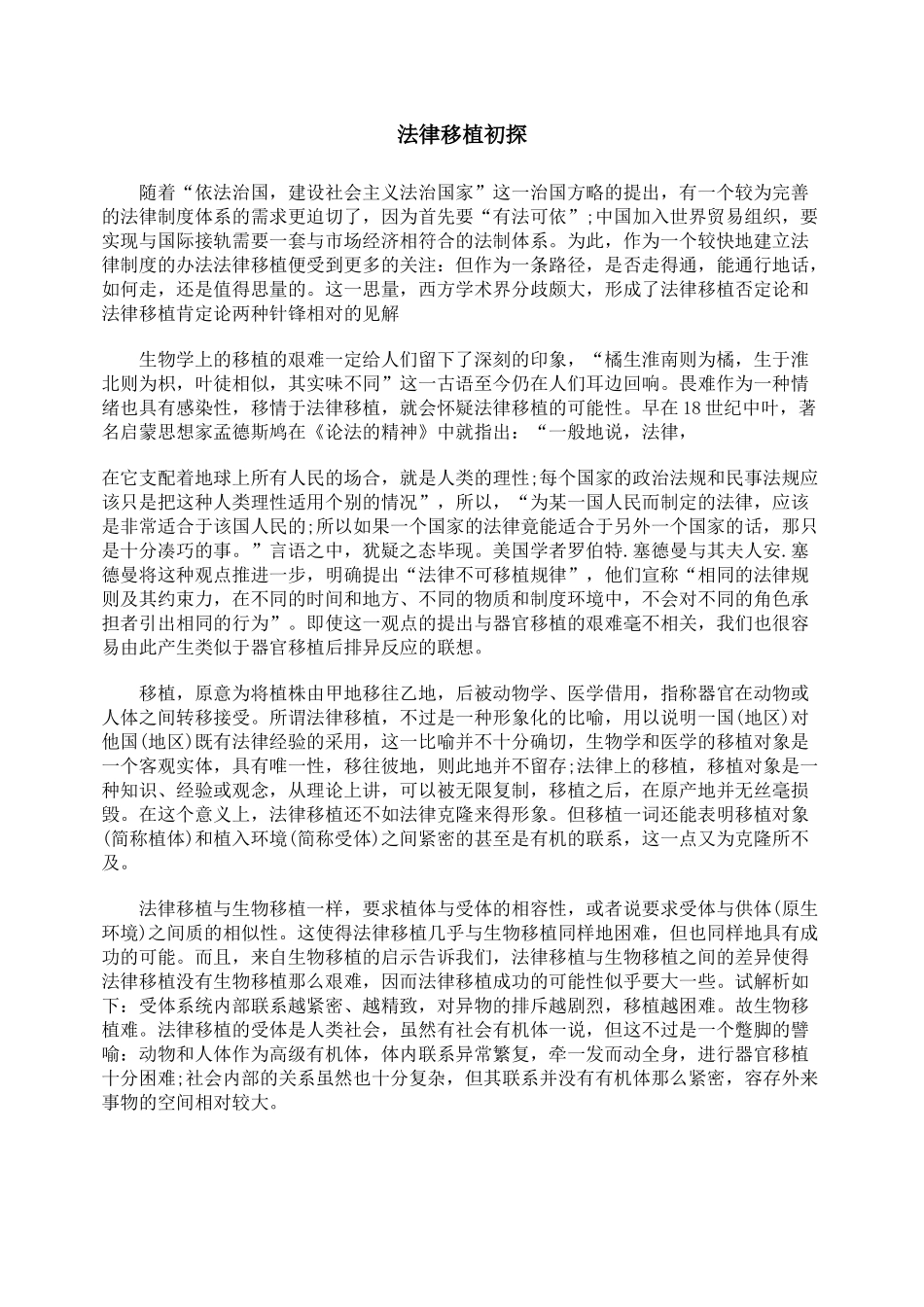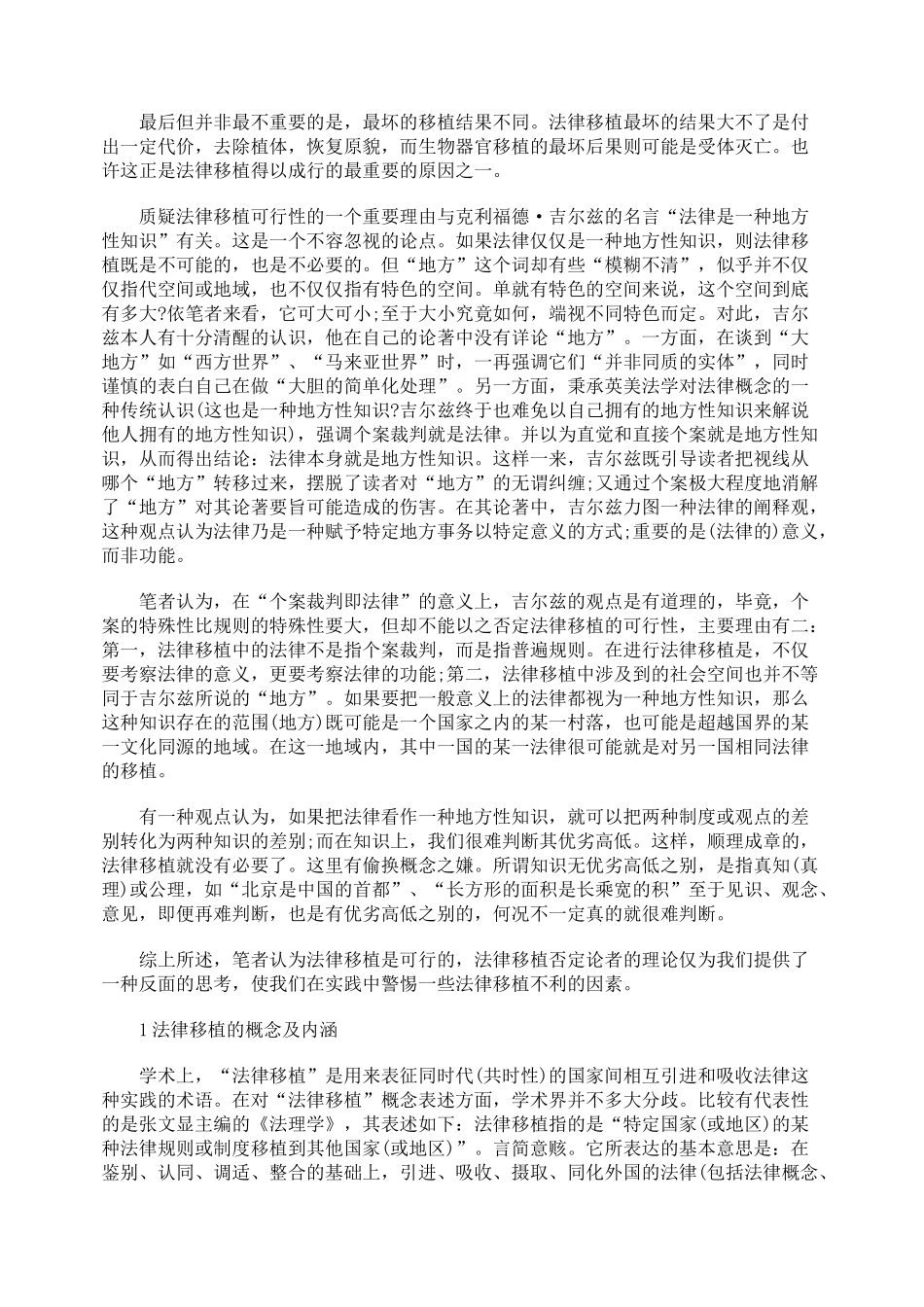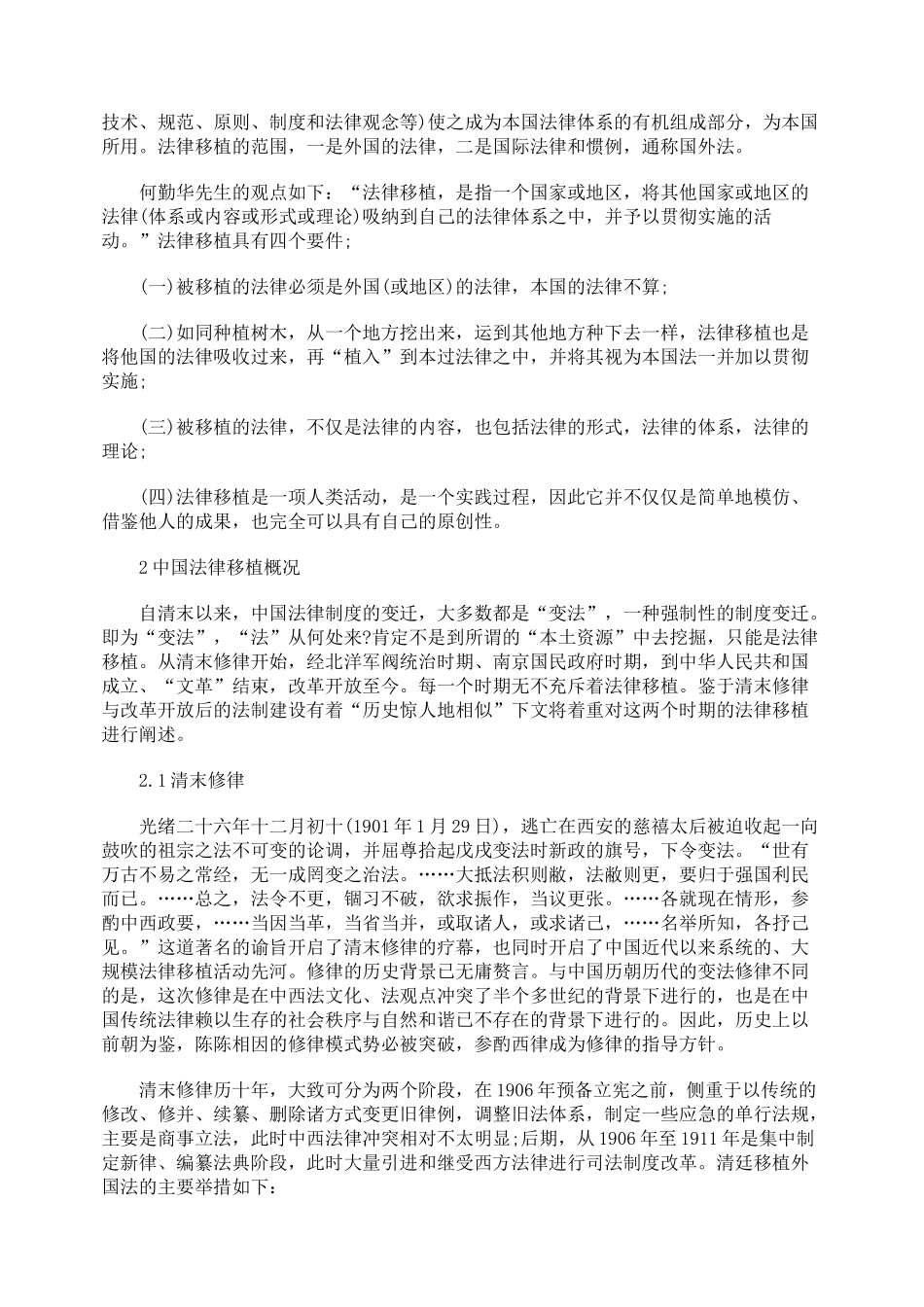法律移植初探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需求更迫切了,因为首先要“有法可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实现与国际接轨需要一套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法制体系。为此,作为一个较快地建立法律制度的办法法律移植便受到更多的关注:但作为一条路径,是否走得通,能通行地话,如何走,还是值得思量的。这一思量,西方学术界分歧颇大,形成了法律移植否定论和法律移植肯定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 生物学上的移植的艰难一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这一古语至今仍在人们耳边回响。畏难作为一种情绪也具有感染性,移情于法律移植,就会怀疑法律移植的可能性。早在 18 世纪中叶,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指出:“一般地说,法律, 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个别的情况”,所以,“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十分凑巧的事。”言语之中,犹疑之态毕现。美国学者罗伯特.塞德曼与其夫人安.塞德曼将这种观点推进一步,明确提出“法律不可移植规律”,他们宣称“相同的法律规则及其约束力,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不同的物质和制度环境中,不会对不同的角色承担者引出相同的行为”。即使这一观点的提出与器官移植的艰难毫不相关,我们也很容易由此产生类似于器官移植后排异反应的联想。 移植,原意为将植株由甲地移往乙地,后被动物学、医学借用,指称器官在动物或人体之间转移接受。所谓法律移植,不过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用以说明一国(地区)对他国(地区)既有法律经验的采用,这一比喻并不十分确切,生物学和医学的移植对象是一个客观实体,具有唯一性,移往彼地,则此地并不留存;法律上的移植,移植对象是一种知识、经验或观念,从理论上讲,可以被无限复制,移植之后,在原产地并无丝毫损毁。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移植还不如法律克隆来得形象。但移植一词还能表明移植对象(简称植体)和植入环境(简称受体)之间紧密的甚至是有机的联系,这一点又为克隆所不及。 法律移植与生物移植一样,要求植体与受体的相容性,或者说要求受体与供体(原生环境)之间质的相似性。这使得法律移植几乎与生物移植同样地困难,但也同样地具有成功的可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