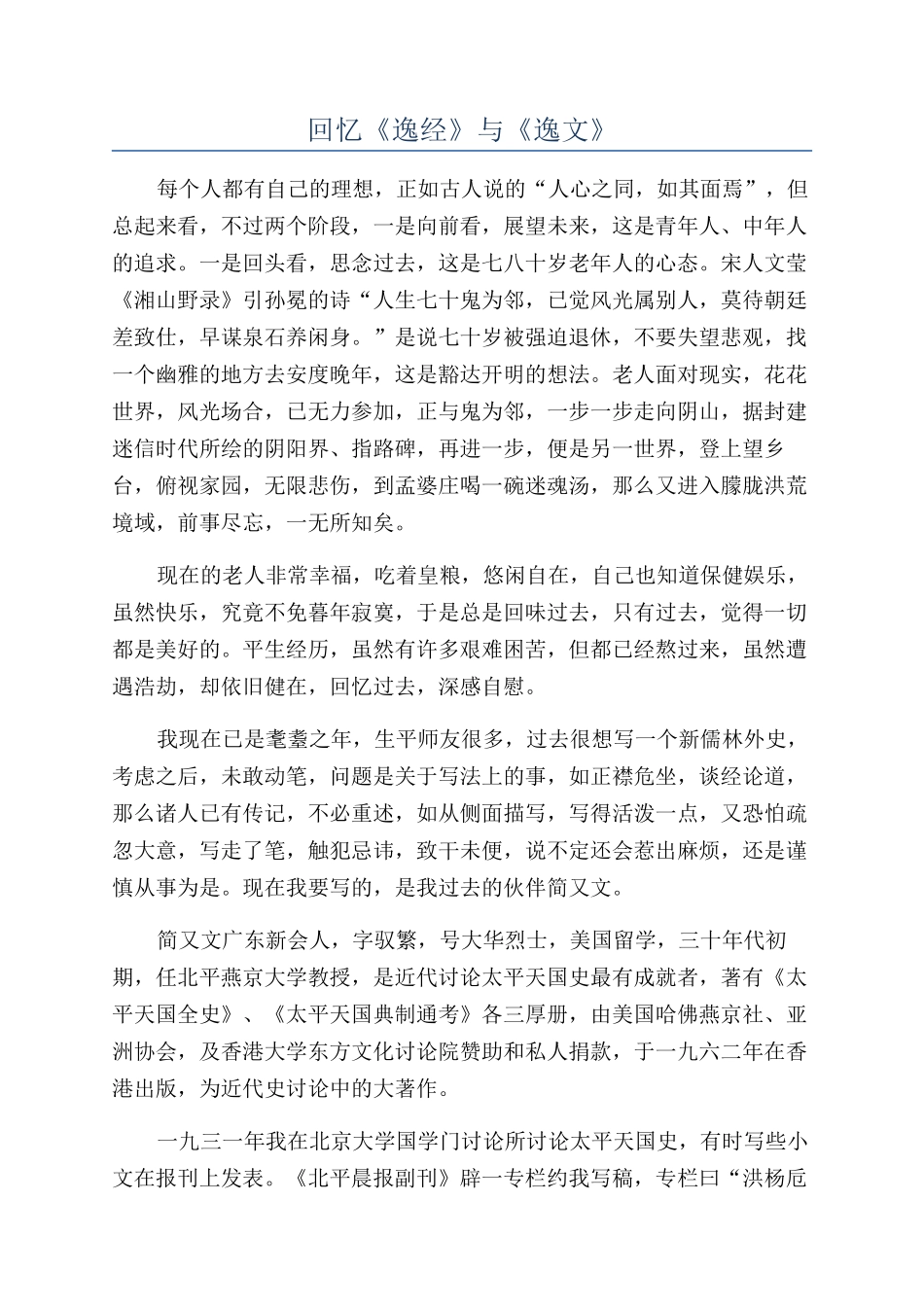回忆《逸经》与《逸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正如古人说的“人心之同,如其面焉”,但总起来看,不过两个阶段,一是向前看,展望未来,这是青年人、中年人的追求。一是回头看,思念过去,这是七八十岁老年人的心态。宋人文莹《湘山野录》引孙冕的诗“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是说七十岁被强迫退休,不要失望悲观,找一个幽雅的地方去安度晚年,这是豁达开明的想法。老人面对现实,花花世界,风光场合,已无力参加,正与鬼为邻,一步一步走向阴山,据封建迷信时代所绘的阴阳界、指路碑,再进一步,便是另一世界,登上望乡台,俯视家园,无限悲伤,到孟婆庄喝一碗迷魂汤,那么又进入朦胧洪荒境域,前事尽忘,一无所知矣。现在的老人非常幸福,吃着皇粮,悠闲自在,自己也知道保健娱乐,虽然快乐,究竟不免暮年寂寞,于是总是回味过去,只有过去,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平生经历,虽然有许多艰难困苦,但都已经熬过来,虽然遭遇浩劫,却依旧健在,回忆过去,深感自慰。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生平师友很多,过去很想写一个新儒林外史,考虑之后,未敢动笔,问题是关于写法上的事,如正襟危坐,谈经论道,那么诸人已有传记,不必重述,如从侧面描写,写得活泼一点,又恐怕疏忽大意,写走了笔,触犯忌讳,致干未便,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还是谨慎从事为是。现在我要写的,是我过去的伙伴简又文。简又文广东新会人,字驭繁,号大华烈士,美国留学,三十年代初期,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是近代讨论太平天国史最有成就者,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社、亚洲协会,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讨论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出版,为近代史讨论中的大著作。一九三一年我在北京大学国学门讨论所讨论太平天国史,有时写些小文在报刊上发表。《北平晨报副刊》辟一专栏约我写稿,专栏曰“洪杨卮谈”,专谈太平天国史事,至一九三二年夏,约写了一百多篇,引起文坛注意,北京图书馆编的《国学论文索引》把它收入第五编内。就在这时,简又文在燕大正从宗教的角度讨论太平天国与耶酥教的关系,写文章陆续在《京报》和《语丝》上发表,他写的《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都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就在此时,胡适之先生我和他见面。胡先生说,你们都是讨论太平天国史的,应该互相补益。又说简在海淀燕京大学(即今北大),只有班车,交通不便,进城后暂住东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