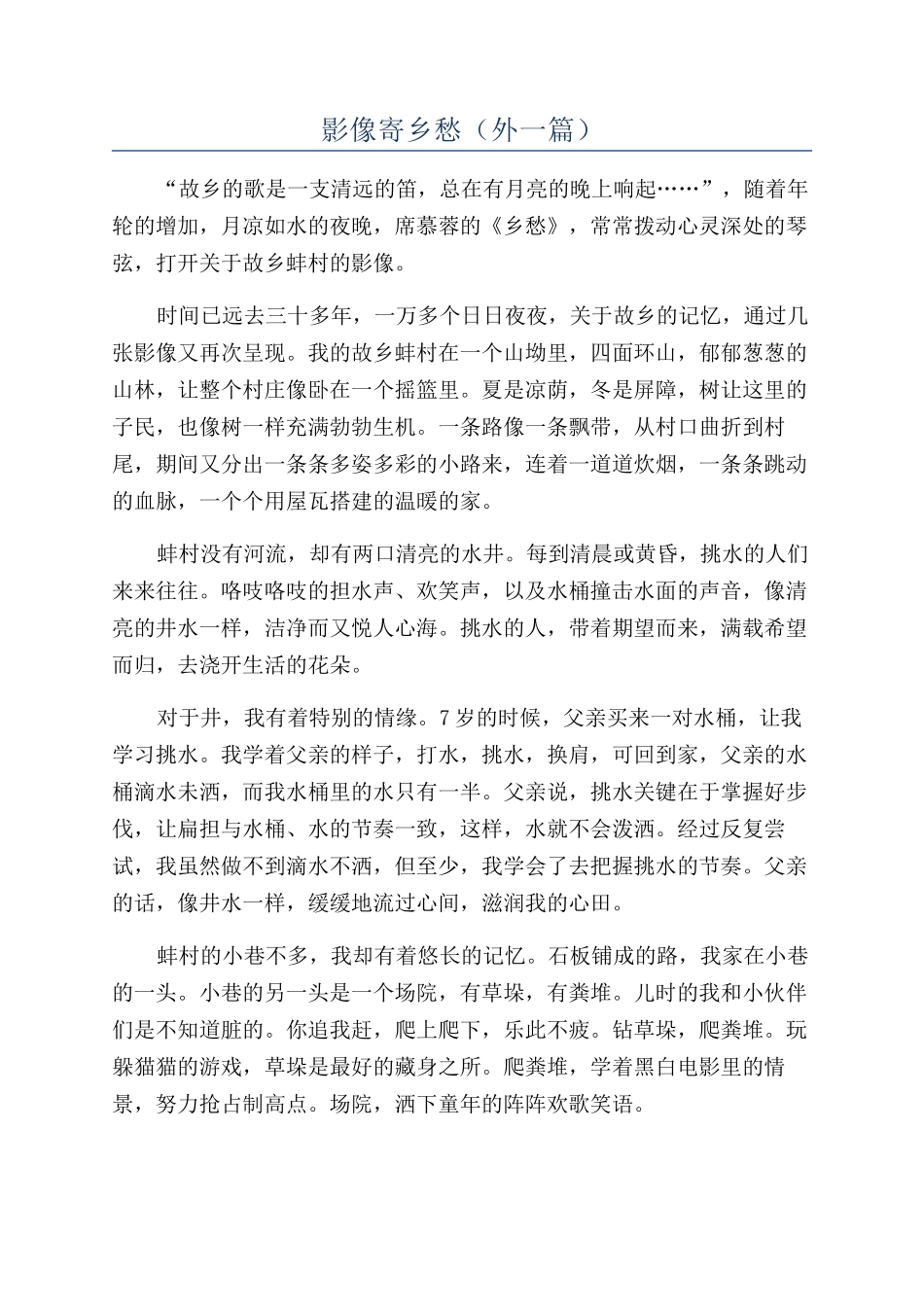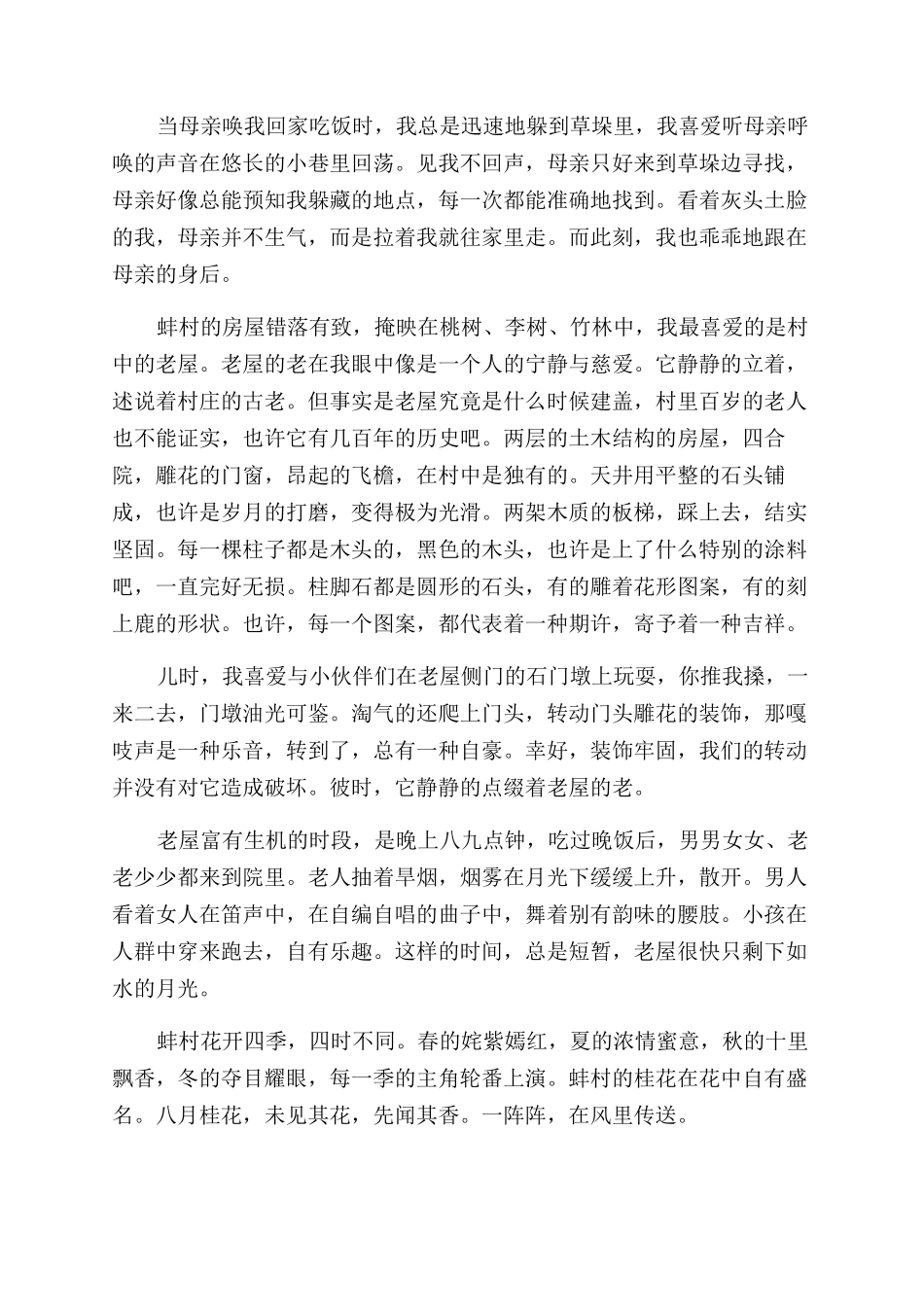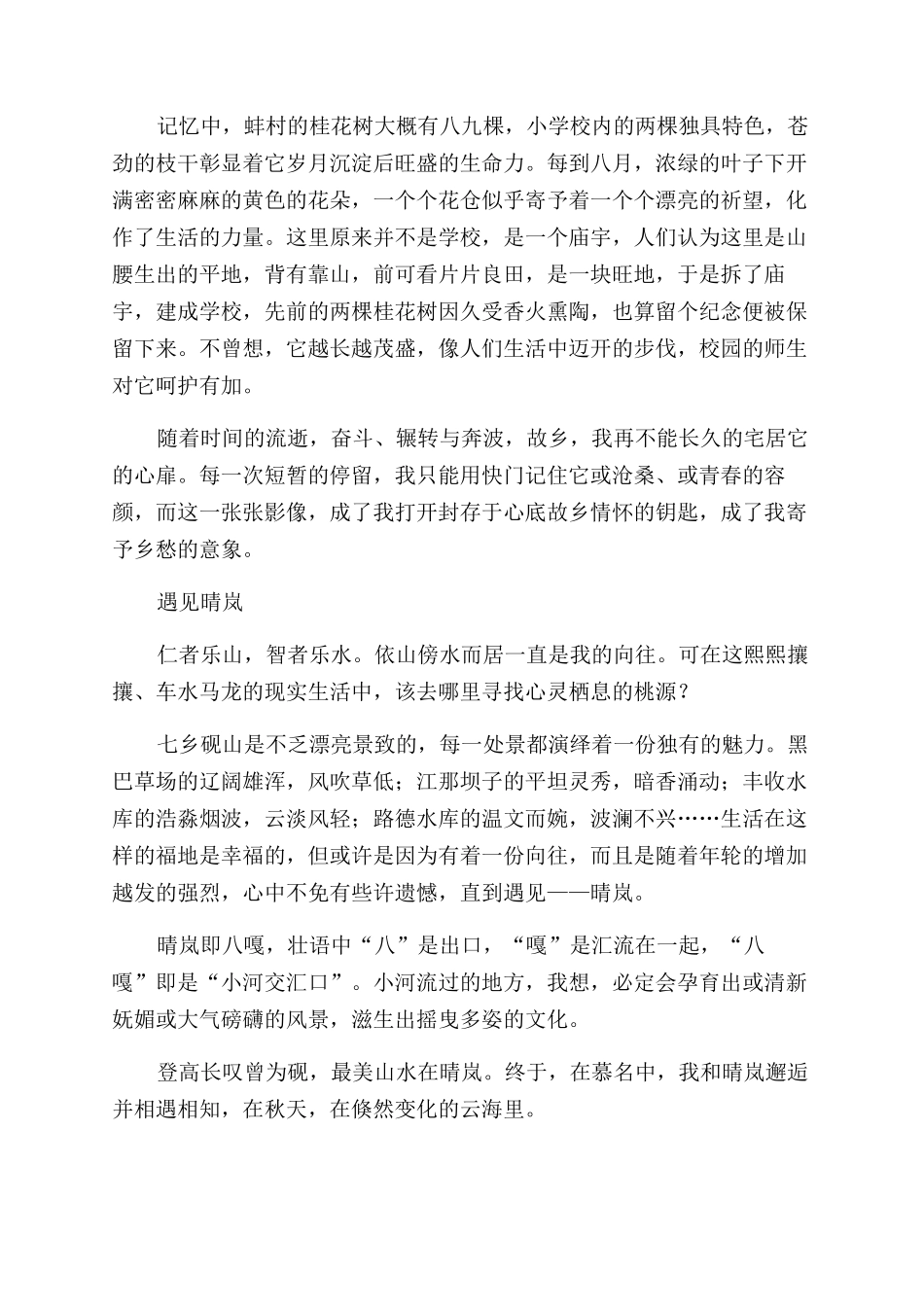影像寄乡愁(外一篇)“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随着年轮的增加,月凉如水的夜晚,席慕蓉的《乡愁》,常常拨动心灵深处的琴弦,打开关于故乡蚌村的影像。时间已远去三十多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关于故乡的记忆,通过几张影像又再次呈现。我的故乡蚌村在一个山坳里,四面环山,郁郁葱葱的山林,让整个村庄像卧在一个摇篮里。夏是凉荫,冬是屏障,树让这里的子民,也像树一样充满勃勃生机。一条路像一条飘带,从村口曲折到村尾,期间又分出一条条多姿多彩的小路来,连着一道道炊烟,一条条跳动的血脉,一个个用屋瓦搭建的温暖的家。蚌村没有河流,却有两口清亮的水井。每到清晨或黄昏,挑水的人们来来往往。咯吱咯吱的担水声、欢笑声,以及水桶撞击水面的声音,像清亮的井水一样,洁净而又悦人心海。挑水的人,带着期望而来,满载希望而归,去浇开生活的花朵。对于井,我有着特别的情缘。7 岁的时候,父亲买来一对水桶,让我学习挑水。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打水,挑水,换肩,可回到家,父亲的水桶滴水未洒,而我水桶里的水只有一半。父亲说,挑水关键在于掌握好步伐,让扁担与水桶、水的节奏一致,这样,水就不会泼洒。经过反复尝试,我虽然做不到滴水不洒,但至少,我学会了去把握挑水的节奏。父亲的话,像井水一样,缓缓地流过心间,滋润我的心田。蚌村的小巷不多,我却有着悠长的记忆。石板铺成的路,我家在小巷的一头。小巷的另一头是一个场院,有草垛,有粪堆。儿时的我和小伙伴们是不知道脏的。你追我赶,爬上爬下,乐此不疲。钻草垛,爬粪堆。玩躲猫猫的游戏,草垛是最好的藏身之所。爬粪堆,学着黑白电影里的情景,努力抢占制高点。场院,洒下童年的阵阵欢歌笑语。当母亲唤我回家吃饭时,我总是迅速地躲到草垛里,我喜爱听母亲呼唤的声音在悠长的小巷里回荡。见我不回声,母亲只好来到草垛边寻找,母亲好像总能预知我躲藏的地点,每一次都能准确地找到。看着灰头土脸的我,母亲并不生气,而是拉着我就往家里走。而此刻,我也乖乖地跟在母亲的身后。蚌村的房屋错落有致,掩映在桃树、李树、竹林中,我最喜爱的是村中的老屋。老屋的老在我眼中像是一个人的宁静与慈爱。它静静的立着,述说着村庄的古老。但事实是老屋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盖,村里百岁的老人也不能证实,也许它有几百年的历史吧。两层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四合院,雕花的门窗,昂起的飞檐,在村中是独有的。天井用平整的石头铺成,也许是岁月的打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