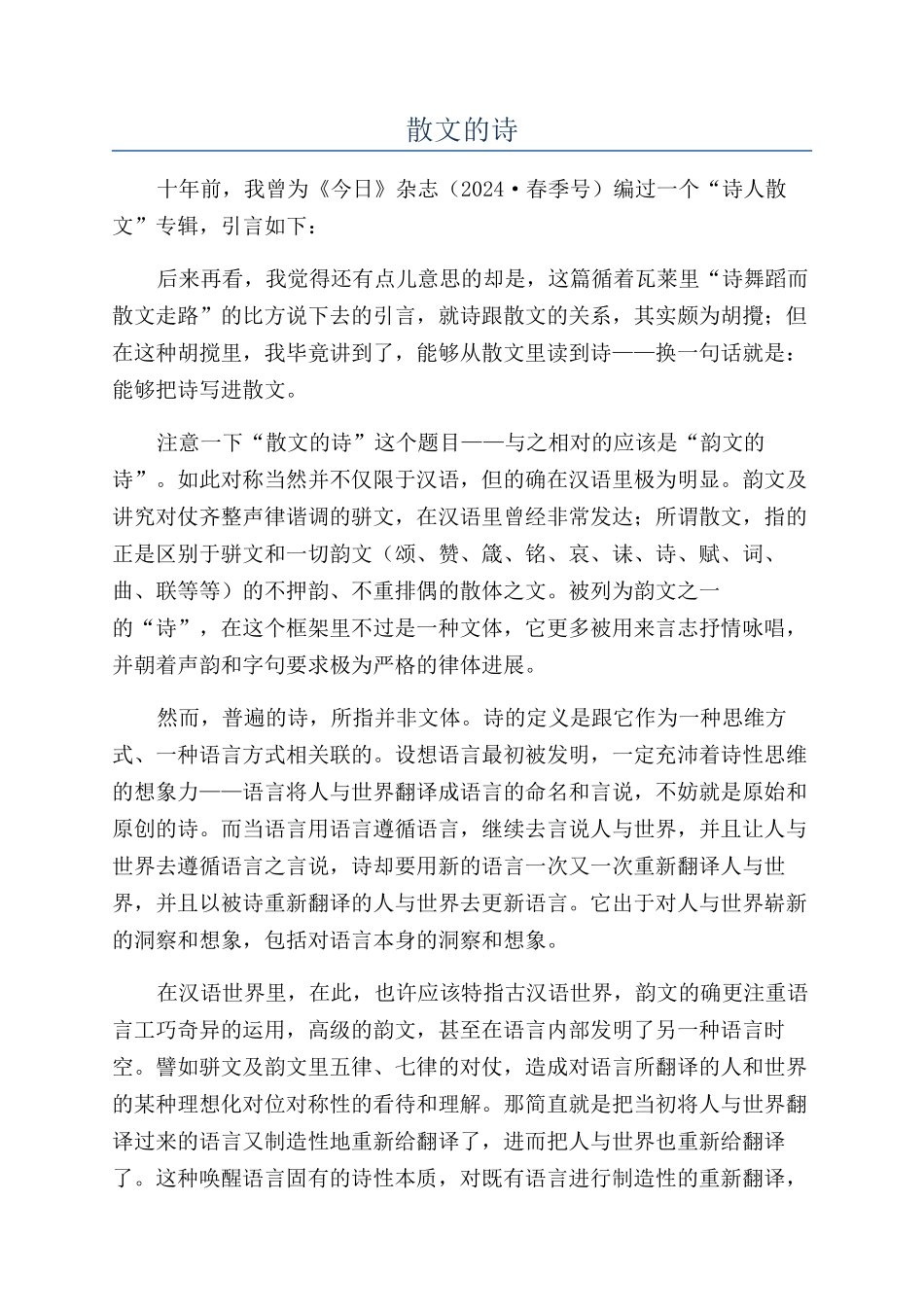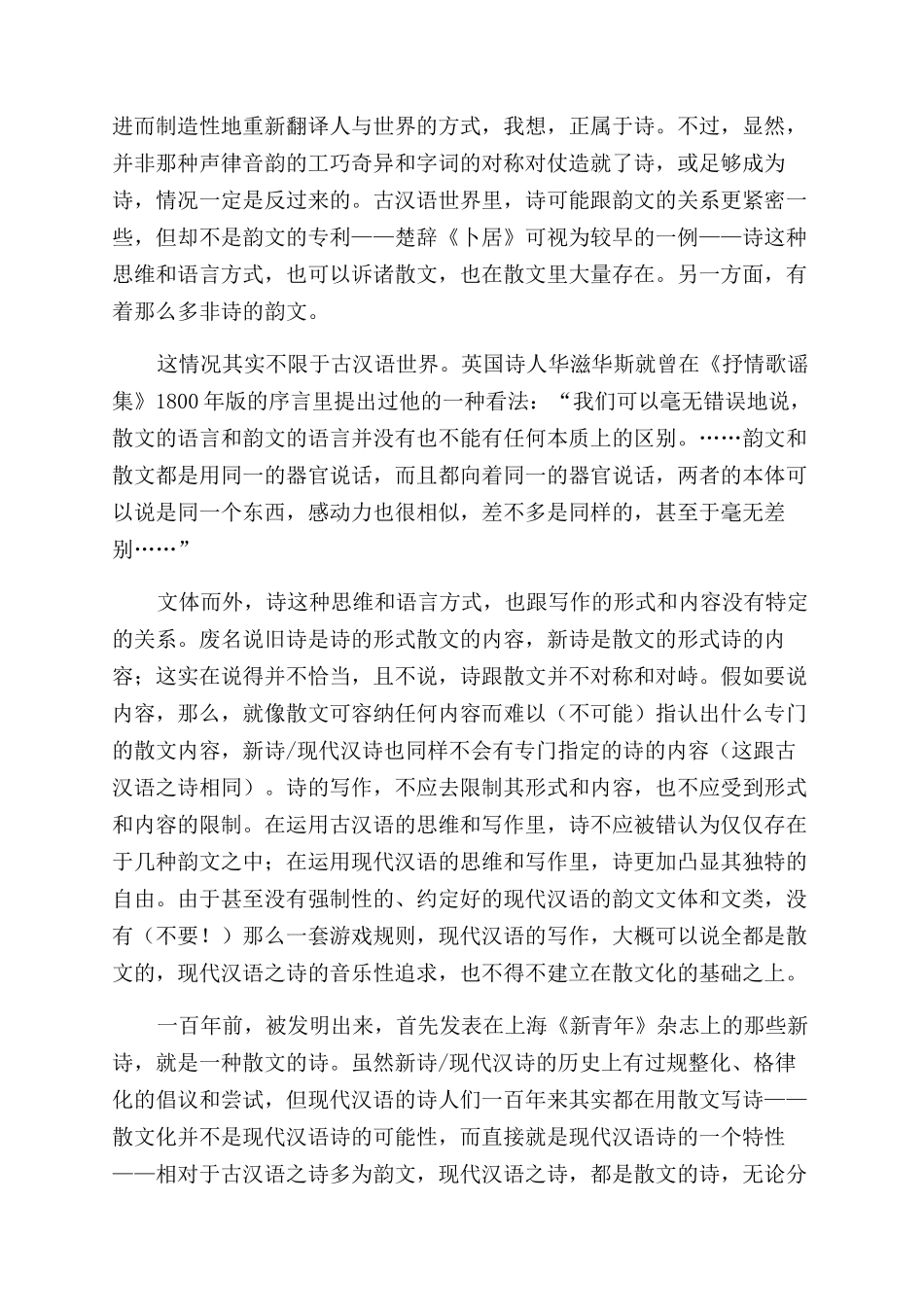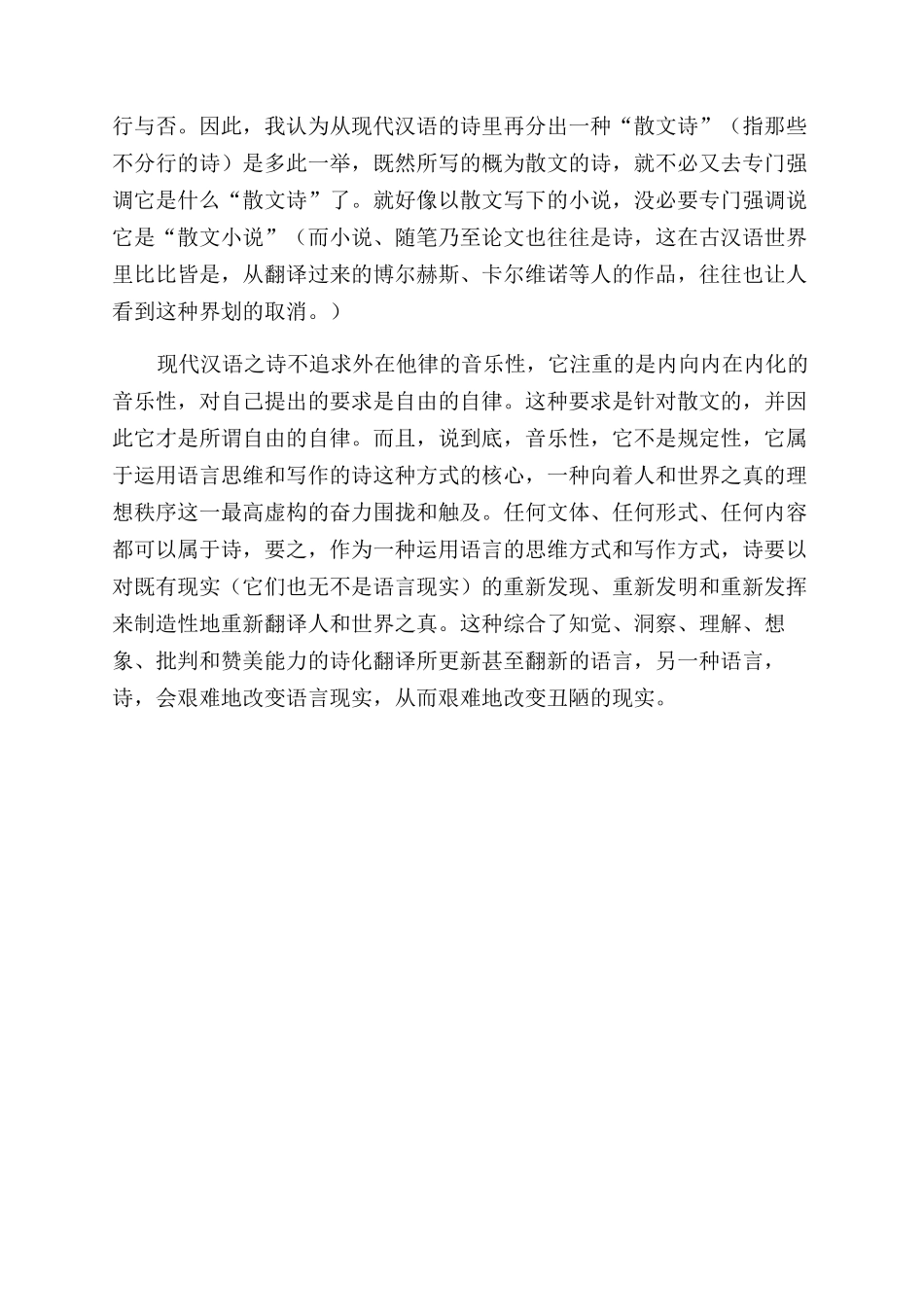散文的诗十年前,我曾为《今日》杂志(2024·春季号)编过一个“诗人散文”专辑,引言如下:后来再看,我觉得还有点儿意思的却是,这篇循着瓦莱里“诗舞蹈而散文走路”的比方说下去的引言,就诗跟散文的关系,其实颇为胡攪;但在这种胡搅里,我毕竟讲到了,能够从散文里读到诗——换一句话就是:能够把诗写进散文。注意一下“散文的诗”这个题目——与之相对的应该是“韵文的诗”。如此对称当然并不仅限于汉语,但的确在汉语里极为明显。韵文及讲究对仗齐整声律谐调的骈文,在汉语里曾经非常发达;所谓散文,指的正是区别于骈文和一切韵文(颂、赞、箴、铭、哀、诔、诗、赋、词、曲、联等等)的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之文。被列为韵文之一的“诗”,在这个框架里不过是一种文体,它更多被用来言志抒情咏唱,并朝着声韵和字句要求极为严格的律体进展。然而,普遍的诗,所指并非文体。诗的定义是跟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语言方式相关联的。设想语言最初被发明,一定充沛着诗性思维的想象力——语言将人与世界翻译成语言的命名和言说,不妨就是原始和原创的诗。而当语言用语言遵循语言,继续去言说人与世界,并且让人与世界去遵循语言之言说,诗却要用新的语言一次又一次重新翻译人与世界,并且以被诗重新翻译的人与世界去更新语言。它出于对人与世界崭新的洞察和想象,包括对语言本身的洞察和想象。在汉语世界里,在此,也许应该特指古汉语世界,韵文的确更注重语言工巧奇异的运用,高级的韵文,甚至在语言内部发明了另一种语言时空。譬如骈文及韵文里五律、七律的对仗,造成对语言所翻译的人和世界的某种理想化对位对称性的看待和理解。那简直就是把当初将人与世界翻译过来的语言又制造性地重新给翻译了,进而把人与世界也重新给翻译了。这种唤醒语言固有的诗性本质,对既有语言进行制造性的重新翻译,进而制造性地重新翻译人与世界的方式,我想,正属于诗。不过,显然,并非那种声律音韵的工巧奇异和字词的对称对仗造就了诗,或足够成为诗,情况一定是反过来的。古汉语世界里,诗可能跟韵文的关系更紧密一些,但却不是韵文的专利——楚辞《卜居》可视为较早的一例——诗这种思维和语言方式,也可以诉诸散文,也在散文里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有着那么多非诗的韵文。这情况其实不限于古汉语世界。英国诗人华滋华斯就曾在《抒情歌谣集》1800 年版的序言里提出过他的一种看法:“我们可以毫无错误地说,散文的语言和韵文的语言并没有也不能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