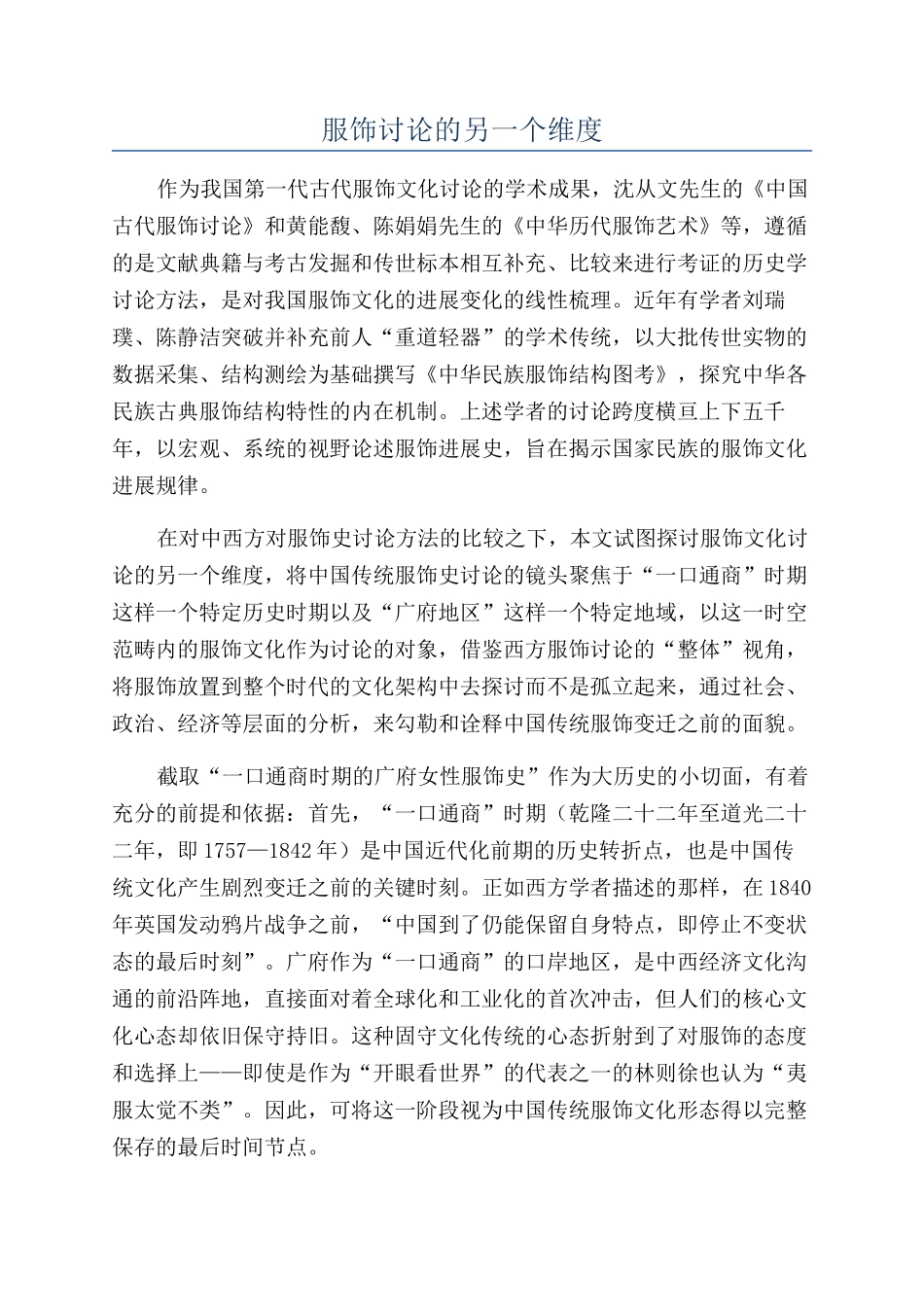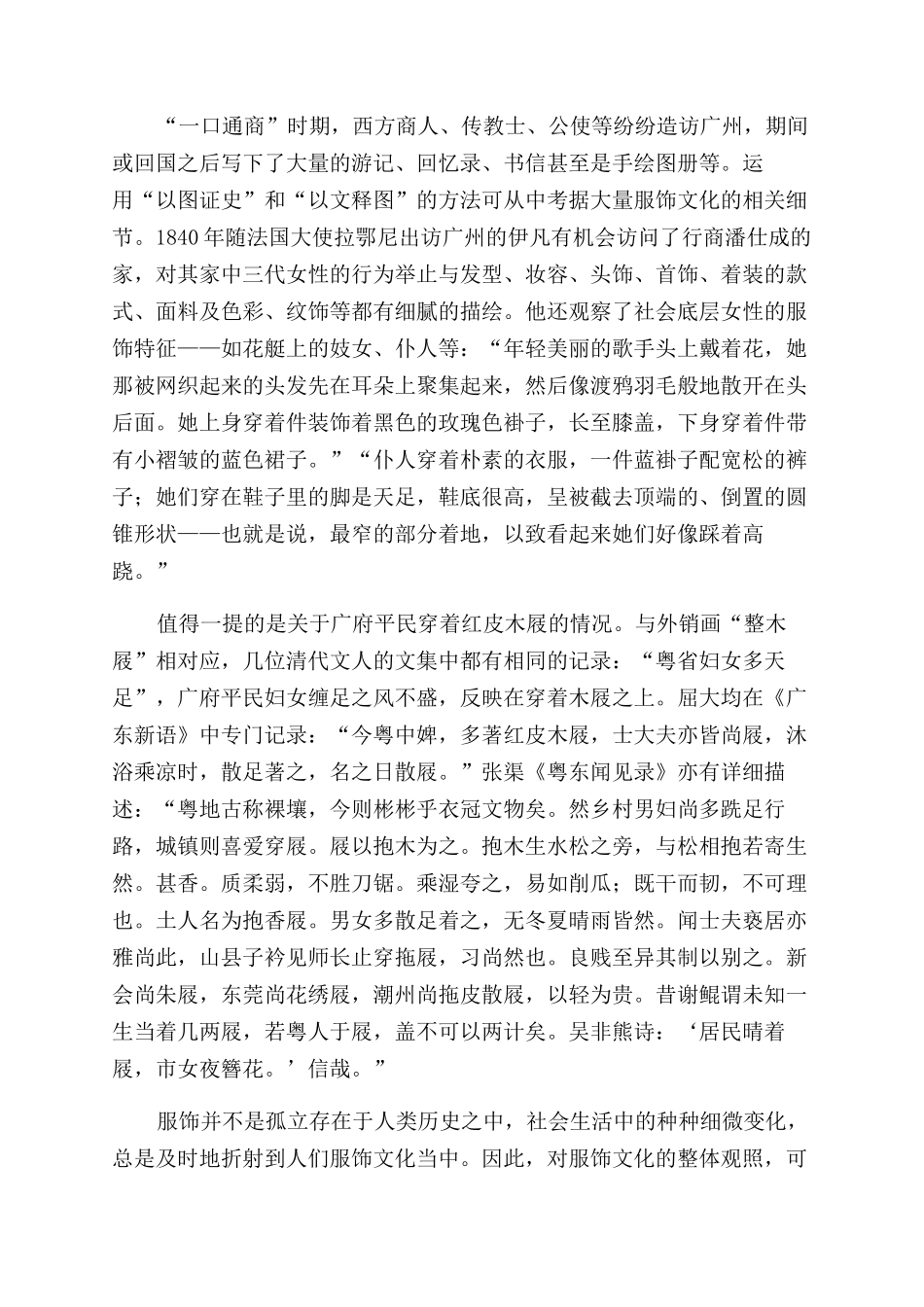服饰讨论的另一个维度作为我国第一代古代服饰文化讨论的学术成果,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讨论》和黄能馥、陈娟娟先生的《中华历代服饰艺术》等,遵循的是文献典籍与考古发掘和传世标本相互补充、比较来进行考证的历史学讨论方法,是对我国服饰文化的进展变化的线性梳理。近年有学者刘瑞璞、陈静洁突破并补充前人“重道轻器”的学术传统,以大批传世实物的数据采集、结构测绘为基础撰写《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探究中华各民族古典服饰结构特性的内在机制。上述学者的讨论跨度横亘上下五千年,以宏观、系统的视野论述服饰进展史,旨在揭示国家民族的服饰文化进展规律。在对中西方对服饰史讨论方法的比较之下,本文试图探讨服饰文化讨论的另一个维度,将中国传统服饰史讨论的镜头聚焦于“一口通商”时期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以及“广府地区”这样一个特定地域,以这一时空范畴内的服饰文化作为讨论的对象,借鉴西方服饰讨论的“整体”视角,将服饰放置到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去探讨而不是孤立起来,通过社会、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分析,来勾勒和诠释中国传统服饰变迁之前的面貌。截取“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府女性服饰史”作为大历史的小切面,有着充分的前提和依据:首先,“一口通商”时期(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即 1757—1842 年)是中国近代化前期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剧烈变迁之前的关键时刻。正如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在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到了仍能保留自身特点,即停止不变状态的最后时刻”。广府作为“一口通商”的口岸地区,是中西经济文化沟通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对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首次冲击,但人们的核心文化心态却依旧保守持旧。这种固守文化传统的心态折射到了对服饰的态度和选择上——即使是作为“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之一的林则徐也认为“夷服太觉不类”。因此,可将这一阶段视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形态得以完整保存的最后时间节点。“一口通商”时期,西方商人、传教士、公使等纷纷造访广州,期间或回国之后写下了大量的游记、回忆录、书信甚至是手绘图册等。运用“以图证史”和“以文释图”的方法可从中考据大量服饰文化的相关细节。1840 年随法国大使拉鄂尼出访广州的伊凡有机会访问了行商潘仕成的家,对其家中三代女性的行为举止与发型、妆容、头饰、首饰、着装的款式、面料及色彩、纹饰等都有细腻的描绘。他还观察了社会底层女性的服饰特征——如花艇上的妓女、仆人等:“年轻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