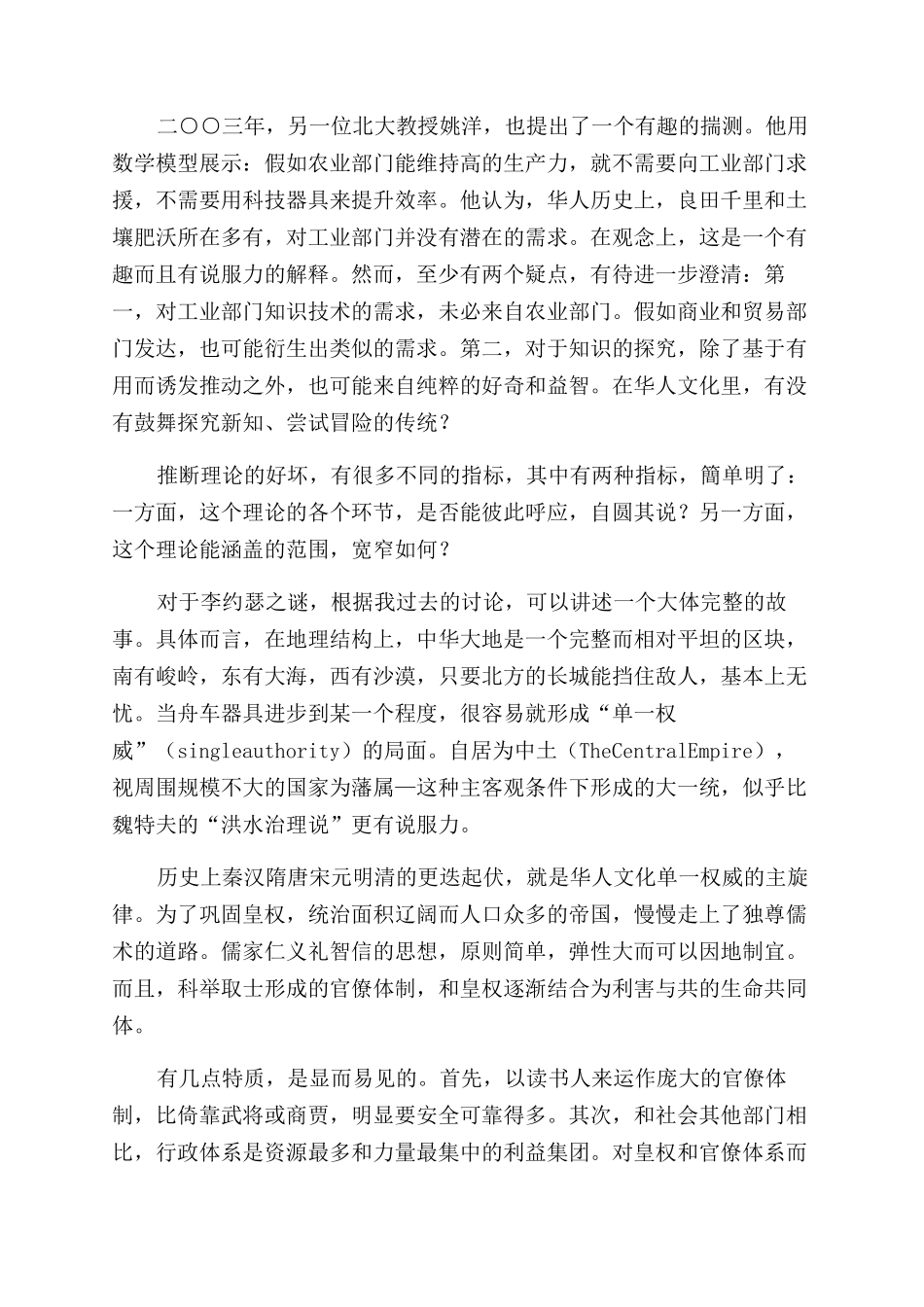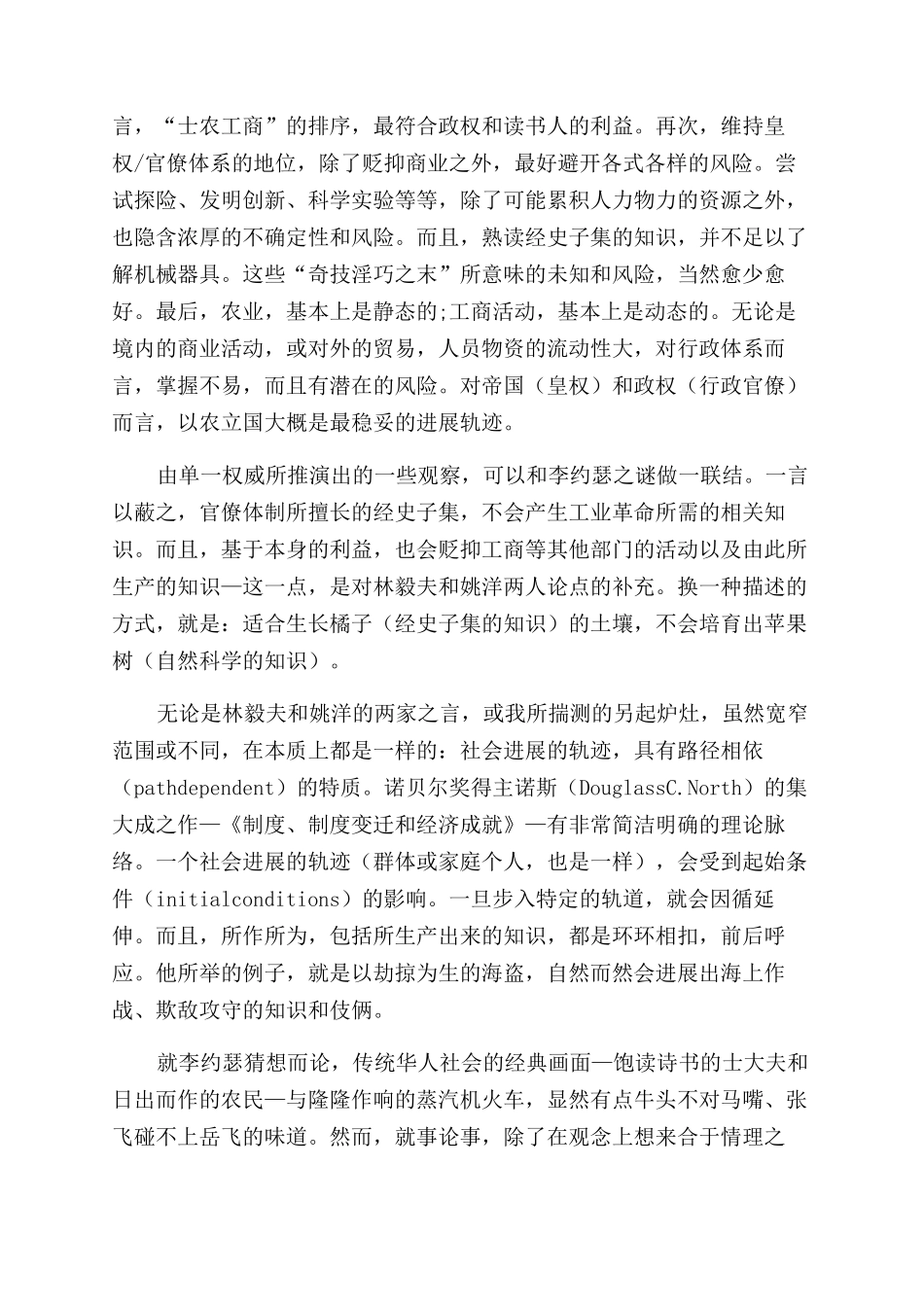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一七五○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科技等都超越西方。可是,从此一落千丈,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为什么呢?他的大哉问,涉及好几个环节,但是可以归纳成一个简单明确的问题: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当初看到这个问题时,觉得有趣,也粗略地看了一些文章。但是,觉得问题本身不好处理—对于任何可能的答案,有谁可以自信十足地回答答案对,或是不对?当有人提出解释时,最多可以增加大家对历史的认识,答案和其他的史实兼容,并不冲突,如此而已!对我而言,智识上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如何“拿证据来”!在试着响应“李约瑟之谜”时,哪些数据能够拿得上台面?除了揣测性的假说之外,有没有信而有征的证据,能直接或间接地呼应谜题和假说?这几年来,这个问题间或会在脑海里出现,琢磨一阵,又悄然遁去。不过,慢慢地,当我把它和其他问题一起联想时,至少在理论上,我认为可以编织出一套说得过去的说辞。所欠缺的,还是信而可征的证据。一九九五年,北大教授林毅夫发表宏文,提出有趣的解读。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培育出一批长于经史子集而短于机械器物的官僚。一方面,他们的知识条件,不足以进展出蒸汽机和铁路火车等;另一方面,官僚体系里,站在捍卫本身利益的立场,他们也不会鼓舞,甚至会排斥和“圣人之学”相左的知识。直觉上,这种解释脉络清楚,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值得进一步探究:首先,除了官僚体系(士)之外,社会上还有农工商等其他部门;官僚体系生产句读之学,其他部门难道不能有各自的趋舍好尚吗?其次,令人好奇而且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华人历史上的官僚,会变成经史子集的书虫?假如是因为科举取士、独尊儒术,也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走上独尊儒术的道路?二○○三年,另一位北大教授姚洋,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揣测。他用数学模型展示:假如农业部门能维持高的生产力,就不需要向工业部门求援,不需要用科技器具来提升效率。他认为,华人历史上,良田千里和土壤肥沃所在多有,对工业部门并没有潜在的需求。在观念上,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至少有两个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第一,对工业部门知识技术的需求,未必来自农业部门。假如商业和贸易部门发达,也可能衍生出类似的需求。第二,对于知识的探究,除了基于有用而诱发推动之外,也可能来自纯粹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