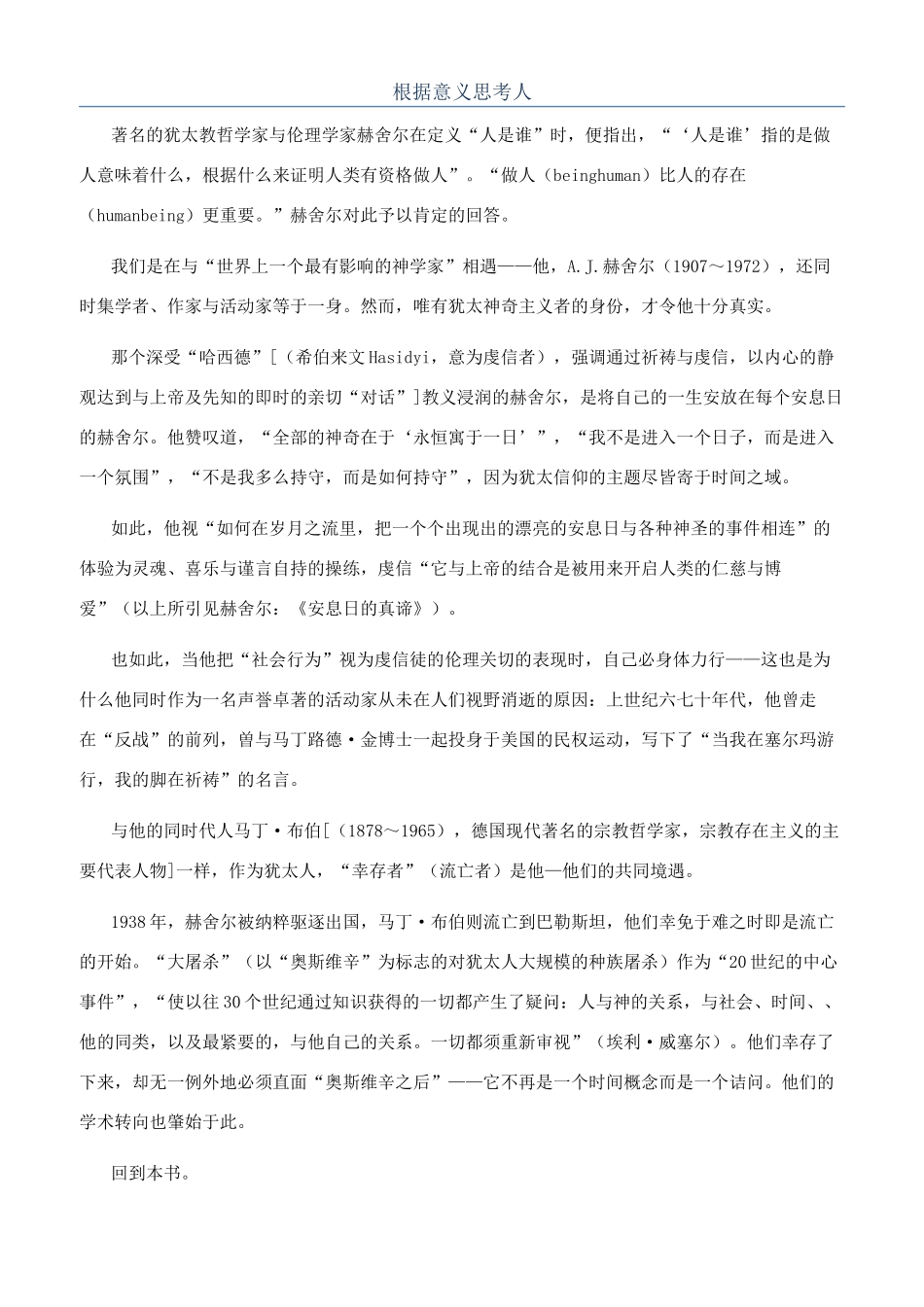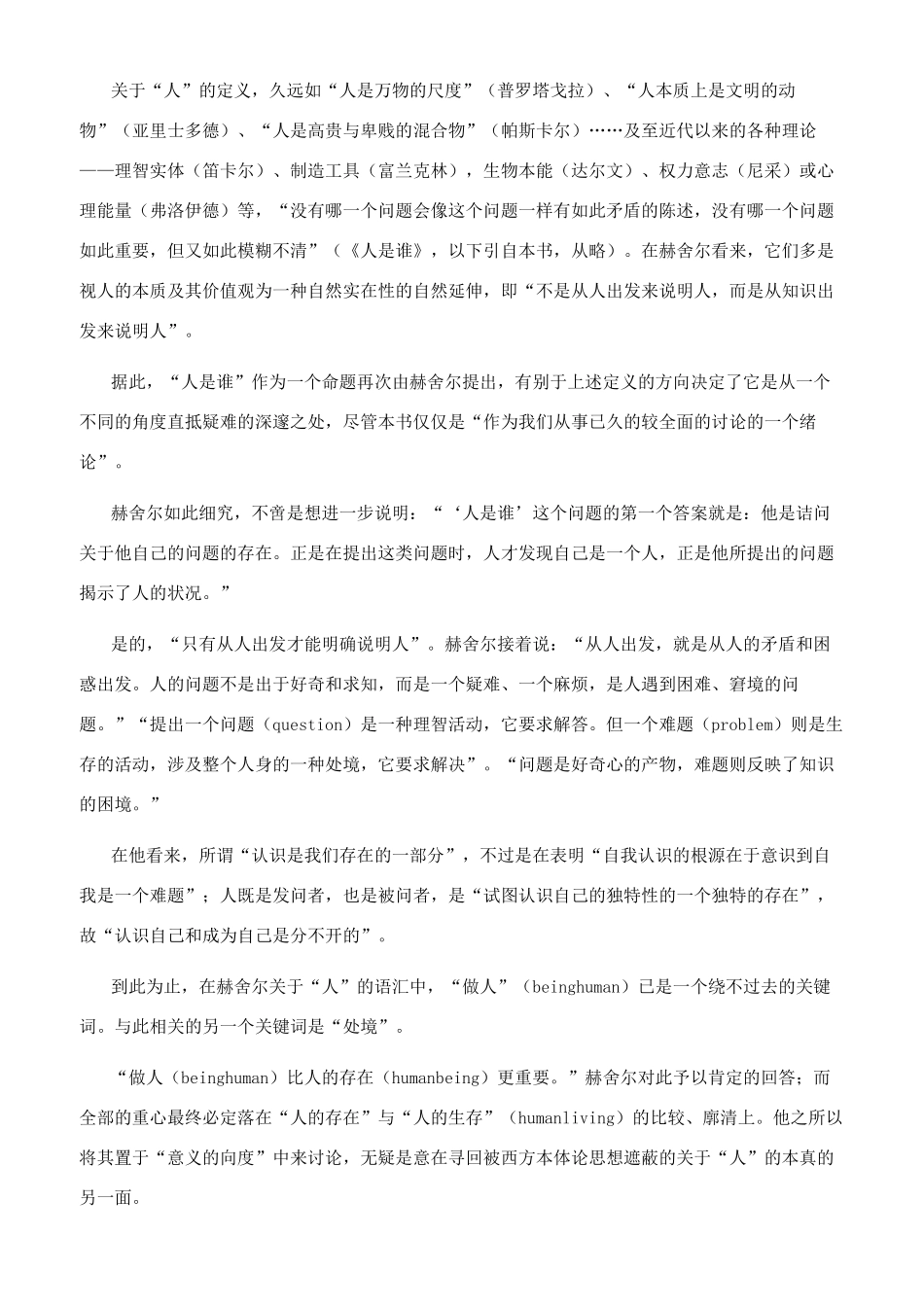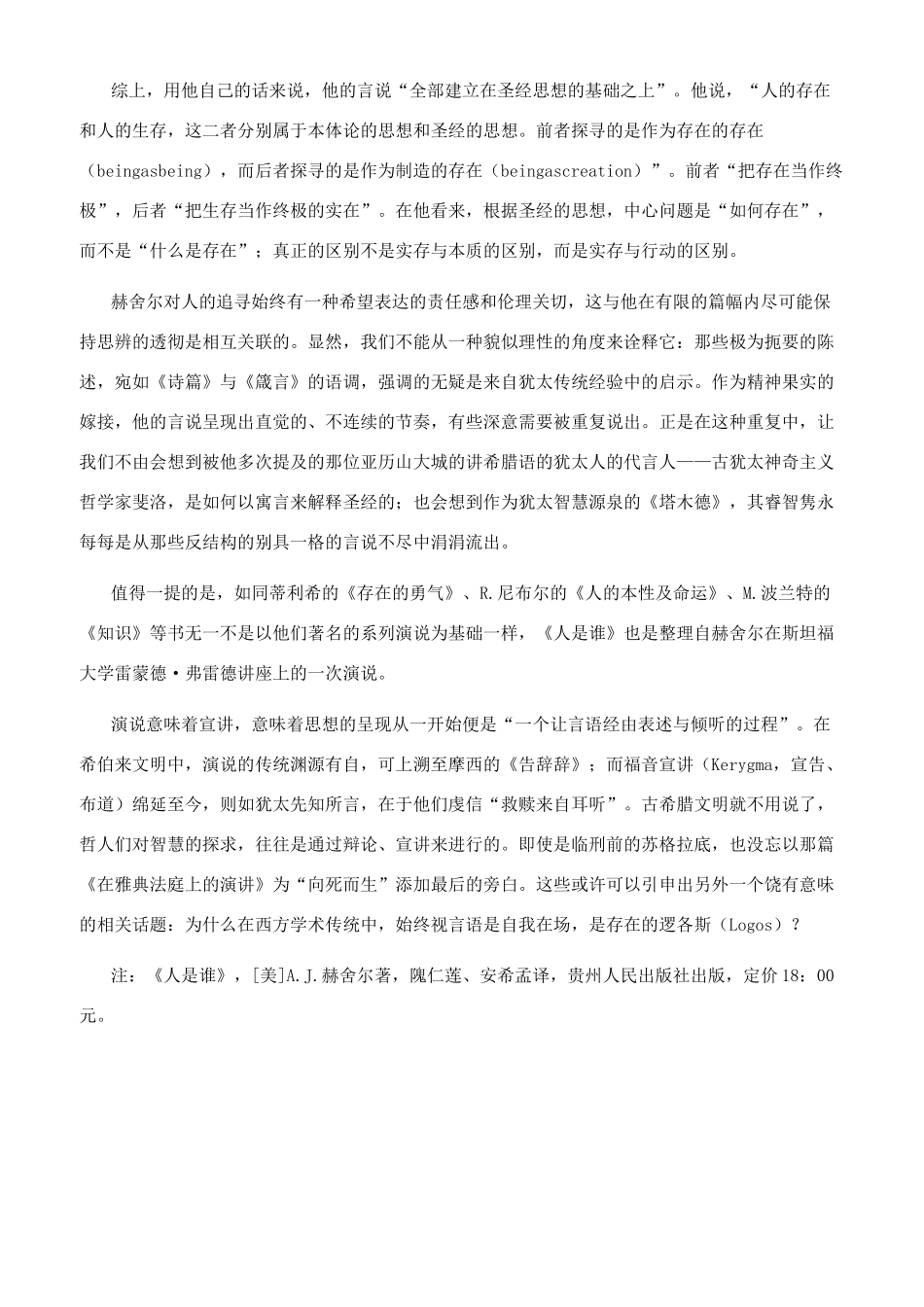根据意义思考人著名的犹太教哲学家与伦理学家赫舍尔在定义“人是谁”时,便指出,“‘人是谁’指的是做人意味着什么,根据什么来证明人类有资格做人”。“做人(beinghuman)比人的存在(humanbeing)更重要。”赫舍尔对此予以肯定的回答。我们是在与“世界上一个最有影响的神学家”相遇——他,A.J.赫舍尔(1907~1972),还同时集学者、作家与活动家等于一身。然而,唯有犹太神奇主义者的身份,才令他十分真实。那个深受“哈西德”[(希伯来文 Hasidyi,意为虔信者),强调通过祈祷与虔信,以内心的静观达到与上帝及先知的即时的亲切“对话”]教义浸润的赫舍尔,是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每个安息日的赫舍尔。他赞叹道,“全部的神奇在于‘永恒寓于一日’”,“我不是进入一个日子,而是进入一个氛围”,“不是我多么持守,而是如何持守”,因为犹太信仰的主题尽皆寄于时间之域。如此,他视“如何在岁月之流里,把一个个出现出的漂亮的安息日与各种神圣的事件相连”的体验为灵魂、喜乐与谨言自持的操练,虔信“它与上帝的结合是被用来开启人类的仁慈与博爱”(以上所引见赫舍尔:《安息日的真谛》)。也如此,当他把“社会行为”视为虔信徒的伦理关切的表现时,自己必身体力行——这也是为什么他同时作为一名声誉卓著的活动家从未在人们视野消逝的原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曾走在“反战”的前列,曽与马丁路德·金博士一起投身于美国的民权运动,写下了“当我在塞尔玛游行,我的脚在祈祷”的名言。与他的同时代人马丁·布伯[(1878~1965),德国现代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样,作为犹太人,“幸存者”(流亡者)是他—他们的共同境遇。1938 年,赫舍尔被纳粹驱逐出国,马丁·布伯则流亡到巴勒斯坦,他们幸免于难之时即是流亡的开始。“大屠杀”(以“奥斯维辛”为标志的对犹太人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作为“20 世纪的中心事件”,“使以往 30 个世纪通过知识获得的一切都产生了疑问:人与神的关系,与社会、时间、、他的同类,以及最紧要的,与他自己的关系。一切都须重新审视”(埃利·威塞尔)。他们幸存了下来,却无一例外地必须直面“奥斯维辛之后”——它不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诘问。他们的学术转向也肇始于此。回到本书。关于“人”的定义,久远如“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人本质上是文明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人是高贵与卑贱的混合物”(帕斯卡尔)……及至近代以来的各种理论——理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