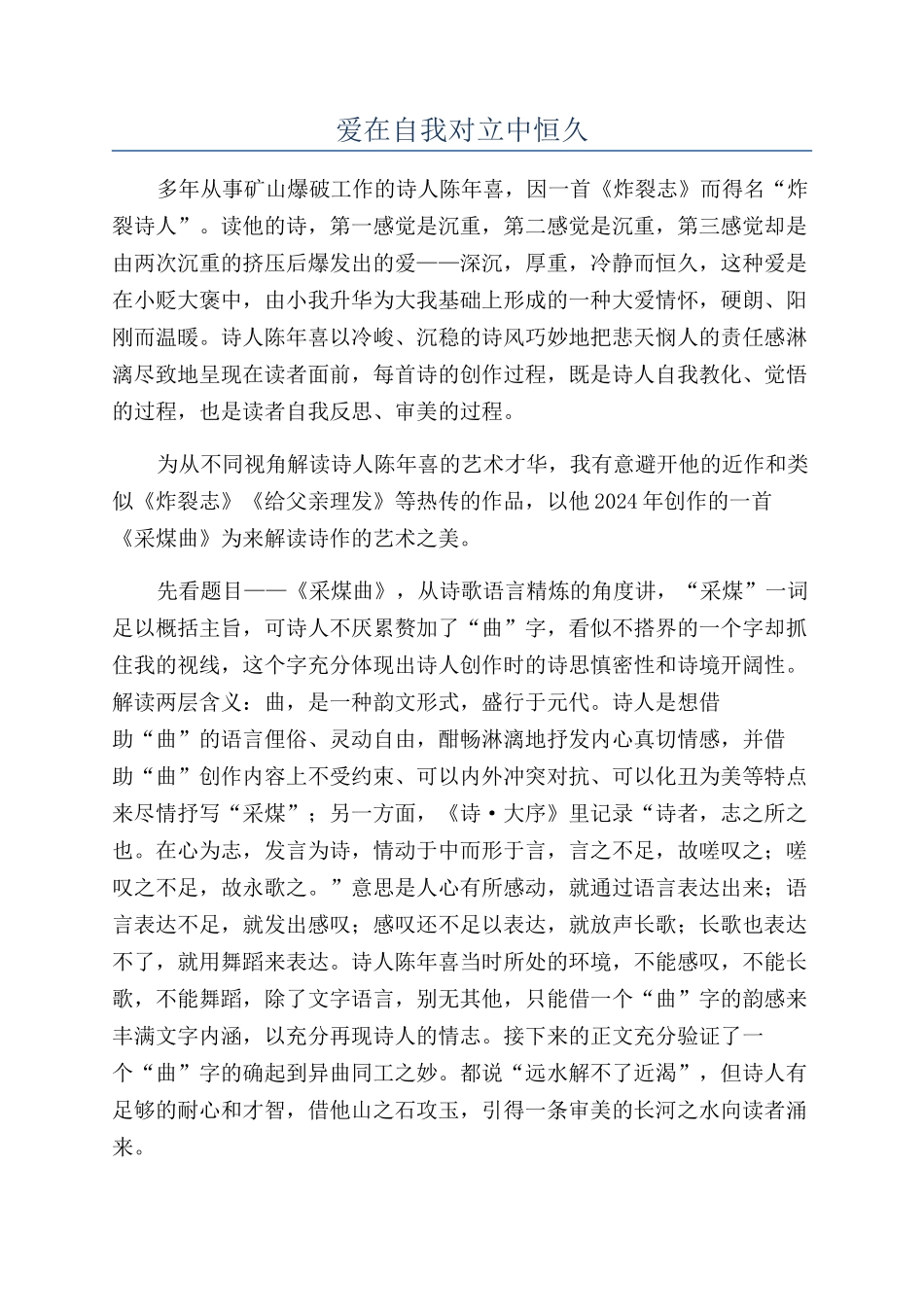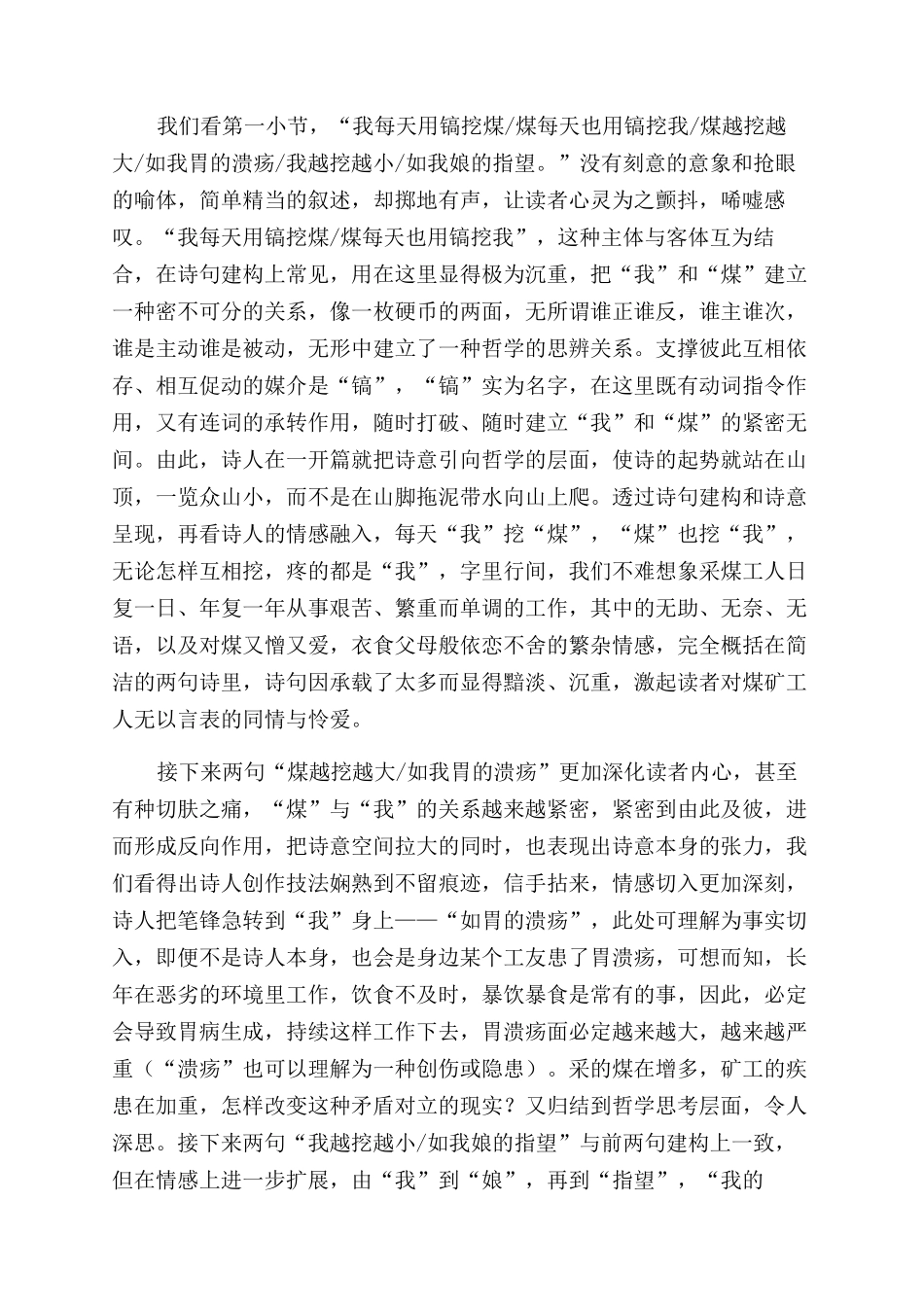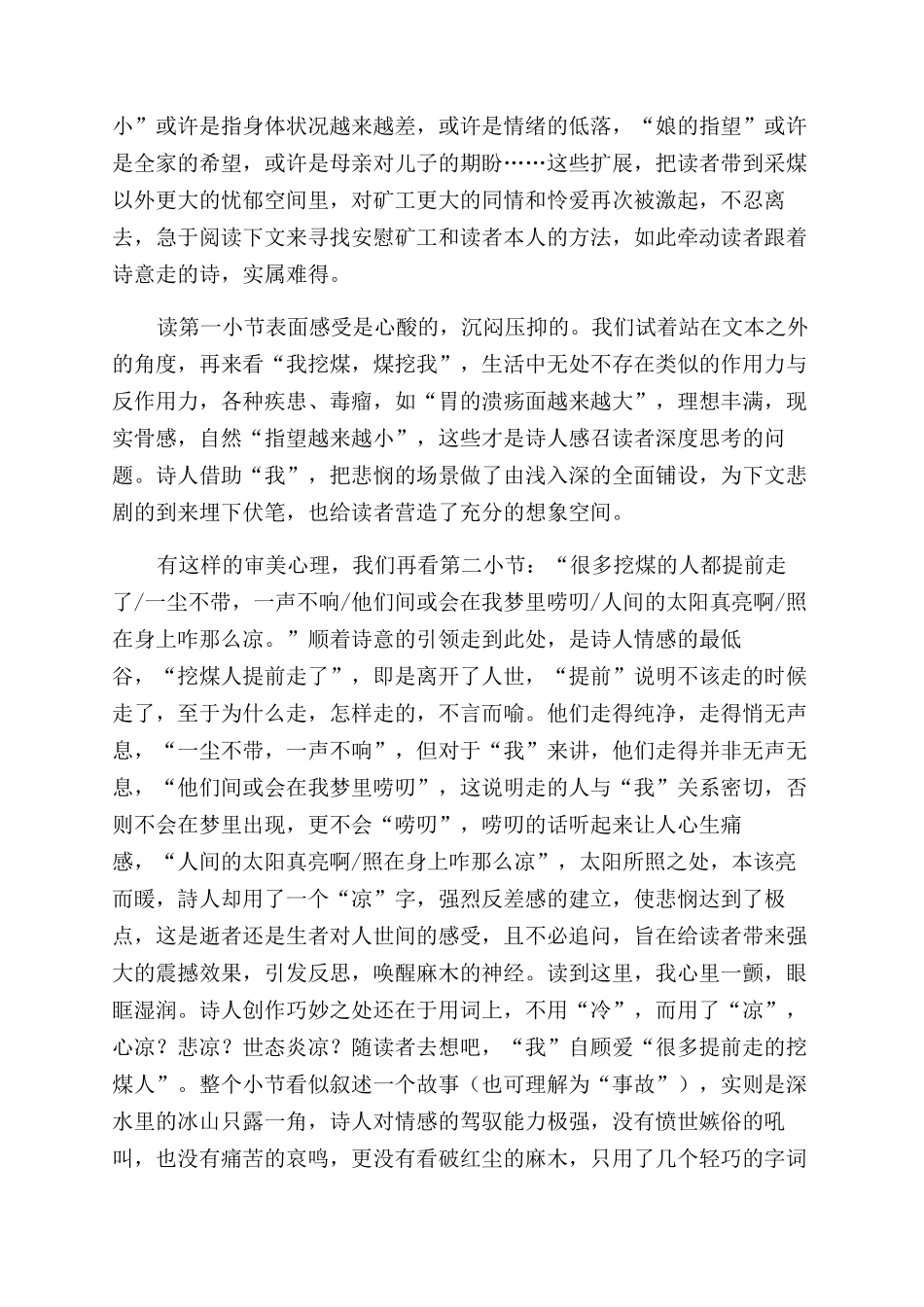爱在自我对立中恒久多年从事矿山爆破工作的诗人陈年喜,因一首《炸裂志》而得名“炸裂诗人”。读他的诗,第一感觉是沉重,第二感觉是沉重,第三感觉却是由两次沉重的挤压后爆发出的爱——深沉,厚重,冷静而恒久,这种爱是在小贬大褒中,由小我升华为大我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大爱情怀,硬朗、阳刚而温暖。诗人陈年喜以冷峻、沉稳的诗风巧妙地把悲天悯人的责任感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每首诗的创作过程,既是诗人自我教化、觉悟的过程,也是读者自我反思、审美的过程。为从不同视角解读诗人陈年喜的艺术才华,我有意避开他的近作和类似《炸裂志》《给父亲理发》等热传的作品,以他 2024 年创作的一首《采煤曲》为来解读诗作的艺术之美。先看题目——《采煤曲》,从诗歌语言精炼的角度讲,“采煤”一词足以概括主旨,可诗人不厌累赘加了“曲”字,看似不搭界的一个字却抓住我的视线,这个字充分体现出诗人创作时的诗思慎密性和诗境开阔性。解读两层含义:曲,是一种韵文形式,盛行于元代。诗人是想借助“曲”的语言俚俗、灵动自由,酣畅淋漓地抒发内心真切情感,并借助“曲”创作内容上不受约束、可以内外冲突对抗、可以化丑为美等特点来尽情抒写“采煤”;另一方面,《诗·大序》里记录“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意思是人心有所感动,就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表达不足,就发出感叹;感叹还不足以表达,就放声长歌;长歌也表达不了,就用舞蹈来表达。诗人陈年喜当时所处的环境,不能感叹,不能长歌,不能舞蹈,除了文字语言,别无其他,只能借一个“曲”字的韵感来丰满文字内涵,以充分再现诗人的情志。接下来的正文充分验证了一个“曲”字的确起到异曲同工之妙。都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但诗人有足够的耐心和才智,借他山之石攻玉,引得一条审美的长河之水向读者涌来。我们看第一小节,“我每天用镐挖煤/煤每天也用镐挖我/煤越挖越大/如我胃的溃疡/我越挖越小/如我娘的指望。”没有刻意的意象和抢眼的喻体,简单精当的叙述,却掷地有声,让读者心灵为之颤抖,唏嘘感叹。“我每天用镐挖煤/煤每天也用镐挖我”,这种主体与客体互为结合,在诗句建构上常见,用在这里显得极为沉重,把“我”和“煤”建立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所谓谁正谁反,谁主谁次,谁是主动谁是被动,无形中建立了一种哲学的思辨关系。支撑彼此互相依存、相互促动的媒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