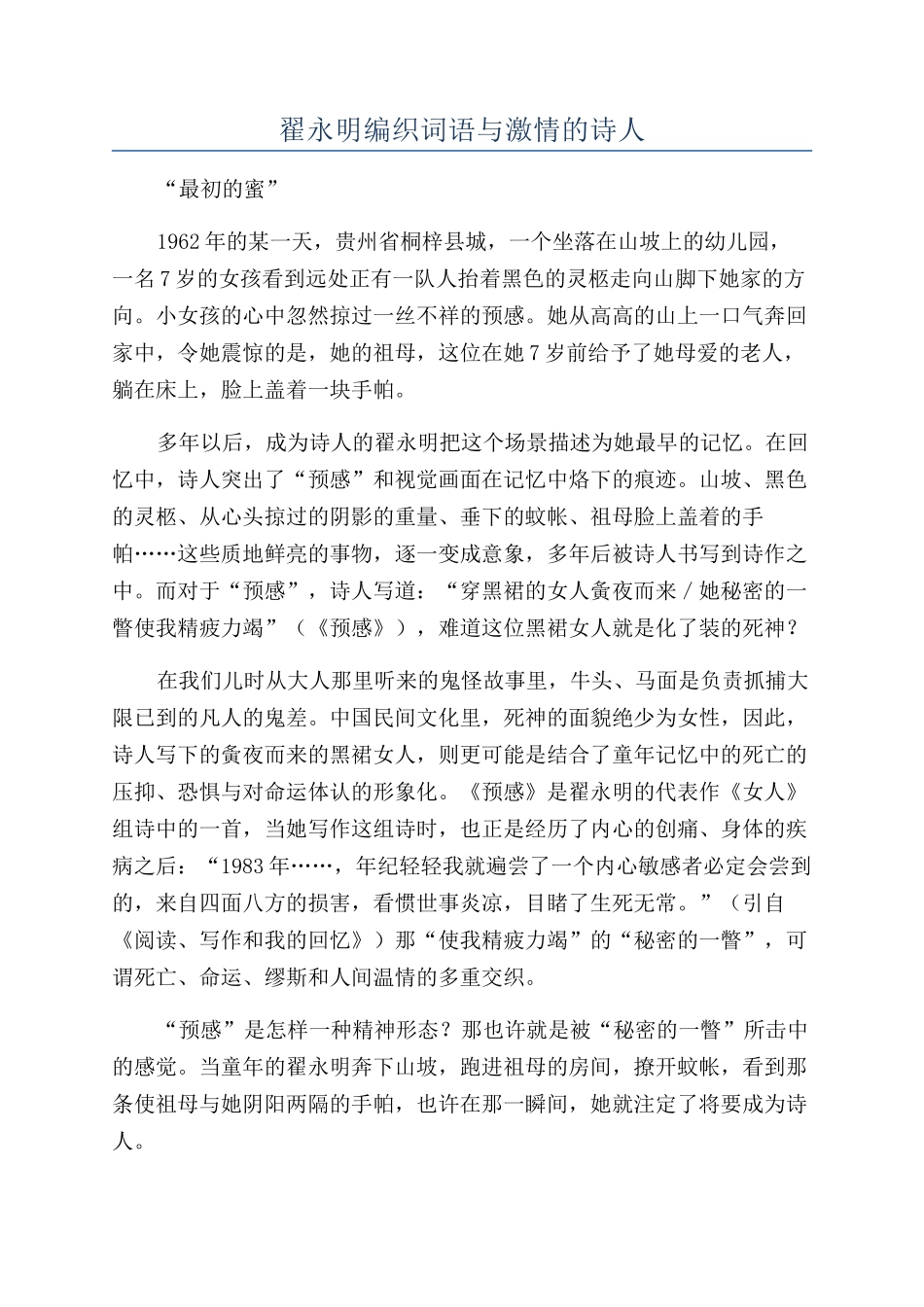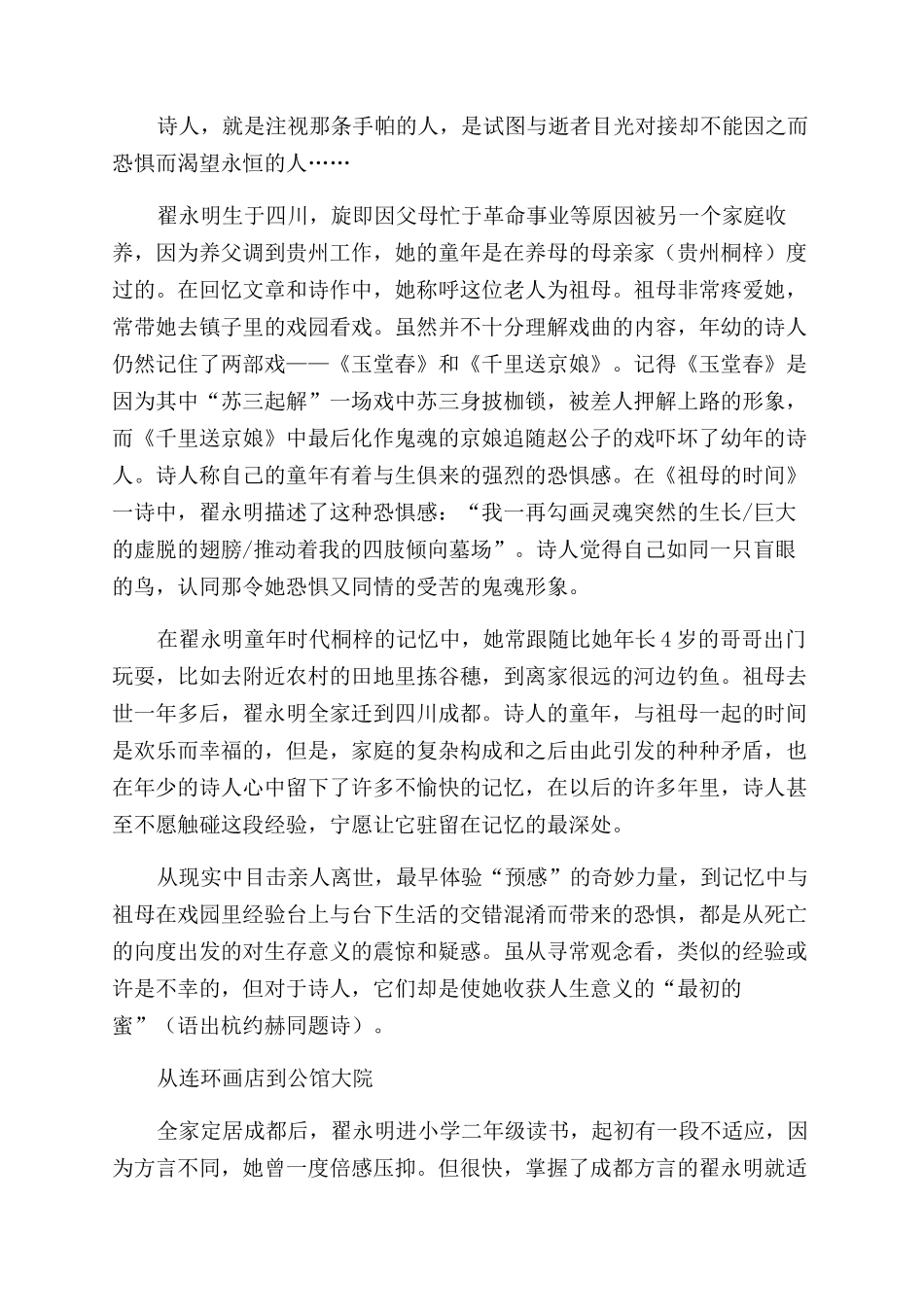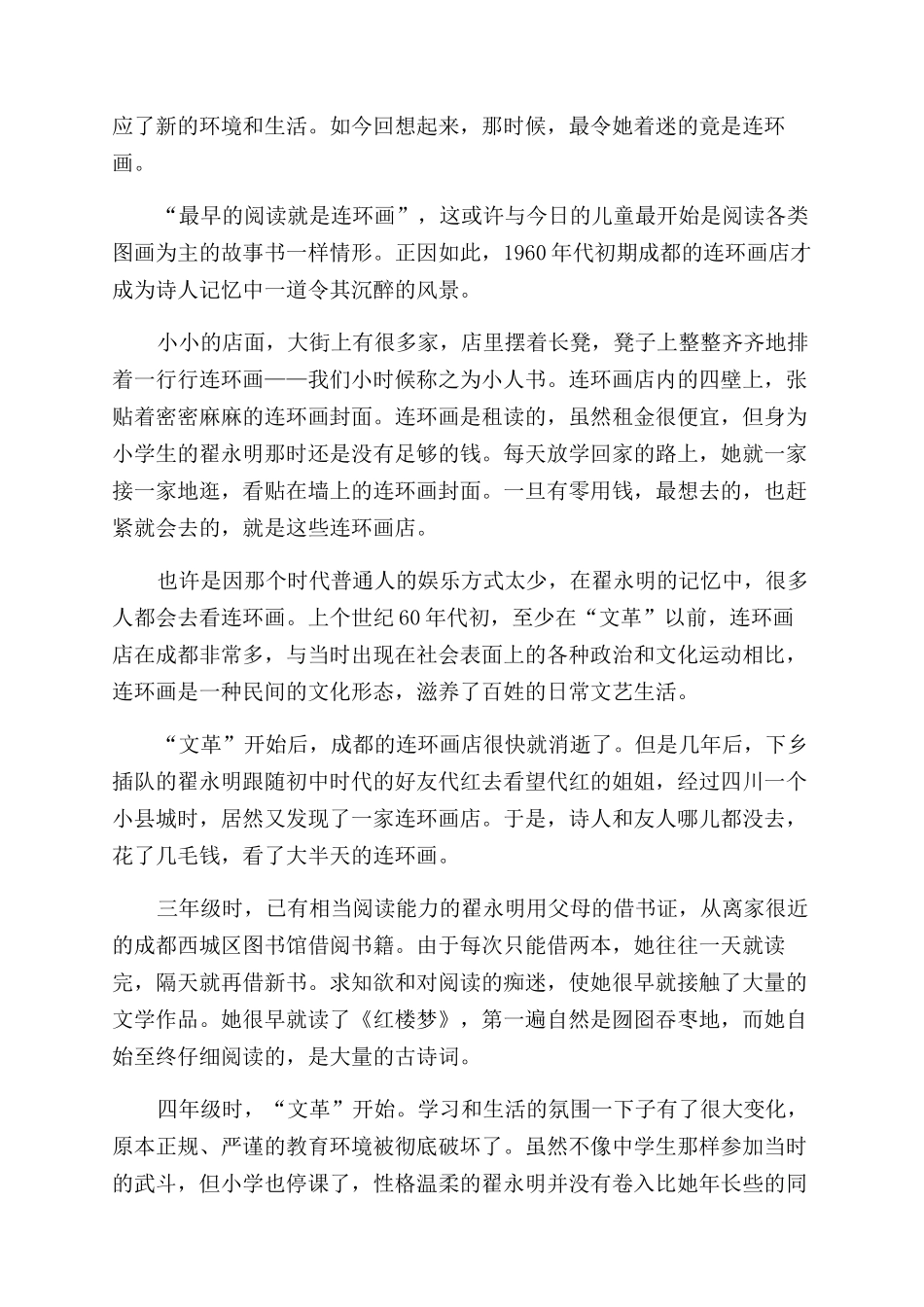翟永明编织词语与激情的诗人“最初的蜜”1962 年的某一天,贵州省桐梓县城,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幼儿园,一名 7 岁的女孩看到远处正有一队人抬着黑色的灵柩走向山脚下她家的方向。小女孩的心中忽然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她从高高的山上一口气奔回家中,令她震惊的是,她的祖母,这位在她 7 岁前给予了她母爱的老人,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手帕。多年以后,成为诗人的翟永明把这个场景描述为她最早的记忆。在回忆中,诗人突出了“预感”和视觉画面在记忆中烙下的痕迹。山坡、黑色的灵柩、从心头掠过的阴影的重量、垂下的蚊帐、祖母脸上盖着的手帕……这些质地鲜亮的事物,逐一变成意象,多年后被诗人书写到诗作之中。而对于“预感”,诗人写道:“穿黑裙的女人夤夜而来/她秘密的一瞥使我精疲力竭”(《预感》),难道这位黑裙女人就是化了装的死神?在我们儿时从大人那里听来的鬼怪故事里,牛头、马面是负责抓捕大限已到的凡人的鬼差。中国民间文化里,死神的面貌绝少为女性,因此,诗人写下的夤夜而来的黑裙女人,则更可能是结合了童年记忆中的死亡的压抑、恐惧与对命运体认的形象化。《预感》是翟永明的代表作《女人》组诗中的一首,当她写作这组诗时,也正是经历了内心的创痛、身体的疾病之后:“1983 年……,年纪轻轻我就遍尝了一个内心敏感者必定会尝到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损害,看惯世事炎凉,目睹了生死无常。”(引自《阅读、写作和我的回忆》)那“使我精疲力竭”的“秘密的一瞥”,可谓死亡、命运、缪斯和人间温情的多重交织。“预感”是怎样一种精神形态?那也许就是被“秘密的一瞥”所击中的感觉。当童年的翟永明奔下山坡,跑进祖母的房间,撩开蚊帐,看到那条使祖母与她阴阳两隔的手帕,也许在那一瞬间,她就注定了将要成为诗人。诗人,就是注视那条手帕的人,是试图与逝者目光对接却不能因之而恐惧而渴望永恒的人……翟永明生于四川,旋即因父母忙于革命事业等原因被另一个家庭收养,因为养父调到贵州工作,她的童年是在养母的母亲家(贵州桐梓)度过的。在回忆文章和诗作中,她称呼这位老人为祖母。祖母非常疼爱她,常带她去镇子里的戏园看戏。虽然并不十分理解戏曲的内容,年幼的诗人仍然记住了两部戏——《玉堂春》和《千里送京娘》。记得《玉堂春》是因为其中“苏三起解”一场戏中苏三身披枷锁,被差人押解上路的形象,而《千里送京娘》中最后化作鬼魂的京娘追随赵公子的戏吓坏了幼年的诗人。诗人称自己的童年有着与生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