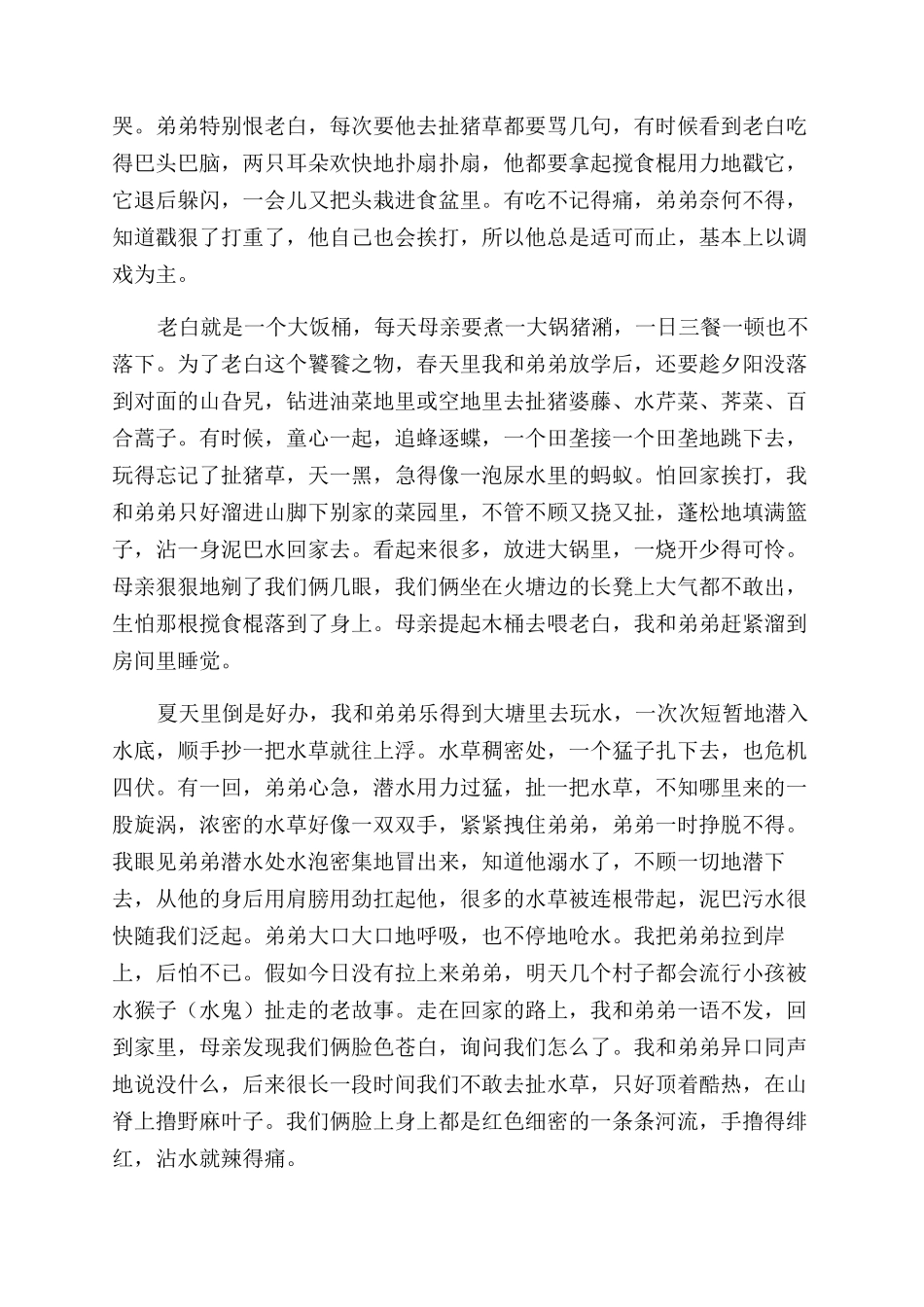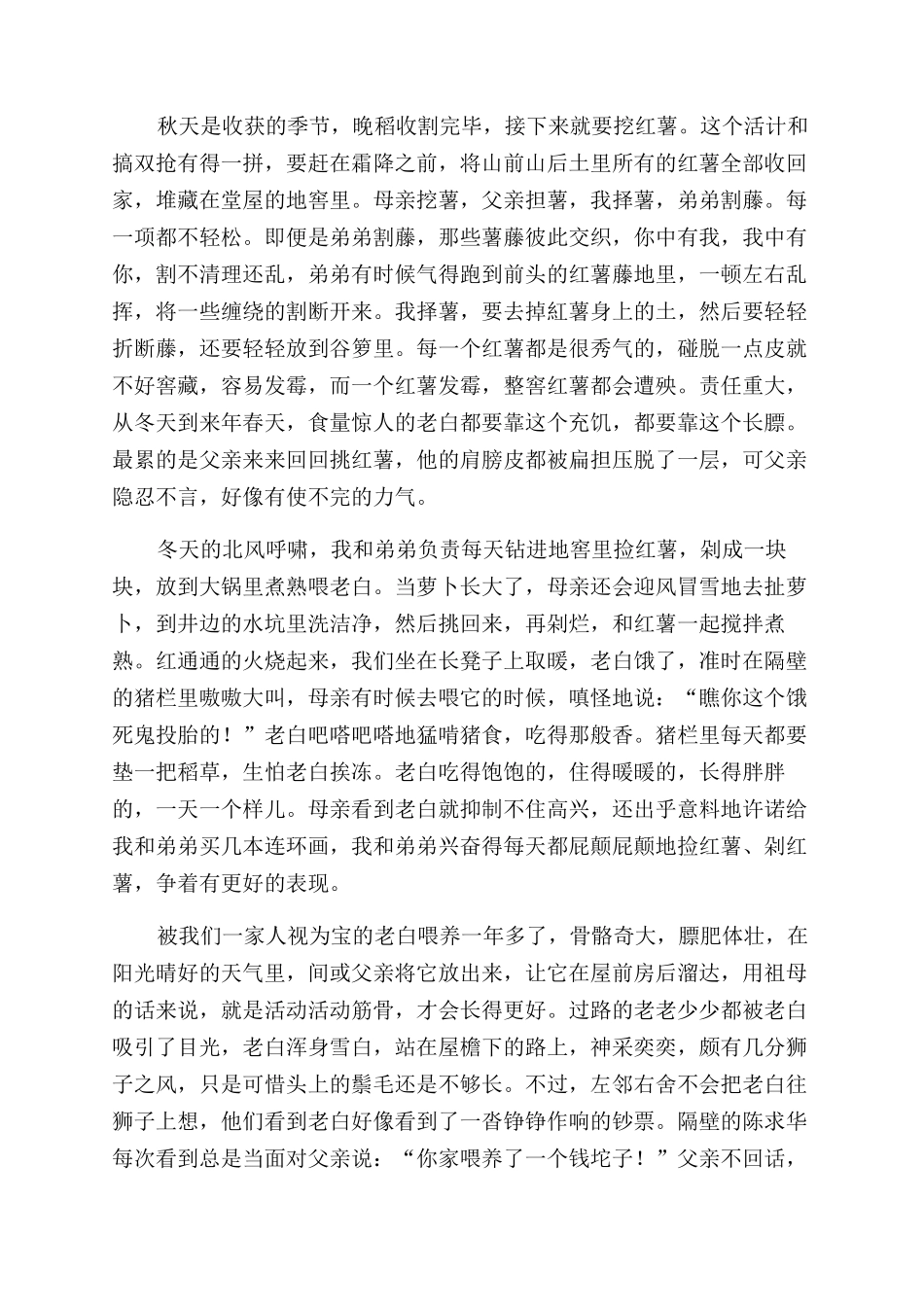血色馈赠的苦夏袁道一,男,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少年文艺》《散文选刊》《散文》《湖南文学》《小溪流》《文艺报》《湖南日报》等,著有散文集《低处的声嚣》。“何得了,老白两天冇吃一口潲了。”“明天还不呷,就去找唐兽医来看看。”隔壁房间里母亲和父亲深更半夜睡不着,忧心忡忡地在说话。我被尿胀醒,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的说话声,拉开房门。因为害怕,我站在门槛上朝外撒尿,一阵哗哗响。我拉上短裤子,神志清醒了很多,朝远方望了一眼,田里的稻禾正在抓紧灌浆结籽。更远的是天空,天空上挂着几颗疲乏的星子。我转过身来,突然听见后背山上的黑鸦发出一声嘹亮的啼叫,刺破幽深的夜色。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一股强烈的不祥之感涌上心头。奶奶常常对我说,后背山上的黑鸦夜半突兀叫一声,村子里就会有灾祸降临,或者是有老人要走了。想到这,我背脊发凉,好像黑鸦阴沉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回到床上,我辗转反侧,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看着蓝印花布做的蚊帐发愣。隔壁房间里的父母还在唉声叹气,母亲在发愁,父亲在安慰。可我还是从父亲安慰的话语里听出了不安和担忧,睡在另一头的弟弟倒是睡得香甜,细小的鼾声节奏分明,韵味深长。老白是家里的那条大白猪,老白是家里的宝。我和弟弟的学费要靠它,一年到头吃的油要靠它,春耕生产的农资化肥要靠它,人情往来的费用要靠它。老白是一条幸福的猪,至少我和弟弟是这样认为的。家里的田少,尽管种双季稻还是顾不住吃,可哪怕再没有米,每夜给老白煮猪潲,母亲都会很大方地倒进去半筒米。弟弟每次看到都要努起嘴巴,觉得母亲对老白比对他还好。去年春节前夕爆米花的进村,家家户户的孩子去爆米花,弟弟捧一升米去,在路上生生被母亲夺走,全然不顾弟弟的号啕大哭。弟弟特别恨老白,每次要他去扯猪草都要骂几句,有时候看到老白吃得巴头巴脑,两只耳朵欢快地扑扇扑扇,他都要拿起搅食棍用力地戳它,它退后躲闪,一会儿又把头栽进食盆里。有吃不记得痛,弟弟奈何不得,知道戳狠了打重了,他自己也会挨打,所以他总是适可而止,基本上以调戏为主。老白就是一个大饭桶,每天母亲要煮一大锅猪潲,一日三餐一顿也不落下。为了老白这个饕餮之物,春天里我和弟弟放学后,还要趁夕阳没落到对面的山旮旯,钻进油菜地里或空地里去扯猪婆藤、水芹菜、荠菜、百合蒿子。有时候,童心一起,追蜂逐蝶,一个田垄接一个田垄地跳下去,玩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