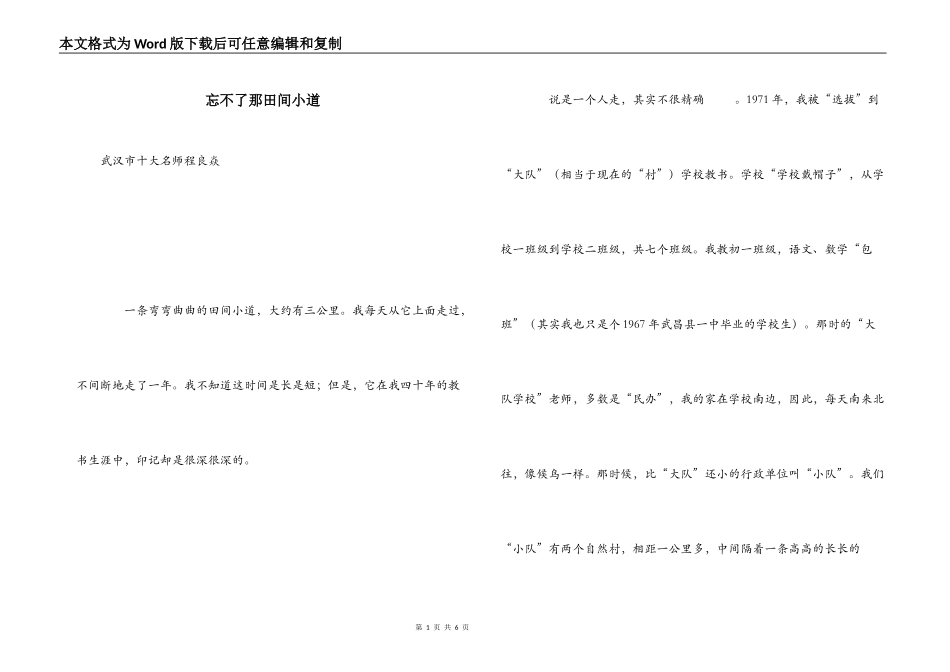第1页共6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忘不了那田间小道武汉市十大名师程良焱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大约有三公里。我每天从它上面走过,不间断地走了一年。我不知道这时间是长是短;但是,它在我四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印记却是很深很深的。说是一个人走,其实不很精确。1971年,我被“选拔”到“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学校教书。学校“学校戴帽子”,从学校一班级到学校二班级,共七个班级。我教初一班级,语文、数学“包班”(其实我也只是个1967年武昌县一中毕业的学校生)。那时的“大队学校”老师,多数是“民办”,我的家在学校南边,因此,每天南来北往,像候鸟一样。那时候,比“大队”还小的行政单位叫“小队”。我们“小队”有两个自然村,相距一公里多,中间隔着一条高高的长长的第2页共6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岭”,乡亲们称为“长岭”。我家住在“长岭”东边;还有一位学校同事,叫朱功淮,大家喊他“朱老师”,住在“长岭”的西边。我们是一个“小队”的人,自然比一般的同事多了一层关系。说起朱老师,这个人可真不简洁。他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中专学历,“公办”老师,这在当时的“大队”学校,那是少之又少了。他在一所初级中学教过几年生物,又在一所规格很高的学校长期从事毕业班数学教学,教学效果很好,名气很大。老师“下放”,他从镇上的学校回到家乡大队的学校,教学校二班级数学。更令人称道的是,他虽然是一位数学老师,语文功底却很深厚,他曾经长期购买和阅读上世纪六十年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胸中“藏书”许多,还写得一笔好文章;而且字也写得不错,毛笔书法在小天地里也算是出类拔萃了。每天放学后,我和朱老师便相约一起回家。一个三十岁开外,一第3页共6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个二十岁不到;一个是教学阅历丰富的“老羔子”,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贩子”;一个虽然说不上“学富五车”,却也学问丰富,一个牵强读完了学校,算是了解一些常识。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田埂上的路太窄),不舍不弃,不紧不慢。出校门,向南,穿过一片稻田,跨过一条小巷,走了大约一半的路程,要分路了。(工作体会.9xwang.com)我朝左,顺着“长岭”往南走,然后转向东边回家;他向右,穿过一畈农田,绕过一片树林,就到家了。可是,我们几乎很少在这里分手。先是邀请一番,谦让一番,后来则是习惯成自然,谁走在前面,就朝着自己回家的相反的一条小路走,始终走到非分路不行才各自朝着自己的家走去。这样,每次总有一个人要多走一里多路。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东拉西扯,几乎无所不谈。现第4页共6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在回忆起来,说得最多的主要是两方面内容,一是学问,二是方法。古今中外,文史哲经,数理化生,什么学问都讲;学习学问、积累学问的方法,教书的方法,也是我们常常谈到的内容。一般状况下,都是他讲我听;也有相互争论乃至争辩的时候。我很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是一期《中华活页文选》,他让我带回去读一读。那上面有一篇古人的什么文章,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最终有一首林则徐的《即目》诗,却印象很深刻:“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眼前直觉群山小,排列儿孙未得名。”这是清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林则徐赴任云南乡试正考官,途中经贵州境时写的一首七律。之所以至今还记得,一是我当时认为,诗的最终两句写得很通俗,很生动,很有味道;二是当天晚上我回家以后背了几遍。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说到他自己晚上读书的事,他说,有些文章读起来很有味,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听见鸡叫了。他还顺便说到了古人读书“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第5页共6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和复制这两个典故,觉得很新奇、很刺激。渐渐地,我开头跟着他读一些东西。那时的读物很少,因此,凡是我们能够找到的,都实行“拿来主义”的态度。记得当时学校订有《人民日报》和《湖北日报》;还有两本杂志,都是上海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