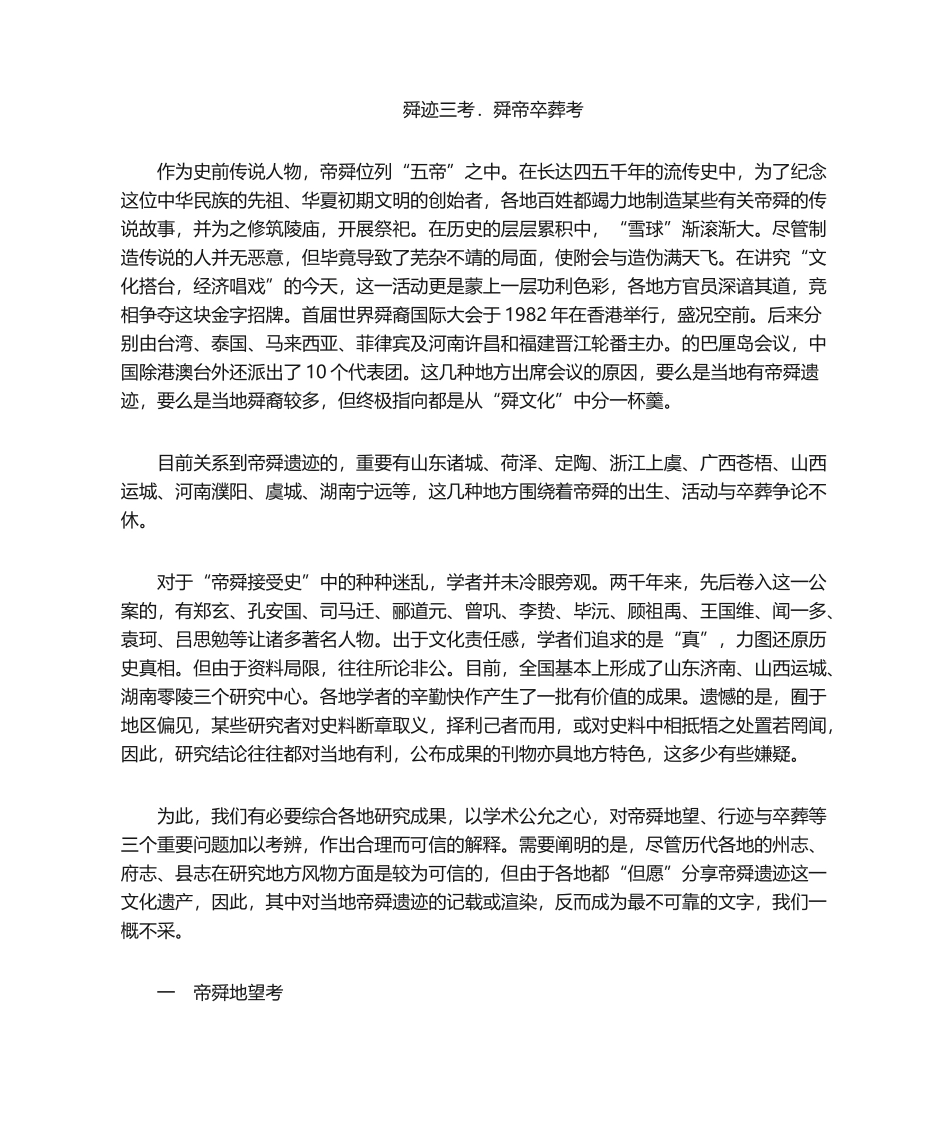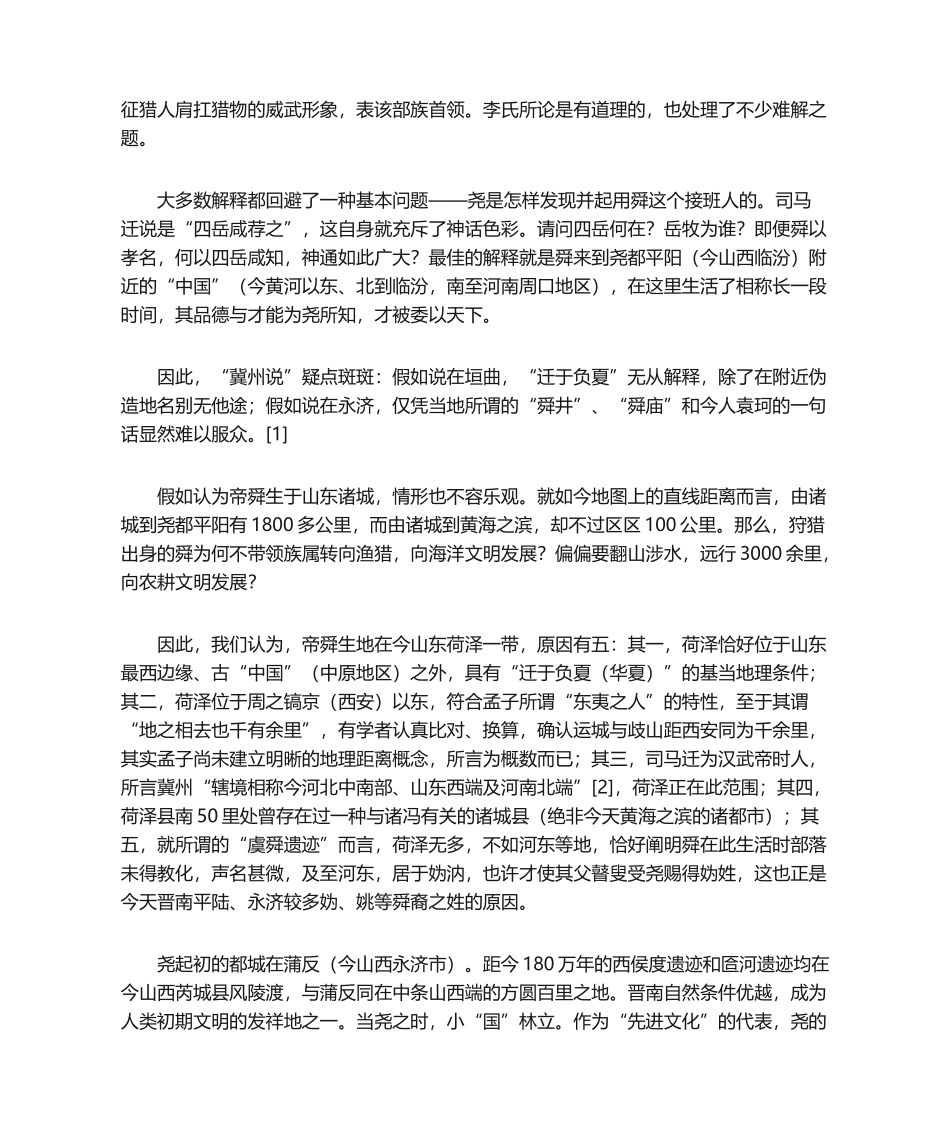舜迹三考.舜帝卒葬考作为史前传说人物,帝舜位列“五帝”之中。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流传史中,为了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先祖、华夏初期文明的创始者,各地百姓都竭力地制造某些有关帝舜的传说故事,并为之修筑陵庙,开展祭祀。在历史的层层累积中,“雪球”渐滚渐大。尽管制造传说的人并无恶意,但毕竟导致了芜杂不靖的局面,使附会与造伪满天飞。在讲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今天,这一活动更是蒙上一层功利色彩,各地方官员深谙其道,竞相争夺这块金字招牌。首届世界舜裔国际大会于1982年在香港举行,盛况空前。后来分别由台湾、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河南许昌和福建晋江轮番主办。的巴厘岛会议,中国除港澳台外还派出了10个代表团。这几种地方出席会议的原因,要么是当地有帝舜遗迹,要么是当地舜裔较多,但终极指向都是从“舜文化”中分一杯羹。目前关系到帝舜遗迹的,重要有山东诸城、荷泽、定陶、浙江上虞、广西苍梧、山西运城、河南濮阳、虞城、湖南宁远等,这几种地方围绕着帝舜的出生、活动与卒葬争论不休。对于“帝舜接受史”中的种种迷乱,学者并未冷眼旁观。两千年来,先后卷入这一公案的,有郑玄、孔安国、司马迁、郦道元、曾巩、李贽、毕沅、顾祖禹、王国维、闻一多、袁珂、吕思勉等让诸多著名人物。出于文化责任感,学者们追求的是“真”,力图还原历史真相。但由于资料局限,往往所论非公。目前,全国基本上形成了山东济南、山西运城、湖南零陵三个研究中心。各地学者的辛勤快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遗憾的是,囿于地区偏见,某些研究者对史料断章取义,择利己者而用,或对史料中相抵牾之处置若罔闻,因此,研究结论往往都对当地有利,公布成果的刊物亦具地方特色,这多少有些嫌疑。为此,我们有必要综合各地研究成果,以学术公允之心,对帝舜地望、行迹与卒葬等三个重要问题加以考辨,作出合理而可信的解释。需要阐明的是,尽管历代各地的州志、府志、县志在研究地方风物方面是较为可信的,但由于各地都“但愿”分享帝舜遗迹这一文化遗产,因此,其中对当地帝舜遗迹的记载或渲染,反而成为最不可靠的文字,我们一概不采。一帝舜地望考谈及帝舜出生地的文献有二:(1)《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2)《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孟子说是“诸冯东夷人”,司马迁说是“冀州人”。二人所述大相径庭,且所指非明,概念模糊。这引起了后人无尽的猜测,也诞生了种种解释。当今有关帝舜地望重要有三说:一为“冀州说”,或曰今山西垣曲,或曰今山西永济,皆在晋南;一说为“诸城说”,即今山东诸都市。持“诸城说”者的理由,重要是“东夷”这一族群的活动范围正在今天的山东与苏北地区。不错,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发现使“诸城说”获得了考古学支持。但以此解释舜的出生却是明显的断章取义。从孟子所言看,在春秋时期,将“东夷”帝舜与“西夷”周文王并举,显然不是把“东夷”作为专有名词使用,而是指周王朝都城镐京(今西安)之外的区域——镐京方圆五百里以外皆称“夷”。是故京都以东称“东夷”,京都以西称“西夷”。诸城在镐京以东两千余里,可称“东夷”,垣曲、永济在镐京东千余里,亦可称“东夷”。这样,“东夷”一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至于“诸冯”,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列出二处:“山东荷泽县南50里,相传即舜生处,即今诸城县。又山西垣曲县东北50里有诸冯山。”有学者便认为“诸冯城”简称为“诸城”(那里有冯村与冯山),有学者认为乃永济(那里有“姚墟”与古称诸冯村的舜帝村),尚有人认为诸冯即今垣曲,不一而足。其实,历史地名的衍化十分复杂,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故局限性采信。在“东夷”与“诸冯”二词失去考证意义后,另一名词——负夏——的意义就弥足宝贵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认为负夏(瑕)是“春秋时鲁邑,在今山东滋阳县三十五里之瑕丘故城”,聊存一说。今人李百勤著文《说虞舜》,从象形文字与古字读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