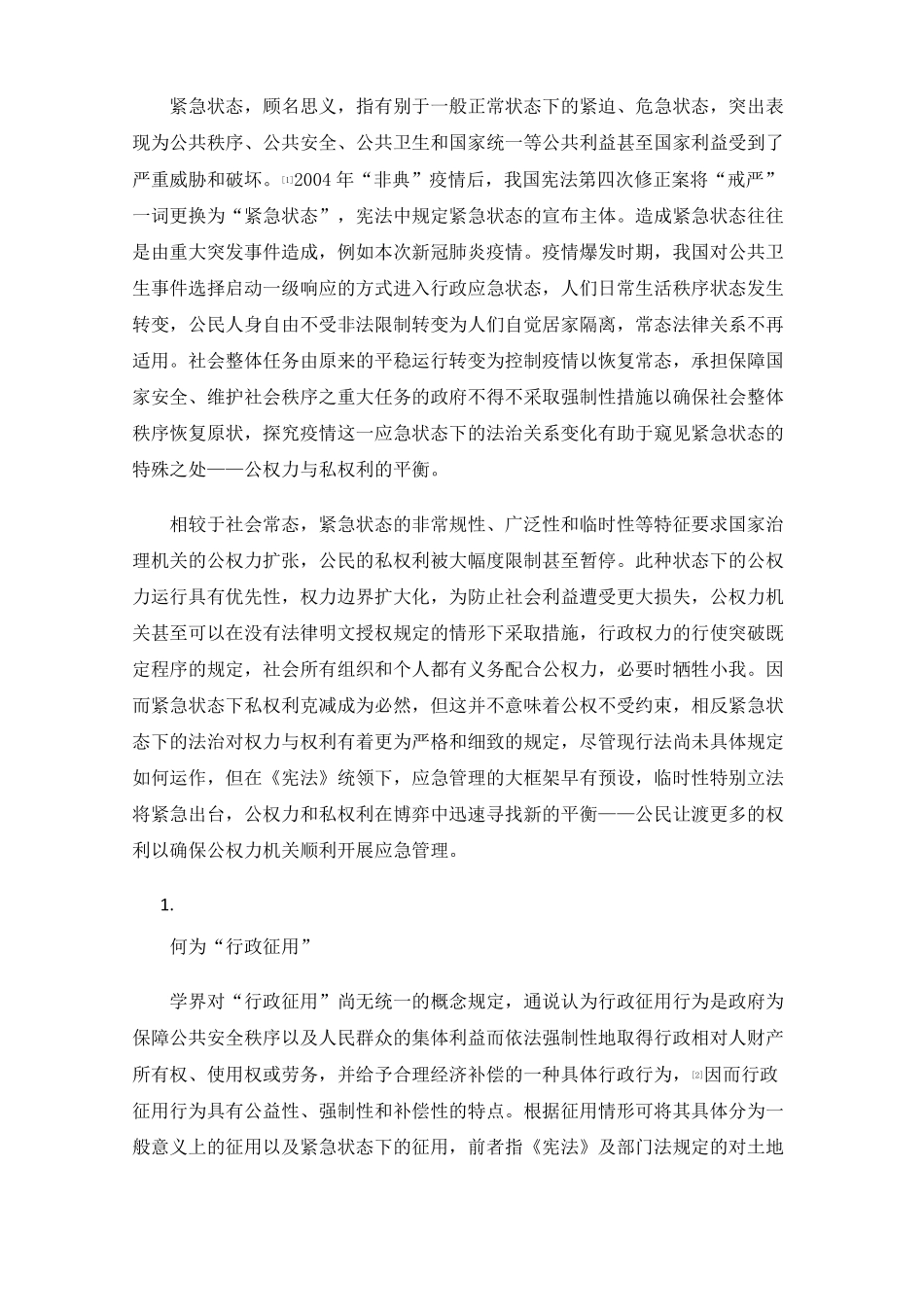论紧急状态征用客体扩展的合法性与救济机制摘要:紧急状态下为恢复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公权力出现适度扩张的趋势,公民私权利克减,原有平衡状态被打破,政府紧急征用人力资源的行为恰恰是对人身自由权限制的体现。尽管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以劳务、服务为代表的人力资源是否属于国家应急征用客体范畴,但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征用客体扩展至人力资源有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依据,有效的配套救济措施应当在法治框架内予以构建。统一紧急状态下人力资源征用的立法规定,明确征用人力资源的程序和损耗的补偿,创新性地引入精神嘉奖与物质补偿相结合、拓宽内部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下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关键词:紧急状态;人力资源;权利克减;征用;救济一、问题的提出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随后席卷世界各国。我国政府紧急征用各类医疗物资、防控场所组织抗疫,政府派遣医护人员驰援疫情严重地区,同时招募建筑工人改造建设方舱医院,传统意义上的征用客体正出现有形财产向无形人力资源扩展的趋势——具体体现在医生的救助行为、征用酒店附带服务人员的服务、应急物资生产者的劳务工作、建筑工人的劳动等一系列人力资源的付出。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征用客体的立法规定并不统一,学界对征用客体的探讨多限于财产,紧急状态下的征用行为是否可以扩展至人力资源,关乎被派遣、征调人员的补偿救济权保障,甚至关乎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因而理论和实务中存在对紧急状态下新型征用客体样态的探索必要。二、相关概念界定1.何为“紧急状态”紧急状态,顾名思义,指有别于一般正常状态下的紧迫、危急状态,突出表现为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国家统一等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和破坏。2004年“非典”疫情后,我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将“戒严”一词更换为“紧急状态”,宪法中规定紧急状态的宣布主体。造成紧急状态往往是由重大突发事件造成,例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疫情爆发时期,我国对公共卫生事件选择启动一级响应的方式进入行政应急状态,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状态发生转变,公民人身自由不受非法限制转变为人们自觉居家隔离,常态法律关系不再适用。社会整体任务由原来的平稳运行转变为控制疫情以恢复常态,承担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之重大任务的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措施以确保社会整体秩序恢复原状,探究疫情这一应急状态下的法治关系变化有助于窥见紧急状态的特殊之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相较于社会常态,紧急状态的非常规性、广泛性和临时性等特征要求国家治理机关的公权力扩张,公民的私权利被大幅度限制甚至暂停。此种状态下的公权力运行具有优先性,权力边界扩大化,为防止社会利益遭受更大损失,公权力机关甚至可以在没有法律明文授权规定的情形下采取措施,行政权力的行使突破既定程序的规定,社会所有组织和个人都有义务配合公权力,必要时牺牲小我。因而紧急状态下私权利克减成为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权不受约束,相反紧急状态下的法治对权力与权利有着更为严格和细致的规定,尽管现行法尚未具体规定如何运作,但在《宪法》统领下,应急管理的大框架早有预设,临时性特别立法将紧急出台,公权力和私权利在博弈中迅速寻找新的平衡——公民让渡更多的权利以确保公权力机关顺利开展应急管理。1.何为“行政征用”学界对“行政征用”尚无统一的概念规定,通说认为行政征用行为是政府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而依法强制性地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因而行政征用行为具有公益性、强制性和补偿性的特点。根据征用情形可将其具体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征用以及紧急状态下的征用,前者指《宪法》及部门法规定的对土地[2][1]承包经营权的一般征用行为,后者则是非常态下应急征用行为。行政征用的前提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一项限制公民权利的行政行为,紧急状态下的征用行为有其特殊性。由于紧急状态事发突然,行政机关仅凭自身力量无法应对,必须发挥其公共职能从而调动社会资源、借助社会力量,因而实践中的紧急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