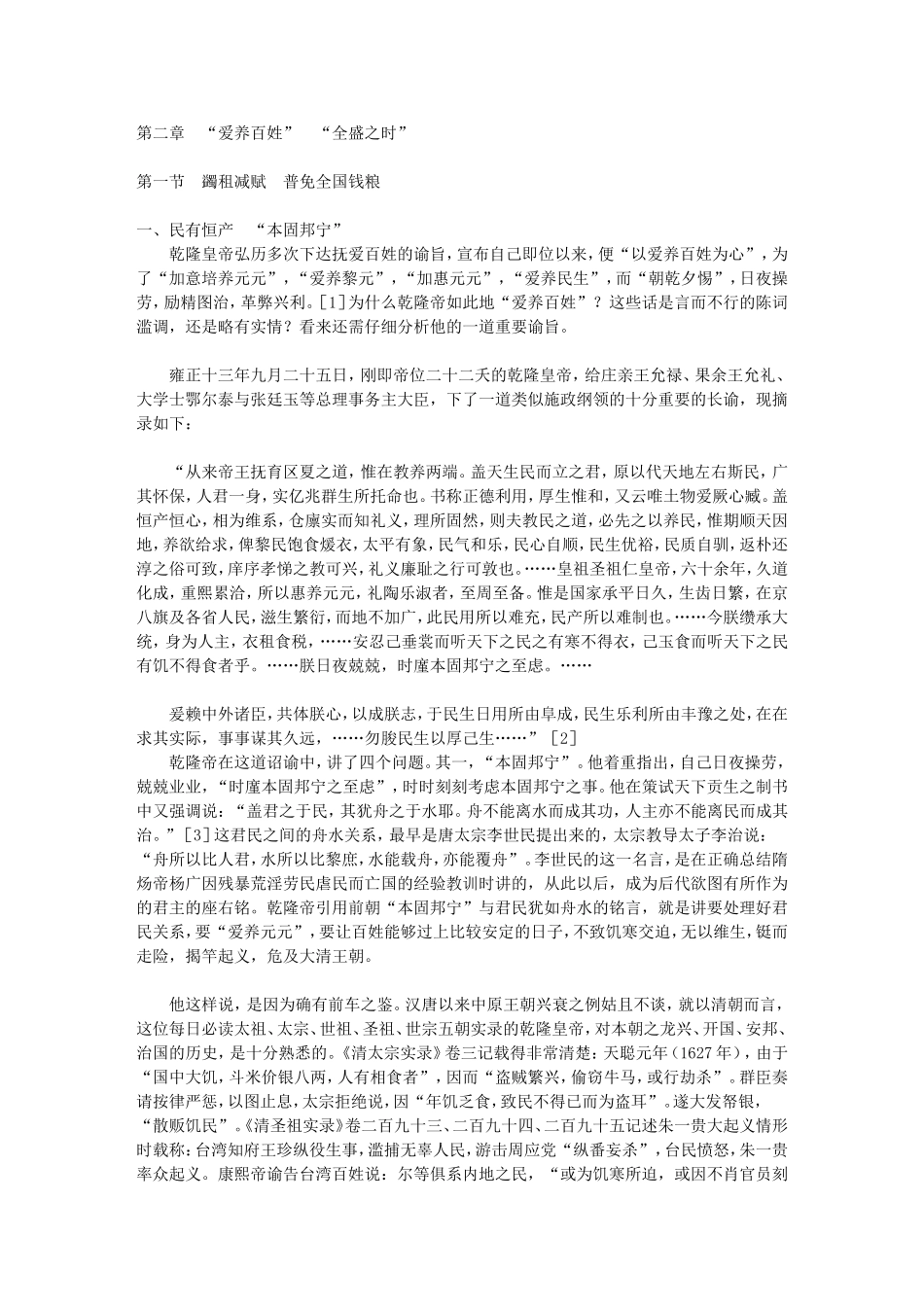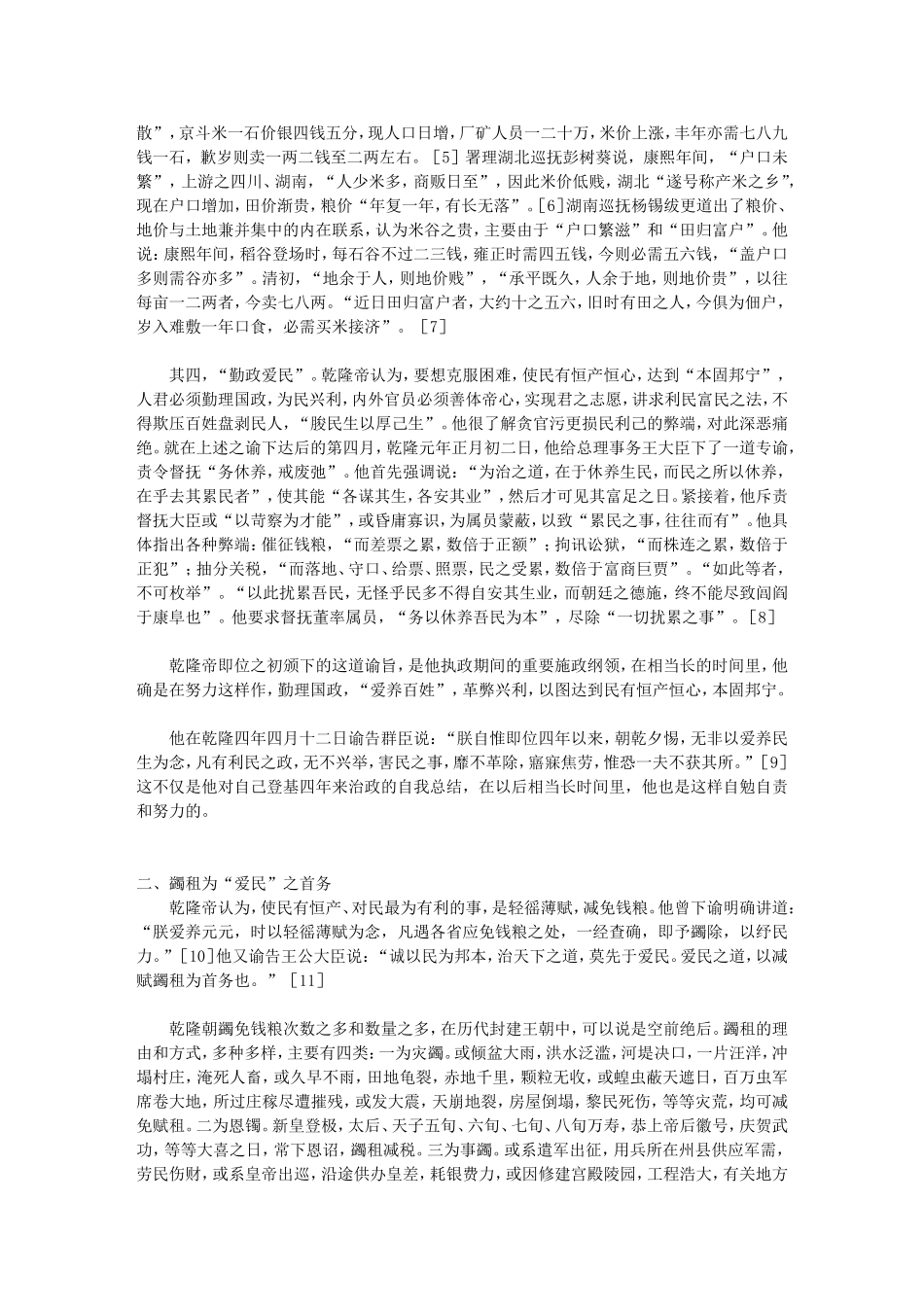第二章“爱养百姓”“全盛之时”第一节蠲租减赋普免全国钱粮一、民有恒产“本固邦宁”乾隆皇帝弘历多次下达抚爱百姓的谕旨,宣布自己即位以来,便“以爱养百姓为心”,为了“加意培养元元”,“爱养黎元”,“加惠元元”,“爱养民生”,而“朝乾夕惕”,日夜操劳,励精图治,革弊兴利。[1]为什么乾隆帝如此地“爱养百姓”?这些话是言而不行的陈词滥调,还是略有实情?看来还需仔细分析他的一道重要谕旨。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刚即帝位二十二夭的乾隆皇帝,给庄亲王允禄、果余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主大臣,下了一道类似施政纲领的十分重要的长谕,现摘录如下:“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盖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广其怀保,人君一身,实亿兆群生所托命也。书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又云唯土物爱厥心臧。盖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理所固然,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惟期顺天因地,养欲给求,俾黎民饱食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悌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皇祖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重熙累洽,所以惠养元元,礼陶乐淑者,至周至备。惟是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今朕缵承大统,身为人主,衣租食税,……安忍己垂裳而听天下之民之有寒不得衣,己玉食而听天下之民有饥不得食者乎。……朕日夜兢兢,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爰赖中外诸臣,共体朕心,以成朕志,于民生日用所由阜成,民生乐利所由丰豫之处,在在求其实际,事事谋其久远,……勿朘民生以厚己生……”[2]乾隆帝在这道诏谕中,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本固邦宁”。他着重指出,自己日夜操劳,兢兢业业,“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时时刻刻考虑本固邦宁之事。他在策试天下贡生之制书中又强调说:“盖君之于民,其犹舟之于水耶。舟不能离水而成其功,人主亦不能离民而成其治。”[3]这君民之间的舟水关系,最早是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来的,太宗教导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世民的这一名言,是在正确总结隋炀帝杨广因残暴荒淫劳民虐民而亡国的经验教训时讲的,从此以后,成为后代欲图有所作为的君主的座右铭。乾隆帝引用前朝“本固邦宁”与君民犹如舟水的铭言,就是讲要处理好君民关系,要“爱养元元”,要让百姓能够过上比较安定的日子,不致饥寒交迫,无以维生,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危及大清王朝。他这样说,是因为确有前车之鉴。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兴衰之例姑且不谈,就以清朝而言,这位每日必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实录的乾隆皇帝,对本朝之龙兴、开国、安邦、治国的历史,是十分熟悉的。《清太宗实录》卷三记载得非常清楚:天聪元年(1627年),由于“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因而“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群臣奏请按律严惩,以图止息,太宗拒绝说,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遂大发帑银,“散贩饥民”。《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记述朱一贵大起义情形时载称:台湾知府王珍纵役生事,滥捕无辜人民,游击周应党“纵番妄杀”,台民愤怒,朱一贵率众起义。康熙帝谕告台湾百姓说:尔等俱系内地之民,“或为饥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员刻剥”,遂致生变,“原其致此之罪,俱在不肖官员”,尔等宜停战就抚。他又下旨,严厉斥责“台湾府文职官员平日并不爱民,但知图利苛索”,“但知肥已,刻剥小民,激变人心,聚众叛逆”,令将道职以下文官全部捉拿,审明后即行正法。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就是乾隆帝强调“本固邦宁”的历史依据。其二,“恒产恒心”。乾隆帝认为,要想作到“本固邦宁”,就必须使民有恒产,因为,恒产与“恒心”是“相为维系”的,有了恒产,便能产生恒心,百姓有吃有穿,“饱食暖衣”,仓有余粮,才能“知礼义”,“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这样,民心顺,四海安宁,“太平有象”,如果民贫如洗,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哪怕酷刑滥杀,民亦将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