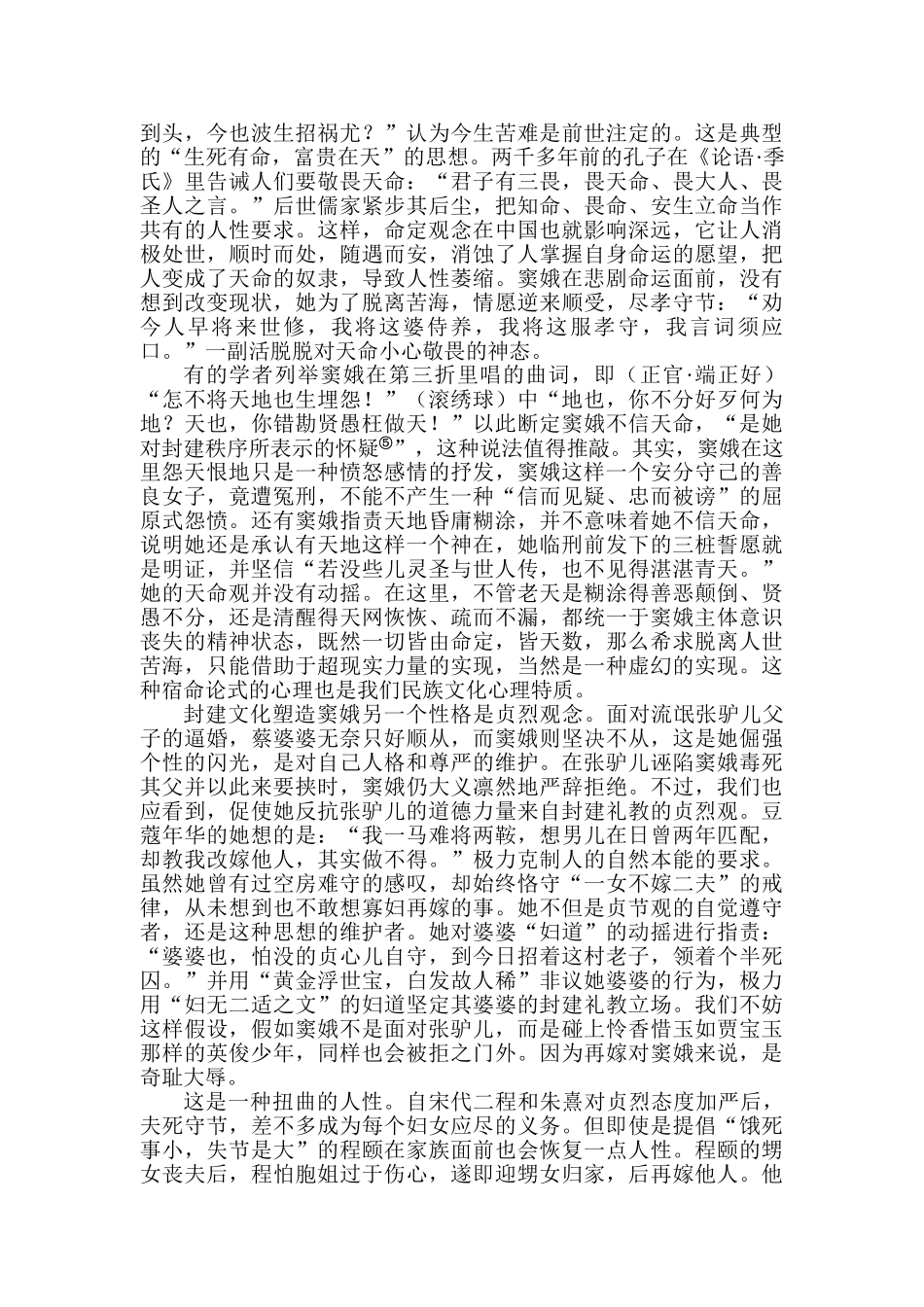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李建明[摘要]《窦娥冤》的主题历来被认为是反封建,本文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窦娥的形象是按封建文化的形象设计而成的,她的宿命论、贞烈观和只知尽义务的孝便是明证。关汉卿通过这对原型的加工,着重表现善良弱小百姓与强大黑暗势力之间的冲突,揭示窦娥悲剧的社会根源。可以认为,《窦娥冤》的悲剧主旨是人性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相交织。[关键词]《窦娥冤》封建文化悲剧《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认为它“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关于这篇作品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窳败的政治,异常强烈地表现了长期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②”。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则认定它是表现“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③”这个主题。总之,学术界大都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反封建。对这个学术界比较笼统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本文拟从作品的人物形象和关汉卿对原型的创造两方面剖析作品主题,从而揭示《窦娥冤》的悲剧实质。一文学作品是通过其描写的生活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主题的。分析《窦娥冤》的主题就应由此入手。这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是窦娥与张驴儿、桃杌的冲突。张驴儿这样的恶棍流氓和桃杌这种贪官污吏的产生,固然与封建社会有关,但他们毕竟不是封建社会的化身,何况封建制度对他们也是严惩不贷的。只有在封建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时,这些人渣才可能肆意横行而逍遥法外。因此,惩治流氓和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恢复封建秩序的努力,当然也体现了人民的某些愿望。我们不可简单地把这种行为看成是反封建的表现。窦娥反抗张驴儿和桃杌的行动,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而不是反封建的表现。如果再结合窦娥的形象作一些分析,这个看法就会显得更清楚明了。窦娥的抗争举动依据的思想武器是封建礼教对它灌输的“三从四德”。她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她的悲剧性格是封建文化道德塑造而成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贞节和孝的思想行为上。七岁的窦娥被生父窦天章以四十两银子为代价,卖到高利贷者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可是还不到二十岁,她就与婆婆一道守寡了。经历了幼年失母、少年离父、青春丧偶的窦娥,在遭受深重苦难时询问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④”显然,她独守空房,对“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尘皱”死水般的生活是哀怨的。但她把这种悲惨遭遇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认为今生苦难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典型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在《论语·季氏》里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后世儒家紧步其后尘,把知命、畏命、安生立命当作共有的人性要求。这样,命定观念在中国也就影响深远,它让人消极处世,顺时而处,随遇而安,消蚀了人掌握自身命运的愿望,把人变成了天命的奴隶,导致人性萎缩。窦娥在悲剧命运面前,没有想到改变现状,她为了脱离苦海,情愿逆来顺受,尽孝守节:“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一副活脱脱对天命小心敬畏的神态。有的学者列举窦娥在第三折里唱的曲词,即(正官·端正好)“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滚绣球)中“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以此断定窦娥不信天命,“是她对封建秩序所表示的怀疑⑤”,这种说法值得推敲。其实,窦娥在这里怨天恨地只是一种愤怒感情的抒发,窦娥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善良女子,竟遭冤刑,不能不产生一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式怨愤。还有窦娥指责天地昏庸糊涂,并不意味着她不信天命,说明她还是承认有天地这样一个神在,她临刑前发下的三桩誓愿就是明证,并坚信“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她的天命观并没有动摇。在这里,不管老天是糊涂得善恶颠倒、贤愚不分,还是清醒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都统一于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