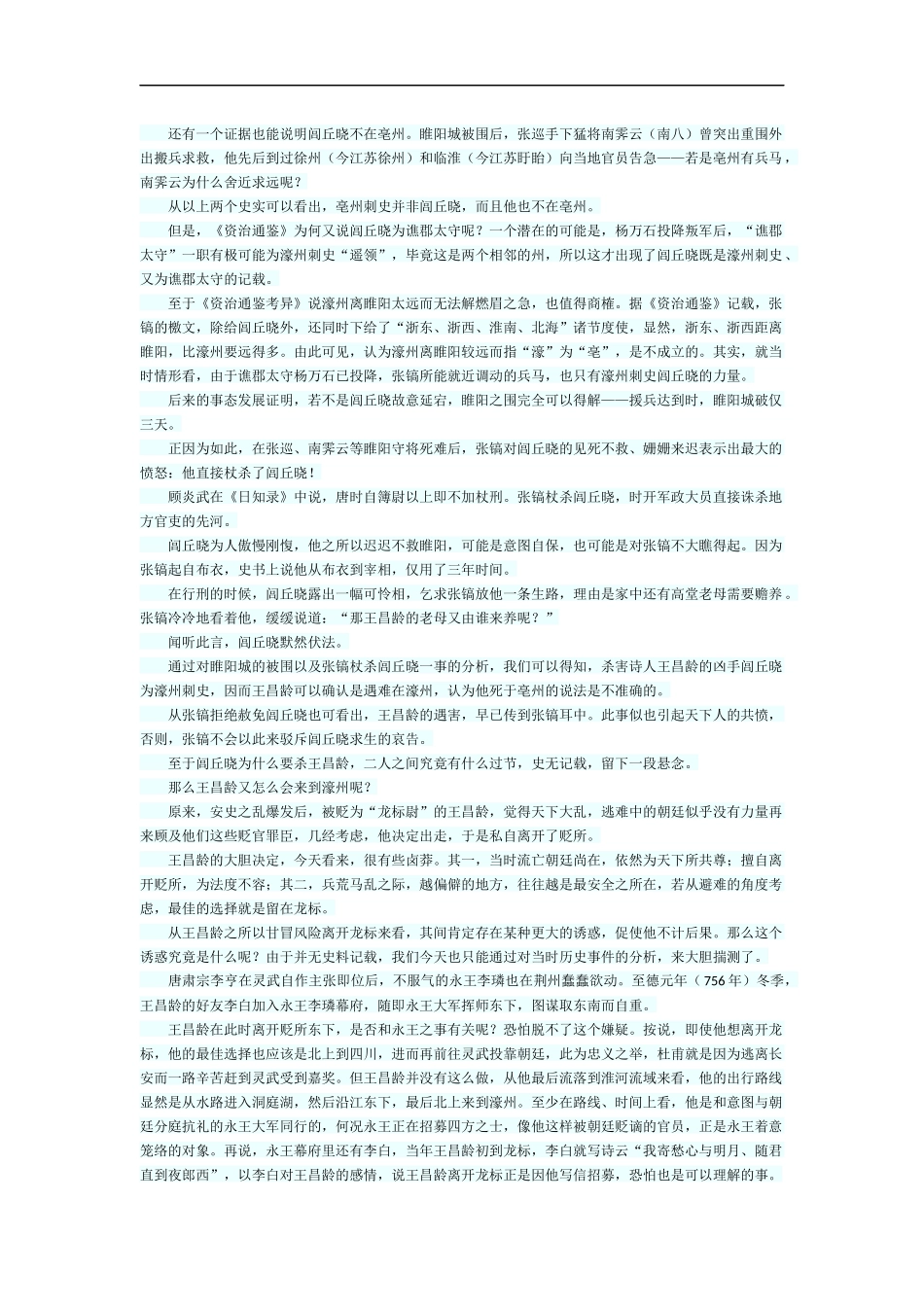在唐代诗人中,被称为“诗家天子”和“七言圣手”的王昌龄,始终是个迷一样的人物。他的许多诗句我们都耳熟能详,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寻渐》)等等,但是,他的一生行状,史书所记却寥寥无几,以致和他相关的许多细节,至今还是一团迷雾。比如,他的籍贯,后人一直众说纷纭。《新唐书》说是江宁人,《旧唐书》说是京兆人,《唐才子传》说是太原人。他流放的地点龙标(李白有诗云“闻道龙标过五溪”),其具体位置,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湖南黔阳,一说是贵州隆里(锦屏)。他在名诗《芙蓉楼送辛渐》中所云之“芙蓉楼”,所在地竟也有两处,一在江苏镇江,一在湖南洪江。他一生两次遭贬,具体原因史书却语焉不详,只有笼统的几个字:“不护细行”。和他有关的诗坛佳话“旗亭画壁”,也有人说是假的,乃后人向壁虚构。最后,就连他遇害的地点,也有两种说法:有人说他死于濠州(李云逸《王昌龄诗注》),也有人说他死于亳州(《辞海·文学卷》。由于史书所记王昌龄史料太少,现存的许多争议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不过,对王昌龄之死,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通过一番攀爬梳理,我们能得出一个清晰的判断。两唐书谈及王昌龄之死,都明确地说他为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刺史闾丘晓所杀,以此来看,王昌龄当死于濠州。但是,关于闾秋晓这个人,《资治通鉴》却说他是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太守,谯郡乃亳州的州治所在,因而后世有人认为王昌龄死于亳州。亳州与濠州,并非简单的笔画混淆,而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在王昌龄的时代,濠州属淮南道,亳州则属河南道。史料记载的差异,为我们探寻王昌龄之死的真相带来一定困惑。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察那个“杀人凶手”闾丘晓的活动范围,即他究竟是在濠州还是在亳州。闾丘晓这个人,本是进士出身,但他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名来,却完全因为他所干的两件不可饶恕之事:杀害王昌龄和不救睢阳之围。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唐玄宗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属宁夏)自行即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叛军攻下洛阳、长安,随即准备沿运河南下,掠夺江南赋税之地。但是,他们在睢阳(今河南商丘)遇到了张巡的殊死抵抗。张巡本是真源(属于亳州)县令,他先是招募兵士守卫雍丘(今河南杞县),后移守睢阳,以不到万人的兵力,抵挡住十倍于己的叛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形下,苦守城池达数月之久,有效地牵制住叛军数十万人马,与坚守南阳的鲁炅一道,成为江淮之地的屏障。在叛军的围困下,睢阳城内粮草断绝,守城军士在吃尽一切可吃之物后,只得吃阵亡和饿死者的尸体。史书云所食之人达三万众。此时,朝廷也认识到睢阳的重要,任命有文武经略之才的张镐为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为了尽快解救睢阳之围,张镐立即传檄江淮间各地刺使火速提兵北上。张镐这道十万火急的命令,两唐书说是下给了濠州刺史闾丘晓。《资治通鉴》也提到此事,云“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按《资治通鉴》的说法,闾丘晓是“谯郡太守”。由于谯郡是亳州的治所,以此推断,闾丘晓当在亳州。《资治通鉴考异》进而认为《新唐书》和《旧唐书》所云闾丘晓为濠州刺史有误,因为亳州和睢阳相邻,只有亳州的兵马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睢阳城下;而濠州则在亳州的南面,远水不解近渴。所以,张镐的调兵命令只能是下给亳州方面的。此说实有可商之处。据《新唐书》“张巡传”,安禄山刚反的时候,“谯郡太守杨万石降贼”;而且正是这个投敌的杨万石胁迫张巡北上雍丘,最后被张巡用计甩掉。对杨万石的投降,《资治通鉴》也有明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谯郡的太守为杨万石,且早已投降叛军,并非闾丘晓。还有一个证据也能说明闾丘晓不在亳州。睢阳城被围后,张巡手下猛将南霁云(南八)曾突出重围外出搬兵求救,他先后到过徐州(今江苏徐州)和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当地官员告急——若是亳州有兵马,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