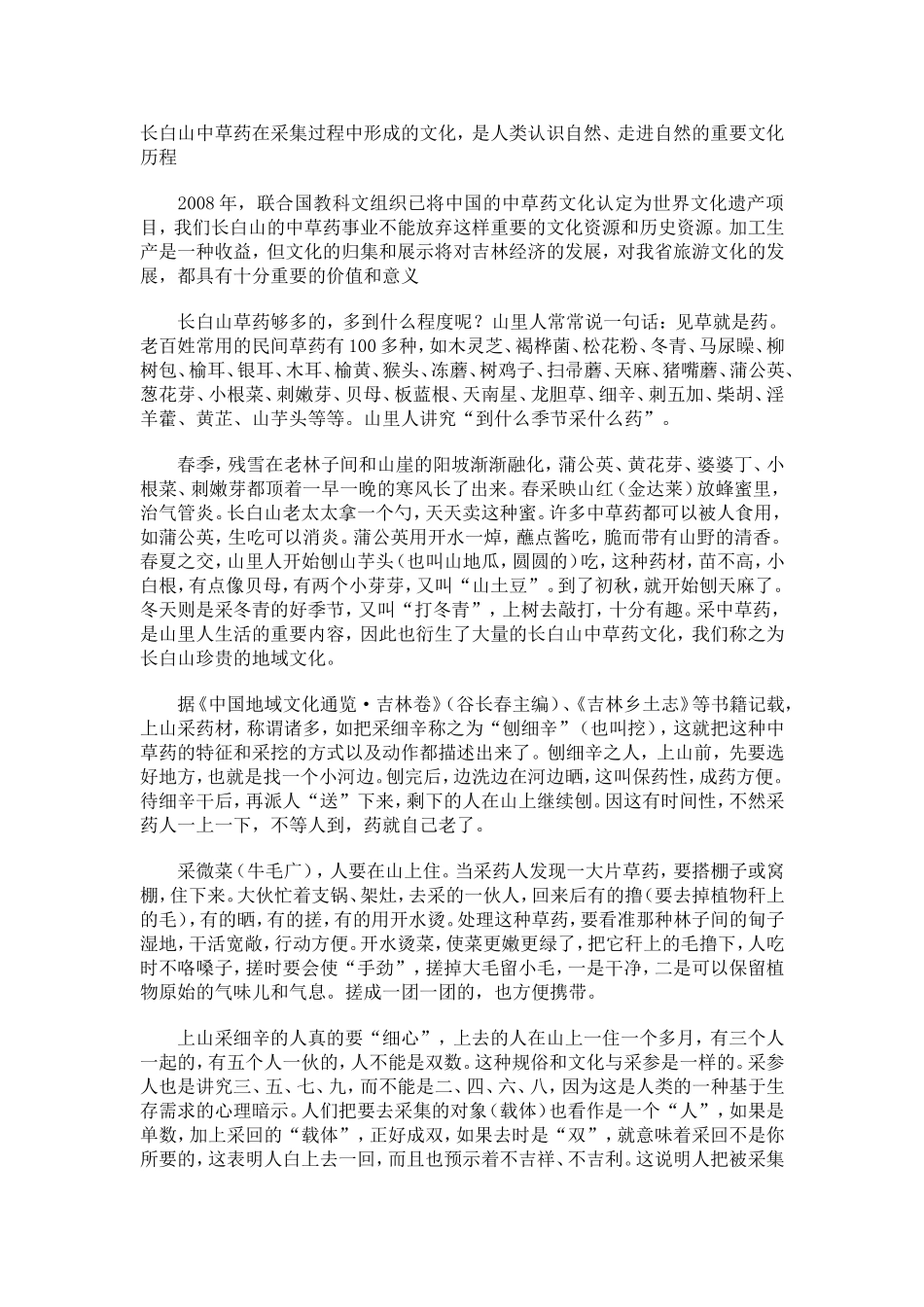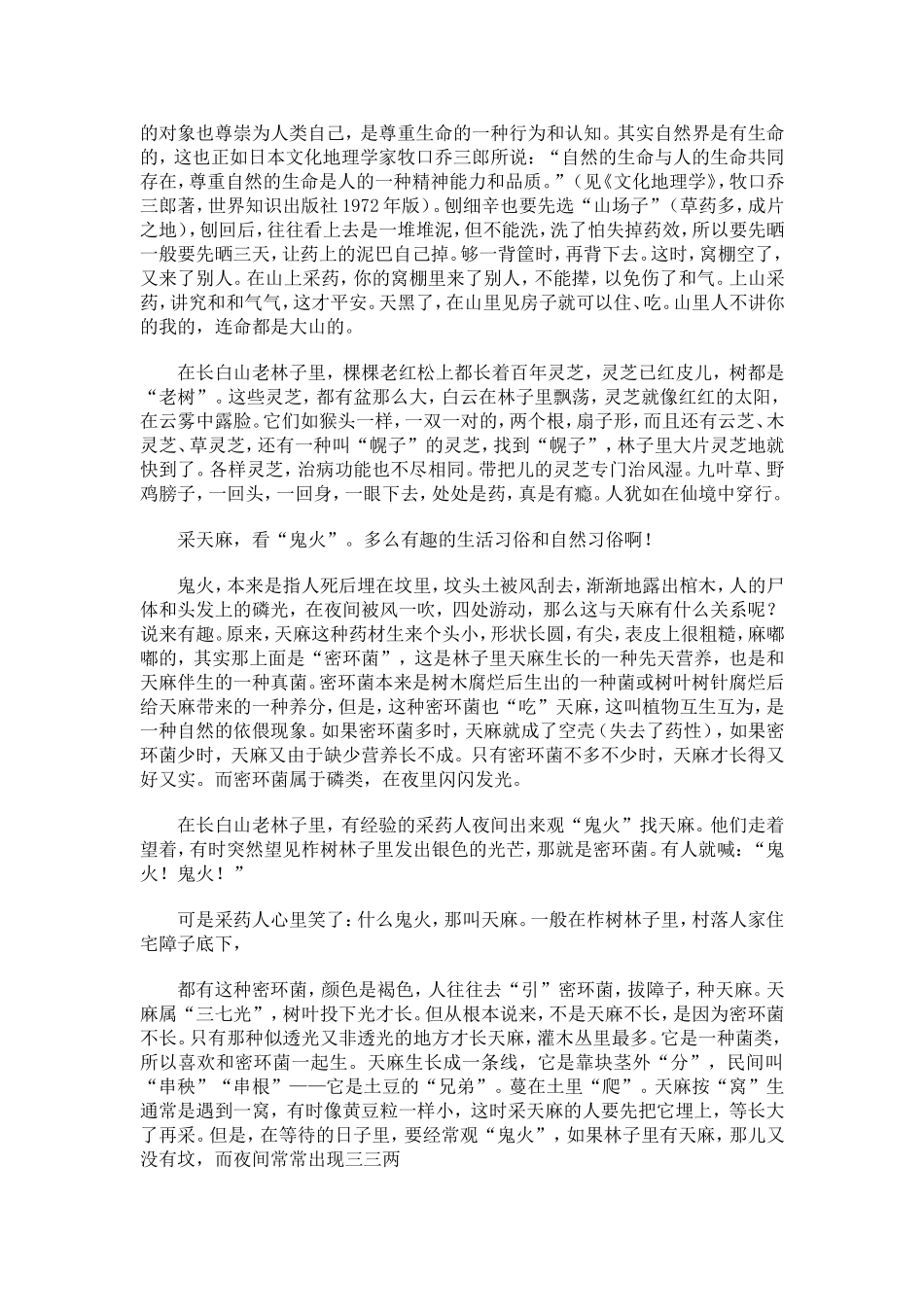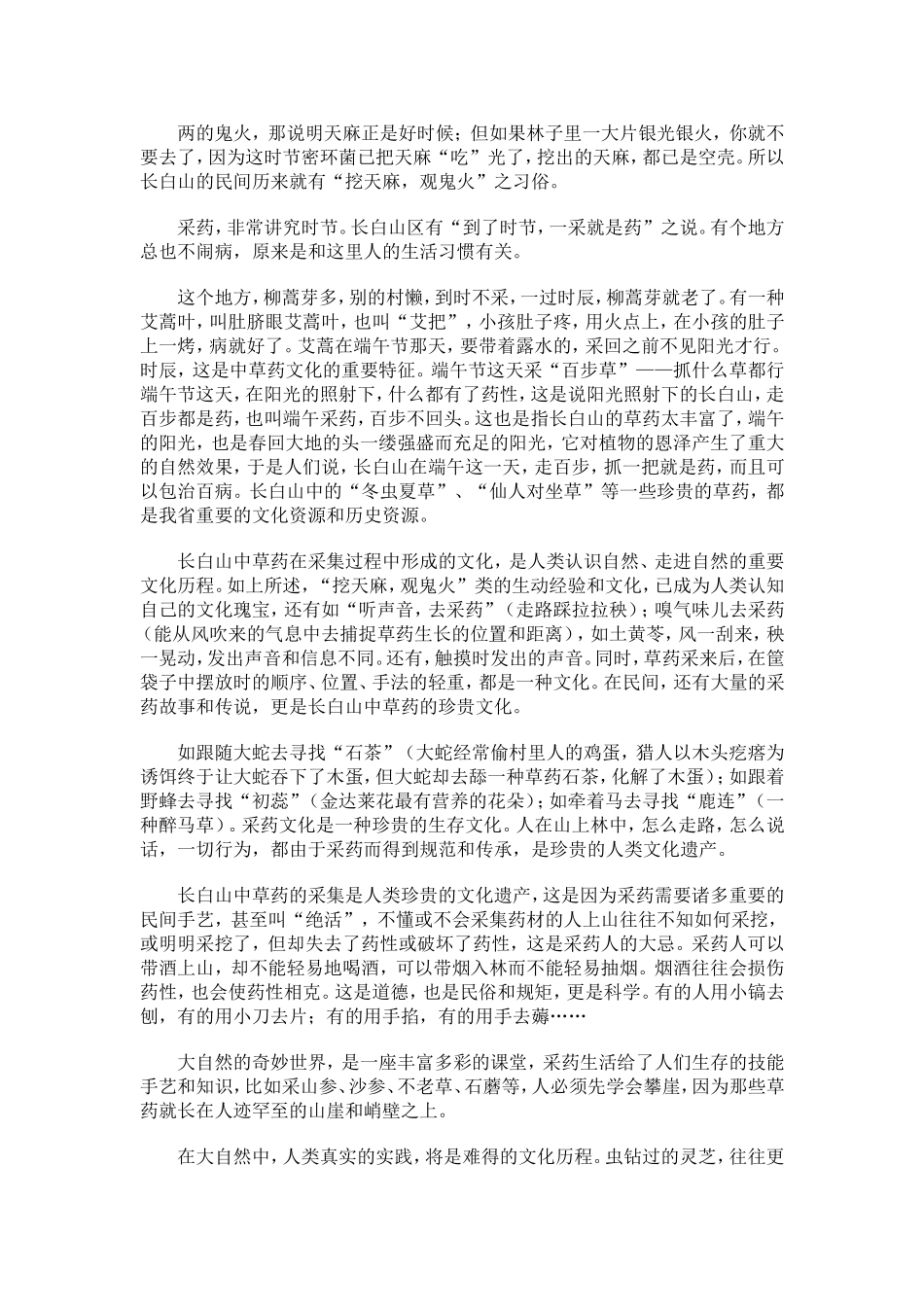长白山中草药在采集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是人类认识自然、走进自然的重要文化历程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中国的中草药文化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我们长白山的中草药事业不能放弃这样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加工生产是一种收益,但文化的归集和展示将对吉林经济的发展,对我省旅游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长白山草药够多的,多到什么程度呢?山里人常常说一句话:见草就是药。老百姓常用的民间草药有100多种,如木灵芝、褐桦菌、松花粉、冬青、马尿矂、柳树包、榆耳、银耳、木耳、榆黄、猴头、冻蘑、树鸡子、扫帚蘑、天麻、猪嘴蘑、蒲公英、葱花芽、小根菜、刺嫩芽、贝母、板蓝根、天南星、龙胆草、细辛、刺五加、柴胡、淫羊藿、黄芷、山芋头等等。山里人讲究“到什么季节采什么药”。春季,残雪在老林子间和山崖的阳坡渐渐融化,蒲公英、黄花芽、婆婆丁、小根菜、刺嫩芽都顶着一早一晚的寒风长了出来。春采映山红(金达莱)放蜂蜜里,治气管炎。长白山老太太拿一个勺,天天卖这种蜜。许多中草药都可以被人食用,如蒲公英,生吃可以消炎。蒲公英用开水一焯,蘸点酱吃,脆而带有山野的清香。春夏之交,山里人开始刨山芋头(也叫山地瓜,圆圆的)吃,这种药材,苗不高,小白根,有点像贝母,有两个小芽芽,又叫“山土豆”。到了初秋,就开始刨天麻了。冬天则是采冬青的好季节,又叫“打冬青”,上树去敲打,十分有趣。采中草药,是山里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衍生了大量的长白山中草药文化,我们称之为长白山珍贵的地域文化。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吉林卷》(谷长春主编)、《吉林乡土志》等书籍记载,上山采药材,称谓诸多,如把采细辛称之为“刨细辛”(也叫挖),这就把这种中草药的特征和采挖的方式以及动作都描述出来了。刨细辛之人,上山前,先要选好地方,也就是找一个小河边。刨完后,边洗边在河边晒,这叫保药性,成药方便。待细辛干后,再派人“送”下来,剩下的人在山上继续刨。因这有时间性,不然采药人一上一下,不等人到,药就自己老了。采微菜(牛毛广),人要在山上住。当采药人发现一大片草药,要搭棚子或窝棚,住下来。大伙忙着支锅、架灶,去采的一伙人,回来后有的撸(要去掉植物秆上的毛),有的晒,有的搓,有的用开水烫。处理这种草药,要看准那种林子间的甸子湿地,干活宽敞,行动方便。开水烫菜,使菜更嫩更绿了,把它秆上的毛撸下,人吃时不咯嗓子,搓时要会使“手劲”,搓掉大毛留小毛,一是干净,二是可以保留植物原始的气味儿和气息。搓成一团一团的,也方便携带。上山采细辛的人真的要“细心”,上去的人在山上一住一个多月,有三个人一起的,有五个人一伙的,人不能是双数。这种规俗和文化与采参是一样的。采参人也是讲究三、五、七、九,而不能是二、四、六、八,因为这是人类的一种基于生存需求的心理暗示。人们把要去采集的对象(载体)也看作是一个“人”,如果是单数,加上采回的“载体”,正好成双,如果去时是“双”,就意味着采回不是你所要的,这表明人白上去一回,而且也预示着不吉祥、不吉利。这说明人把被采集的对象也尊崇为人类自己,是尊重生命的一种行为和认知。其实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这也正如日本文化地理学家牧口乔三郎所说:“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共同存在,尊重自然的生命是人的一种精神能力和品质。”(见《文化地理学》,牧口乔三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72年版)。刨细辛也要先选“山场子”(草药多,成片之地),刨回后,往往看上去是一堆堆泥,但不能洗,洗了怕失掉药效,所以要先晒一般要先晒三天,让药上的泥巴自己掉。够一背筐时,再背下去。这时,窝棚空了,又来了别人。在山上采药,你的窝棚里来了别人,不能撵,以免伤了和气。上山采药,讲究和和气气,这才平安。天黑了,在山里见房子就可以住、吃。山里人不讲你的我的,连命都是大山的。在长白山老林子里,棵棵老红松上都长着百年灵芝,灵芝已红皮儿,树都是“老树”。这些灵芝,都有盆那么大,白云在林子里飘荡,灵芝就像红红的太阳,在云雾中露脸。它们如猴头一样,一双一对的,两个根,扇子形,而且还有云芝、木灵芝、草灵芝,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