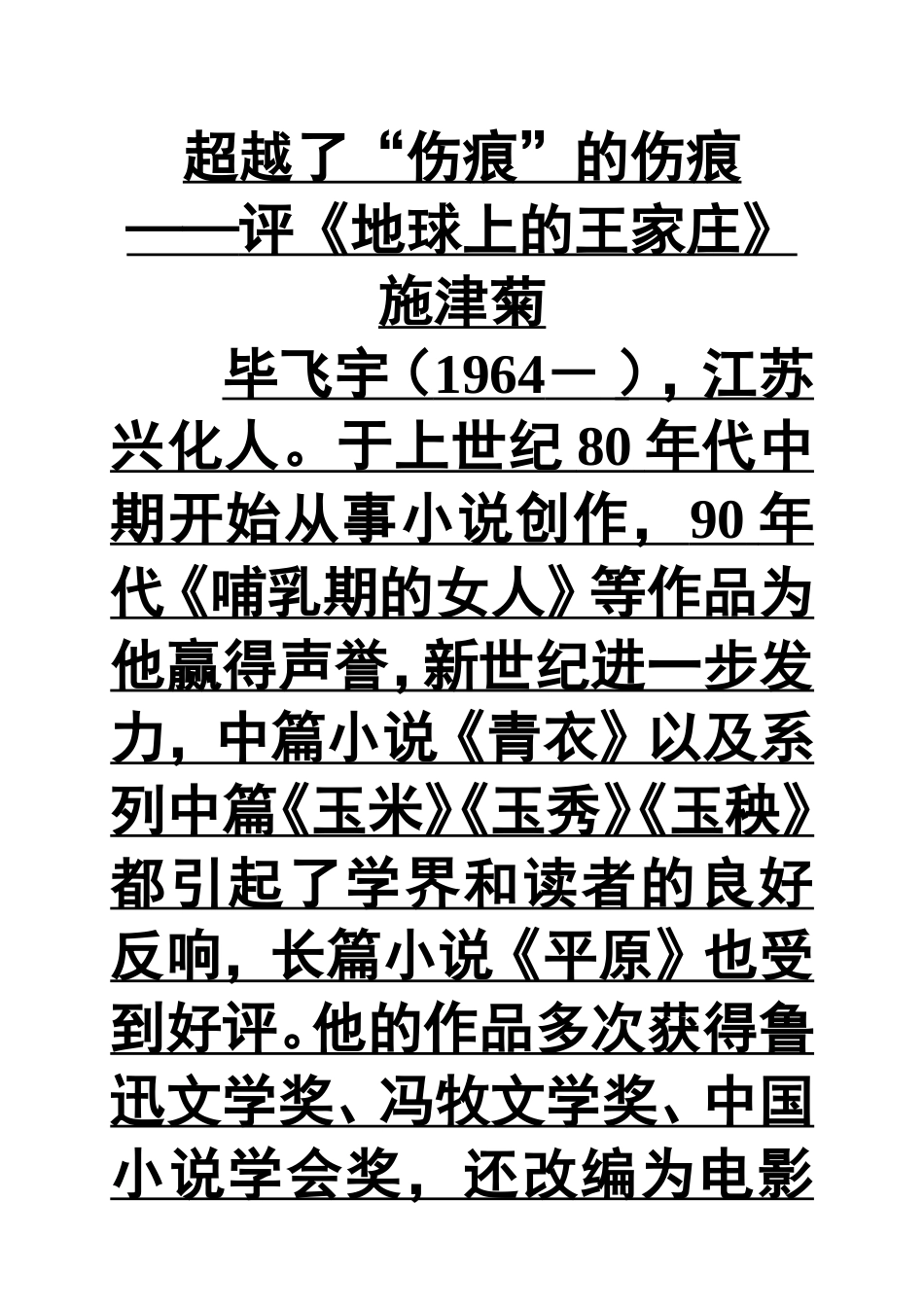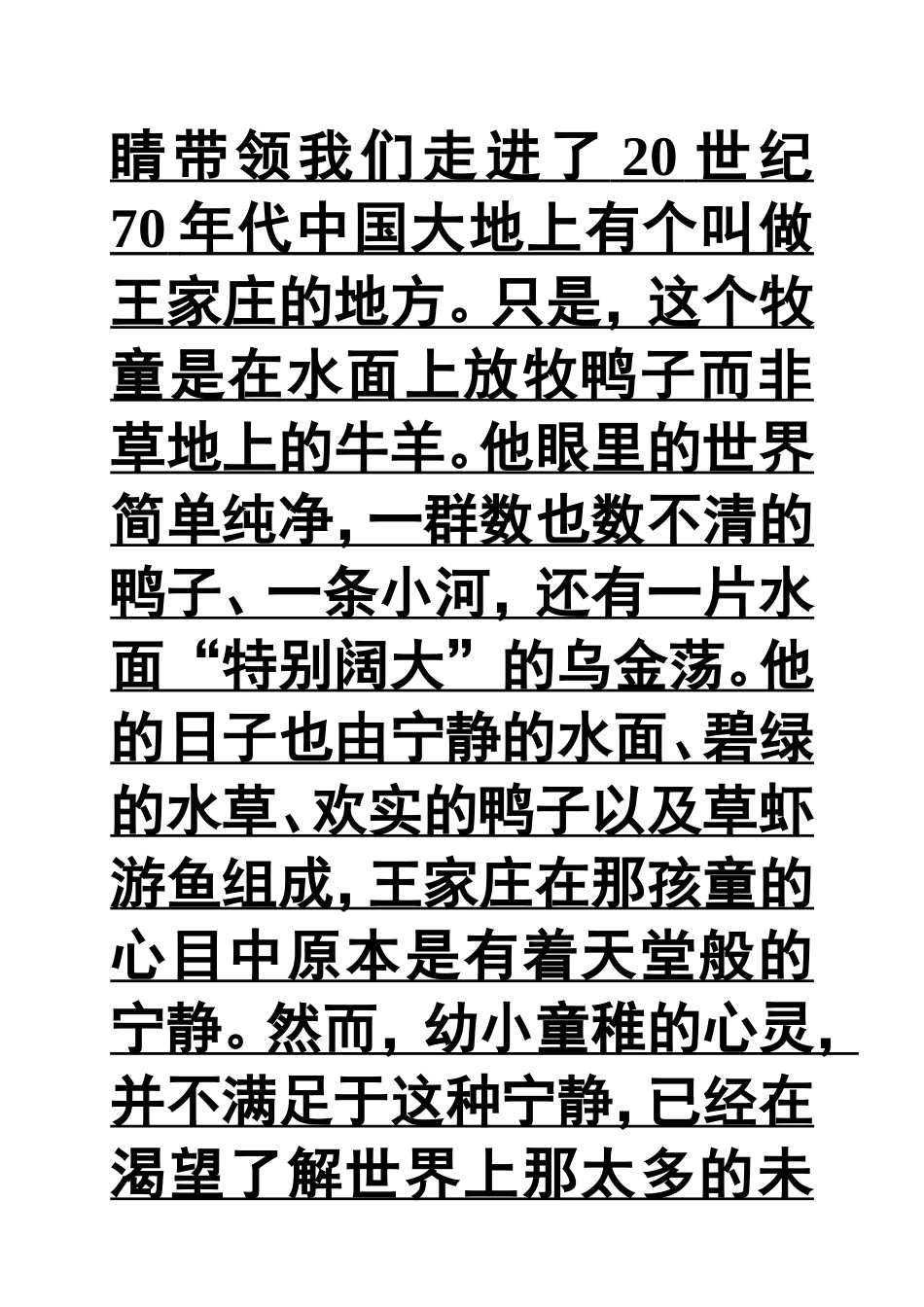超越了“伤痕”的伤痕——评《地球上的王家庄》施津菊毕飞宇(1964-),江苏兴化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小说创作,90年代《哺乳期的女人》等作品为他赢得声誉,新世纪进一步发力,中篇小说《青衣》以及系列中篇《玉米》《玉秀》《玉秧》都引起了学界和读者的良好反响,长篇小说《平原》也受到好评。他的作品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奖,还改编为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电视剧《青衣》。他对当代农村有着独具只眼的观照,尤其擅长表现女性的悲剧命运与复杂隐秘的心灵世界。在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毕飞宇是有着骄人成就的。2002年《上海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毕飞宇创作中又一别开生面之作,被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列为当年短篇的榜首。小说以一个八岁的蒙昧未开的牧童视角和童真的眼睛带领我们走进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地上有个叫做王家庄的地方。只是,这个牧童是在水面上放牧鸭子而非草地上的牛羊。他眼里的世界简单纯净,一群数也数不清的鸭子、一条小河,还有一片水面“特别阔大”的乌金荡。他的日子也由宁静的水面、碧绿的水草、欢实的鸭子以及草虾游鱼组成,王家庄在那孩童的心目中原本是有着天堂般的宁静。然而,幼小童稚的心灵,并不满足于这种宁静,已经在渴望了解世界上那太多的未知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这种渴望依然是不可压抑的人之天性。而在当时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速成式的教育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刘胡兰、雷锋的故事已经像随风飘散的种子播撒到了“我”懵懂颟顸的小小灵魂里。小说到此都一直氤氲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轻描淡写之中,那个历史时代的疯狂与斗争的激烈氛围都被滤去了,这也为后来王家庄年轻人的精神探索做了含蓄自然的铺垫。不管外面的世界怎样的风雷激荡,王家庄之于“我”,仍然是水乡牧鸭式的天堂。而这天堂里的不和谐因素,居然是父亲。父亲似乎不属于王家庄,他永远也晒不黑的双手和屁股便是标志,这也就注定了他是孤独的异乡者;正如他儿子所说,人间的麻烦是如此巨大,他不问不管,却去操宇宙的那份心,而面对现实的沉默、白眼和对黑夜之中宇宙星空的迷恋,又使他完全不附和那个时代激励人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革命潮流,而显得乖戾并成为异端。更甚的是,父亲带回家并挂在山墙上的那张世界地图。可谓一图就激起了王家庄年轻人心底的千层浪,自然而然地引发出那些让他们一度恐慌不得安宁的问题。仔细想想困扰王家庄的年轻人的那些问题,就像世界“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大”这样的疑问,似乎太形而下了,恐怕只有王家庄的人才会这么小儿科。当然,在知识和文明遭到践踏和封杀的年代,只要是从来没有见过家乡之外的世界的人,不管是李家庄或赵家庄的人,都可能也只会用那样的眼光衡量和思考外面的天地。虽然每一个人眼中的自身和世界都可能是不一样的,但人对自身和世界的思考却又有着共通之处。小说的自然巧妙之处也就在于借一张世界地图表达了人类心灵共性中的一部分——即使是那个渺小的在世界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王家庄,即使是处于那个特定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蛮荒岁月,即使是在那个意识形态的灌输替代了科学知识传播的政治高压年代,也仍然没能泯灭王家庄的年轻人、包括蒙昧无知的“我”,对自身、对世界的求知渴望和对未知世界以及世界尽头怀有恐惧的自然天性。王家庄的人愤慨地说:“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对此,谁能说王家庄的人所表达的不是对自身存在的关注和对世界疑问的探求呢。正因为如此,八岁的“我”,在经历了这次心灵历险之后,想用自己的脚和眼睛去寻找答案:“我要带上我的鸭子,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看一看。”一个八岁的村童,划一条小舢板,赶着一群自己都数不清的鸭子,去寻找世界的边缘,去做当年哥伦布式的探险壮举,这是何等的壮怀激烈,何等的浪漫执著,又是何等的稚嫩可爱,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以上是这篇小说叙述的意义层面之一,它用人物简单幼稚的方式、直白的语言和朴素的动机,生动地传达出人们探索世界奥秘的本能渴望和对生命与世界终极的深刻追问,而这又是不论任何时代中的任何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