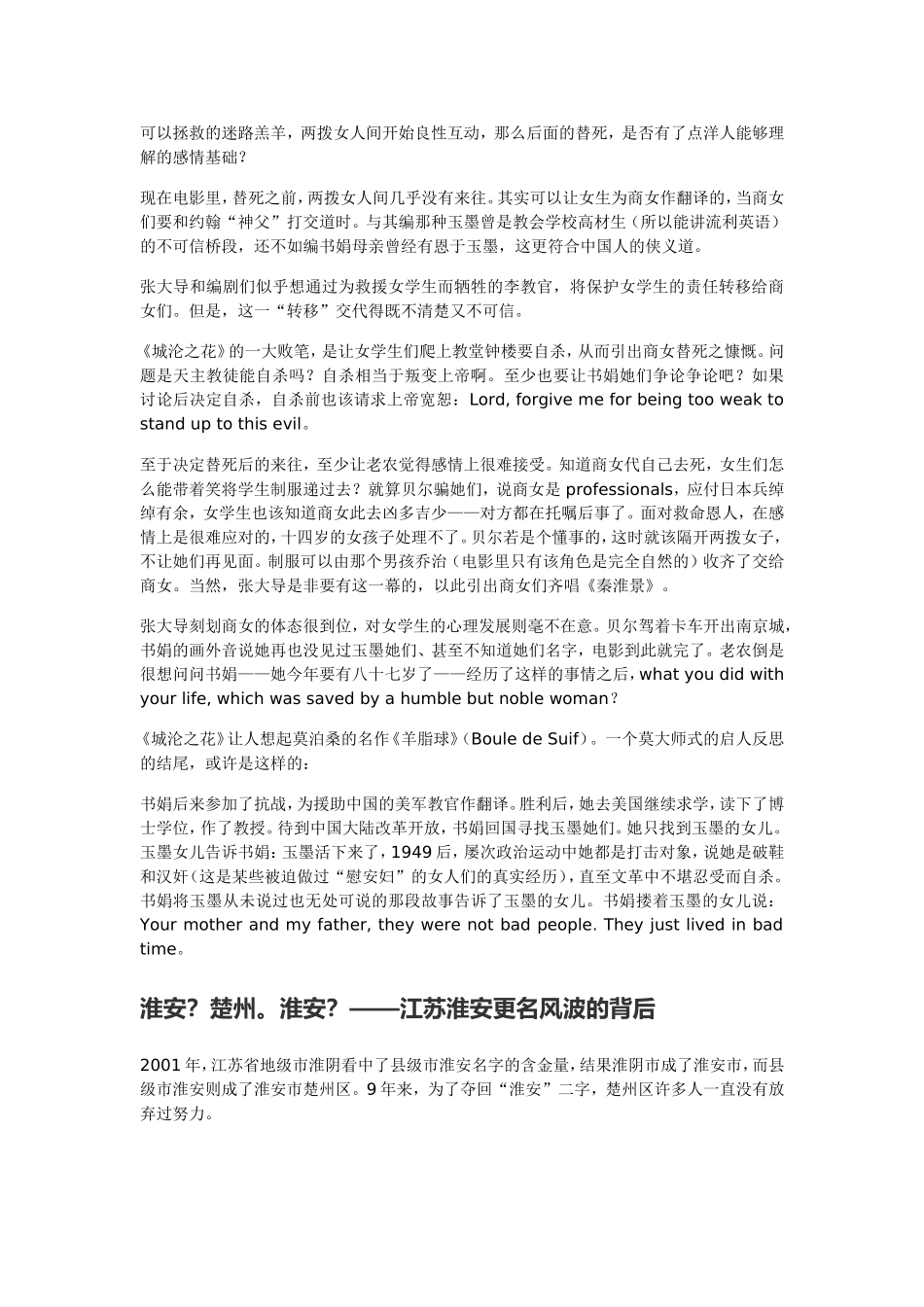国破商女恨,城沦烟花真张艺谋导演的电影《TheFlowersofWar》(下文将译作“城沦之花”——吴老农宁愿唐突张大导,也不愿唐突《红楼梦》里“金陵十二钗”),最近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各选一家影院上映一周。奥斯卡有规矩,新片只要年底前在洛杉矶任何影院公映至少七天,就有资格报名参选。显然,这部电影是冲着明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去的。故事想来大家已知道。1937年12月,日本兵攻陷南京。南京天主堂内,有两拨女子躲在那里避难。一拨是教会学校女学生;另一拨是秦淮河上的商女。一个美国来的假神父约翰,代表教会与日本占领当局打交道。当日本兵要把女学生带走蹂躏时,商女们挺身而出,替下了女学生。坐在影院里,感觉上,这几乎就是一部美国电影了。编排和节奏是好莱坞式的,甚至男主角起用的都是洋人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大把的英语之外,汉语讲的是南京方言,从根上甩掉了央视腔。摄影很好,拍国军战士很酷,拍秦淮商女很美。片中的江南丝竹,也是老农爱听的音乐。张艺谋的一贯弱项是编故事,这次基本编顺了,看来刘恒和严歌苓起了作用。有些细节略为用力过度,过于巧合,比如贝尔的角色约翰“神父”之女儿在女学生书娟的年龄死去,头牌商女玉墨在这年龄被嫖客开苞,以此建立这两位与女学生的暗中感情联系。但这至少说明编剧尽力了。戏里甚至有黑色幽默。为日军作翻译的书娟父亲,见到被日本人拉走的“女学生”里没有自己的女儿,他很可能叫唤坏事,日本兵却没有给他机会。中国第一部基本好莱坞化(说得好听点是全球化)的片子,在中国电影史上或许可算划时代,但要打开海外局面,却还得是上乘的好莱坞电影才行。可惜洋人不太买账,至少俺找到的几篇美国影评不太买账。我们中国人多少读过些武侠小说,商女们仅凭一腔侠情而代女学生去死,还觉得可以接受。美国影评人则认为整个故事不可信,当它纯为煽情之作。其实,就是侠义,多少也要点报恩成分的。这里就看出张艺谋的局限了。这老小子也是老农德性,扎根乡土坚定不移,虽说表现不同。老农是自知土而拼命装,明明只是中学程度——英语算是勉强有英国中学程度吧,其他各科中国中学程度——却整天装得像是有点文化的样子;老谋子则跟俺老家的乡亲一样,坐田埂上聊天,三句里总有两句跟男性生理偏好有关。他在《南方周末》的采访(12月15日)中说:“在创作前期,我跟许多专家讨论,专家给我讲好多秦淮文化,因为电影讲的是秦淮女子嘛”——更严格地说,《城沦之花》讲的只是秦淮女子。电影里另一拨女子,书娟她们这些教会学生所受的基督教文化影响,则对不起,通忘记了。老谋子只对商女感性趣,他才不会想到要请专家给他讲讲基督教义。难怪电影里书娟她们祈祷完了,连个十字都不划。书娟她们在电影中是conventstudents,读的是修女院办的女校,在那个时代,是按准修女培养的。而且那时的十四岁也不是今日的十四岁,今日的十四岁还是傻的,那时已是准大人。她们不可能没有受过基本的宗教教育,不可能不受传教士活动的影响。当年传教士在中国做的一大好事就是收容妓女,为她们治病。明年是赛珍珠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她因着写了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大地》(TheGoodEarth),而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女性桂冠作家。从小带她并教她汉语的王阿妈,就是赛珍珠的传教士父母从妓院赎出来的。但老谋子把这些学生拍得像是纯受旧式中国教育似的,她们看不起商女,不让玉墨她们用楼上的厕所。如果改为商女们逃难时受尽歧视,人们不准她们进入藏身洞所;倒是这些女学生将她们当作可以拯救的迷路羔羊,两拨女人间开始良性互动,那么后面的替死,是否有了点洋人能够理解的感情基础?现在电影里,替死之前,两拨女人间几乎没有来往。其实可以让女生为商女作翻译的,当商女们要和约翰“神父”打交道时。与其编那种玉墨曾是教会学校高材生(所以能讲流利英语)的不可信桥段,还不如编书娟母亲曾经有恩于玉墨,这更符合中国人的侠义道。张大导和编剧们似乎想通过为救援女学生而牺牲的李教官,将保护女学生的责任转移给商女们。但是,这一“转移”交代得既不清楚又不可信。《城沦之花》的一大败笔,是让女学生们爬上教堂钟楼要自杀,从而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