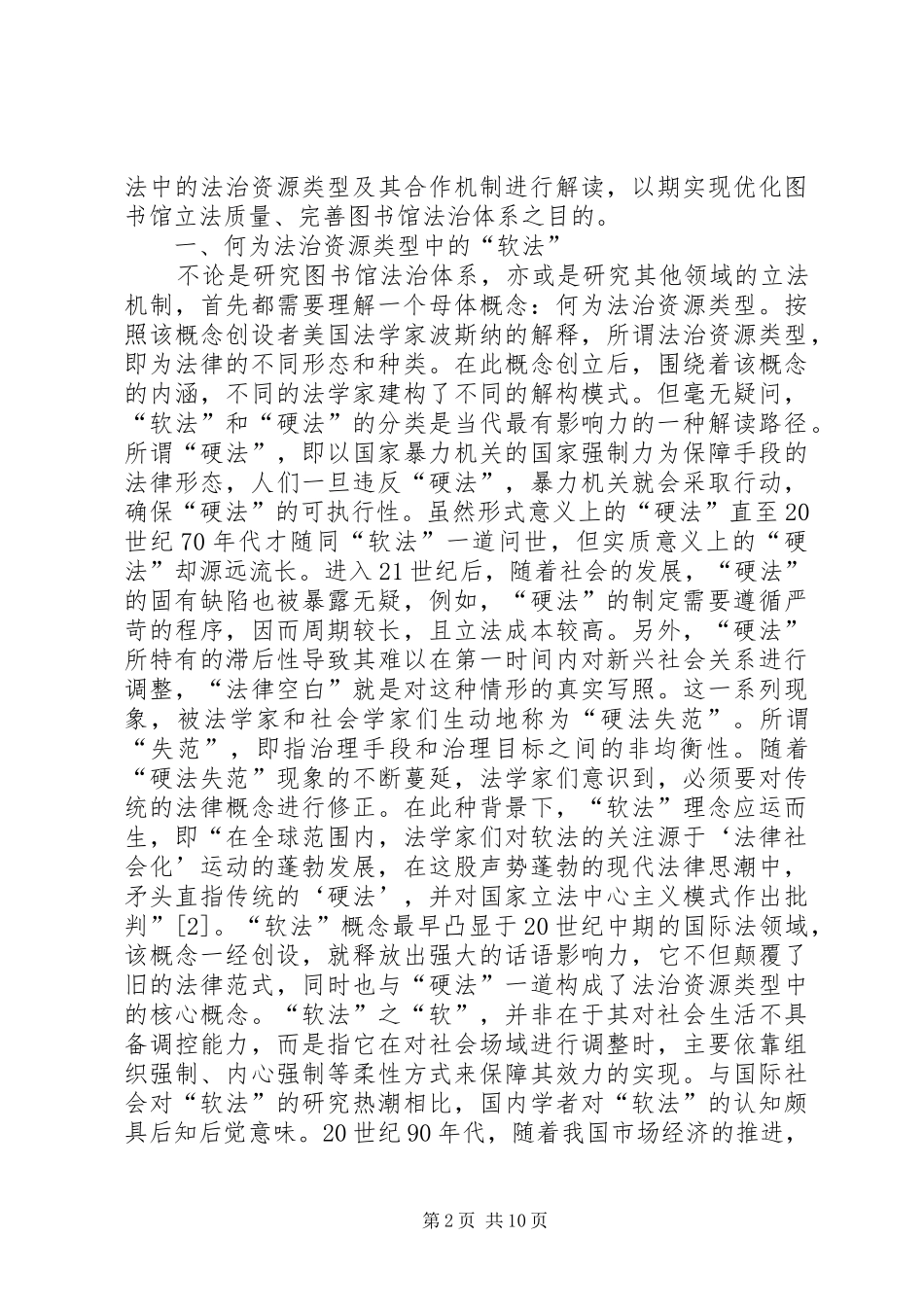图书馆法治建设互动机制研究摘要。“软法”的创立,体现了社会内生规范对于国家治理的正向作用,并成为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新变量。在图书馆法治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软法”基于其协商民主价值,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的文本分析,可以对“软法”与“硬法”在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运行机制作出考察;而通过对“软法”与“硬法”进行的swot分析,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耦合”效应。在未来语境下,应该遵循公共文化领域立法的一般规律,实现“软法”与“硬法”在图书馆法治建设中的共生与共存,即促成“图书馆软法”与“图书馆硬法”之间的有机转化和良性共存。关键词:“软法”;“硬法”;图书馆法治;共生而治法者,治之端也[1]。法治作为社会调控的依据,兼具理论与实践维度的双重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讲,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应渗透至社会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就涵盖了图书馆领域。从实践层面而言,法治作为一种调控工具,对社会各个行业都应具备启迪作用,进而促成行业运转的规范化、可控化。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沿革的图书馆业,自然也需要配备法治思维,进而应对多变的社会生态结构。事实上,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在图书馆领域,一场“图书馆法治现代化”运动也应运而生。其中,用法治来引领图书馆领域的未来发展,已成为图书馆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所不谋而合的共识。20XX年,在当时尚未有全国性图书馆立法的情形下,国家科学技术部就先行制定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28220-20XX)(以下简称《规范》),为图书馆领域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秩序供给。20XX年,在众多图书馆学人的联手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图书馆法》)得以问世,并在20XX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实践中,这两部规范性文件为图书馆工作的正常运转奠定了基础。但在学界,迄今尚未有学者对这两部规范文件中的资源要素进行系统性解构,这实则为一种缺憾。本文欲以《规范》和《图书馆法》为标准化样本,对图书馆立第1页共10页法中的法治资源类型及其合作机制进行解读,以期实现优化图书馆立法质量、完善图书馆法治体系之目的。一、何为法治资源类型中的“软法”不论是研究图书馆法治体系,亦或是研究其他领域的立法机制,首先都需要理解一个母体概念:何为法治资源类型。按照该概念创设者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解释,所谓法治资源类型,即为法律的不同形态和种类。在此概念创立后,围绕着该概念的内涵,不同的法学家建构了不同的解构模式。但毫无疑问,“软法”和“硬法”的分类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解读路径。所谓“硬法”,即以国家暴力机关的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手段的法律形态,人们一旦违反“硬法”,暴力机关就会采取行动,确保“硬法”的可执行性。虽然形式意义上的“硬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随同“软法”一道问世,但实质意义上的“硬法”却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硬法”的固有缺陷也被暴露无疑,例如,“硬法”的制定需要遵循严苛的程序,因而周期较长,且立法成本较高。另外,“硬法”所特有的滞后性导致其难以在第一时间内对新兴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法律空白”就是对这种情形的真实写照。这一系列现象,被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生动地称为“硬法失范”。所谓“失范”,即指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之间的非均衡性。随着“硬法失范”现象的不断蔓延,法学家们意识到,必须要对传统的法律概念进行修正。在此种背景下,“软法”理念应运而生,即“在全球范围内,法学家们对软法的关注源于‘法律社会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股声势蓬勃的现代法律思潮中,矛头直指传统的‘硬法’,并对国家立法中心主义模式作出批判”[2]。“软法”概念最早凸显于20世纪中期的国际法领域,该概念一经创设,就释放出强大的话语影响力,它不但颠覆了旧的法律范式,同时也与“硬法”一道构成了法治资源类型中的核心概念。“软法”之“软”,并非在于其对社会生活不具备调控能力,而是指它在对社会场域进行调整时,主要依靠组织强制、内心强制等柔性方式来保障其效力的实现。与国际社会对“软法”的研究热潮相比,国内学者对“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