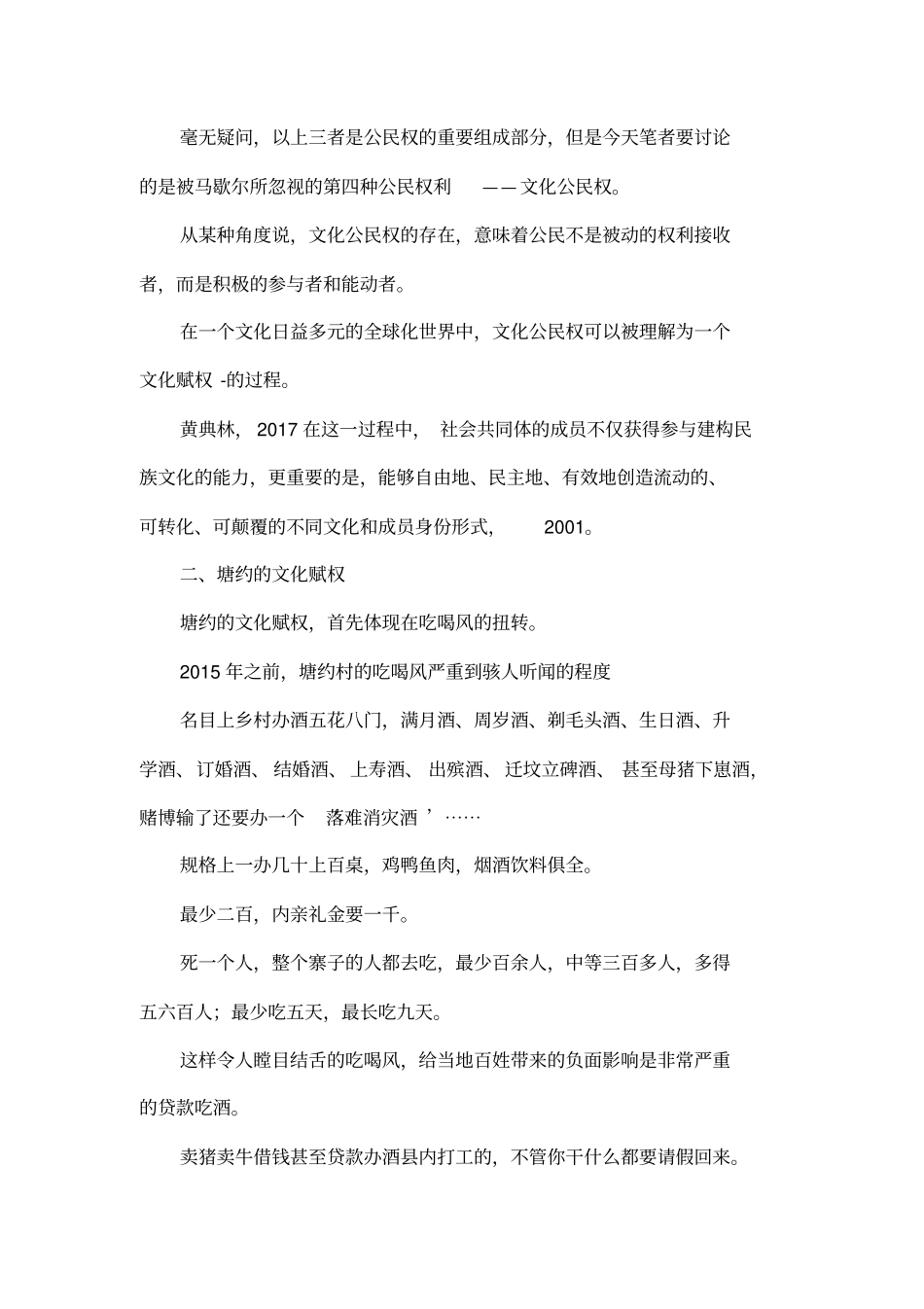《塘约道路》读后感:塘约的文化公民权塘约的文化公民权——《塘约道路》读后感云霆《塘约道路》是福建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此书记录了三年来福建省安顺市塘约村从2014年到2016年发生的剧烈变革。变革的核心是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这场变革是当今中国农村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在塘约的改革中,文化公民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内容,也是笔者今天讨论的核心。一、公民权与文化公民权关于公民权的定义,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准确的共识,但是大体来讲,人们一般认为公民权涉及的一个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成员的身份和归属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权利与义务。至于对现代公民权所包含的具体权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马歇尔认为现代公民权分为三个不同层面民事、政治和社会,1998。毫无疑问,以上三者是公民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今天笔者要讨论的是被马歇尔所忽视的第四种公民权利——文化公民权。从某种角度说,文化公民权的存在,意味着公民不是被动的权利接收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能动者。在一个文化日益多元的全球化世界中,文化公民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文化赋权-的过程。黄典林,2017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不仅获得参与建构民族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民主地、有效地创造流动的、可转化、可颠覆的不同文化和成员身份形式,2001。二、塘约的文化赋权塘约的文化赋权,首先体现在吃喝风的扭转。2015年之前,塘约村的吃喝风严重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名目上乡村办酒五花八门,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出殡酒、迁坟立碑酒、甚至母猪下崽酒,赌博输了还要办一个‘落难消灾酒’⋯⋯规格上一办几十上百桌,鸡鸭鱼肉,烟酒饮料俱全。最少二百,内亲礼金要一千。死一个人,整个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得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长吃九天。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吃喝风,给当地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贷款吃酒。卖猪卖牛借钱甚至贷款办酒县内打工的,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请假回来。一请一周,要请人去代班,你150元一天的工资,请人去替要花250到3000元,不然你回去就没那个岗位了。能不来赴宴吗?不能。最不能不来的就是丧宴。不来,你会被看作不敬老人。从理论上说,塘约的村民当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变这种吃喝风。但是从客观条件来讲,一个形成多年的歪风邪气,基本不可能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条件下自发改变。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它背后的深层原因穷民无奈,虽知酒宴泛滥谁都难逃‘酒债’,仍不放过眼前操办可以立聚一笔钱。穷村便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塘约之所以能够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大洪水这一天灾之后,村支书左文学和一众村干部的猛然觉醒。当然,天灾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促成改变的,还是左文学十几年来目睹塘约村积贫积弱的现实之后,总结的经验和协定的决心。量变引发质变。塘约的文化赋权过程并不复杂,村干部制定了村规民约,规定了红九条,也就是九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条就是不准乱办酒席。同时,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只允许办结婚酒和丧葬酒,其他一律禁止。而这两种的规格也有严格的限制,细节甚至精确到不上瓶子酒。不发整包烟。这一举措立竿见影,之前一年办酒要花3000万,现在只要60万。吃喝风是多年的痼疾,为什么一年时间就可以完全刹车?笔者认为,原因有五第一,是党组织的力量。首先制定村规民约,然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讨论通过后村支两委署名,再把村规民约发到每家每户,确保每一家都学习、学会、贴上墙,并且签订承诺书。第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八项规定六条禁令出台之后,党员干部被管住了,进而也会影响到普通百姓。第三,党组织在出台这几条禁令的同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百姓们生活水平上去了,抵触情绪自然也就没有那么严重第四,是天灾。大洪水之后,虽然没有死人,但是村民的财产损失十分严重。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大办酒席了。第五,是这份痼疾只是一个风气,这是无形的东西,有形的党组织、村主任,在有形的县委书记支持下,想要改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