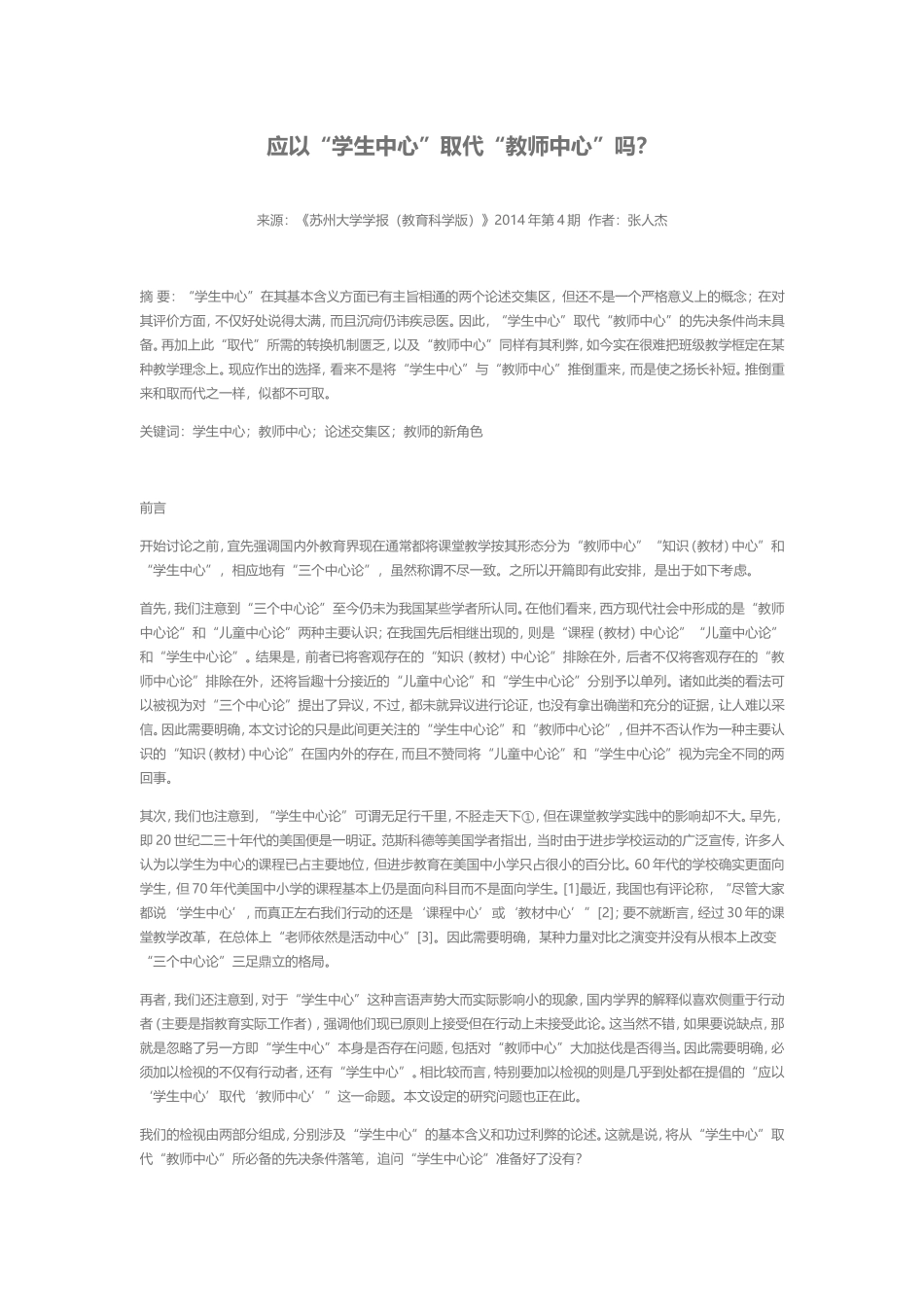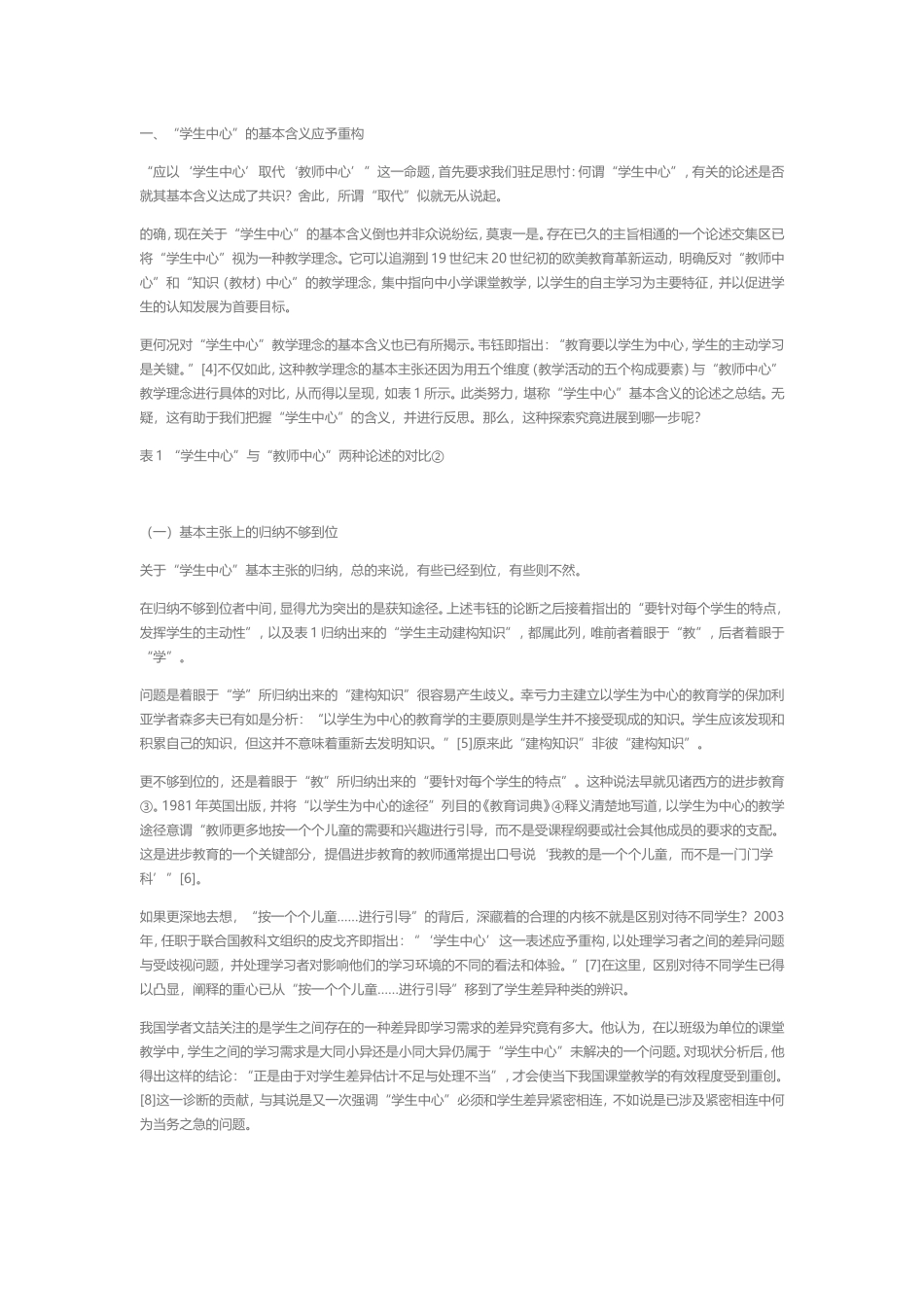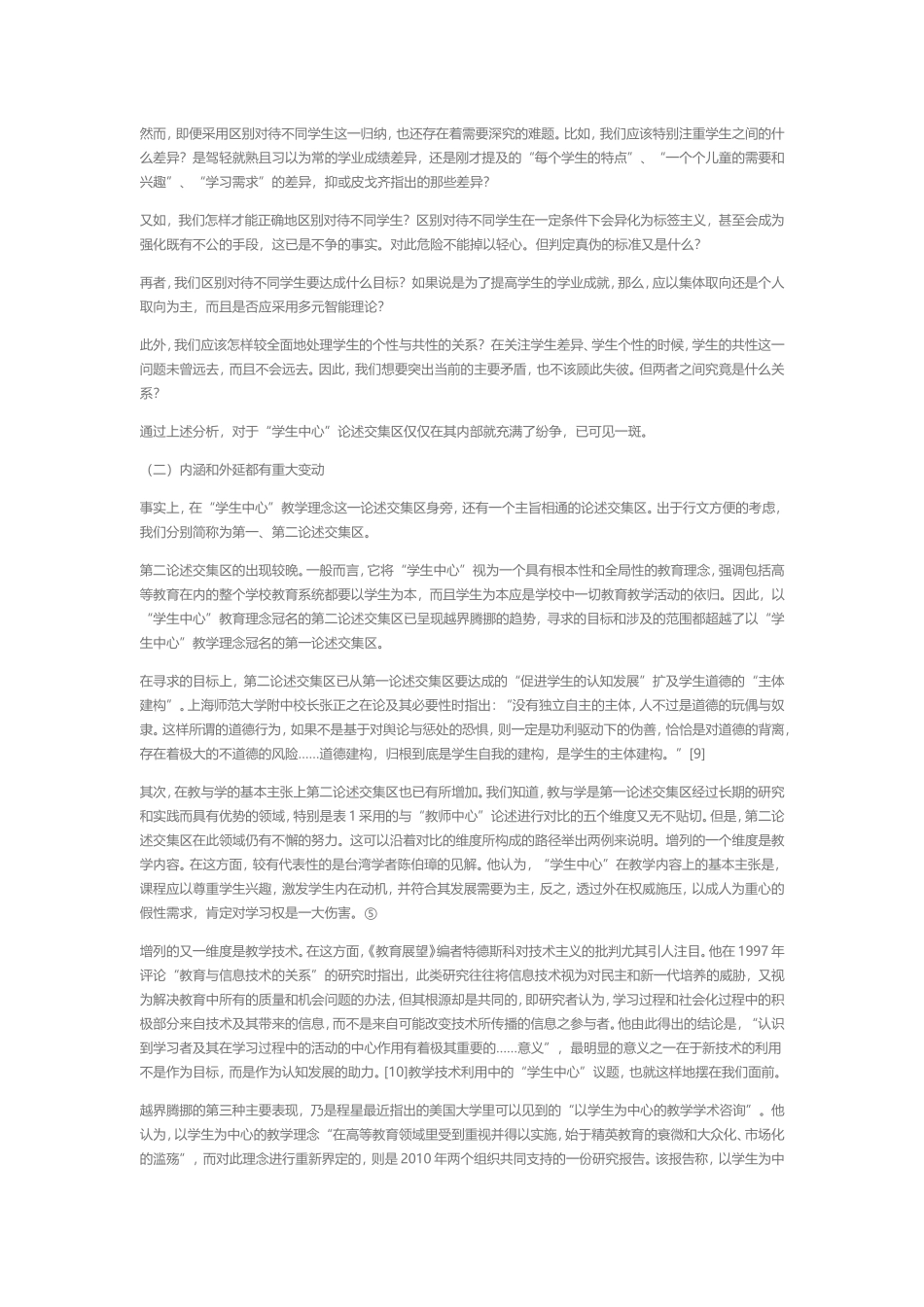应以“学生中心”取代“教师中心”吗?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4期作者:张人杰摘要:“学生中心”在其基本含义方面已有主旨相通的两个论述交集区,但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在对其评价方面,不仅好处说得太满,而且沉疴仍讳疾忌医。因此,“学生中心”取代“教师中心”的先决条件尚未具备。再加上此“取代”所需的转换机制匮乏,以及“教师中心”同样有其利弊,如今实在很难把班级教学框定在某种教学理念上。现应作出的选择,看来不是将“学生中心”与“教师中心”推倒重来,而是使之扬长补短。推倒重来和取而代之一样,似都不可取。关键词:学生中心;教师中心;论述交集区;教师的新角色前言开始讨论之前,宜先强调国内外教育界现在通常都将课堂教学按其形态分为“教师中心”“知识(教材)中心”和“学生中心”,相应地有“三个中心论”,虽然称谓不尽一致。之所以开篇即有此安排,是出于如下考虑。首先,我们注意到“三个中心论”至今仍未为我国某些学者所认同。在他们看来,西方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是“教师中心论”和“儿童中心论”两种主要认识;在我国先后相继出现的,则是“课程(教材)中心论”“儿童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结果是,前者已将客观存在的“知识(教材)中心论”排除在外,后者不仅将客观存在的“教师中心论”排除在外,还将旨趣十分接近的“儿童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分别予以单列。诸如此类的看法可以被视为对“三个中心论”提出了异议,不过,都未就异议进行论证,也没有拿出确凿和充分的证据,让人难以采信。因此需要明确,本文讨论的只是此间更关注的“学生中心论”和“教师中心论”,但并不否认作为一种主要认识的“知识(教材)中心论”在国内外的存在,而且不赞同将“儿童中心论”和“学生中心论”视为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其次,我们也注意到,“学生中心论”可谓无足行千里,不胫走天下①,但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的影响却不大。早先,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便是一明证。范斯科德等美国学者指出,当时由于进步学校运动的广泛宣传,许多人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已占主要地位,但进步教育在美国中小学只占很小的百分比。60年代的学校确实更面向学生,但70年代美国中小学的课程基本上仍是面向科目而不是面向学生。[1]最近,我国也有评论称,“尽管大家都说‘学生中心’,而真正左右我们行动的还是‘课程中心’或‘教材中心’”[2];要不就断言,经过30年的课堂教学改革,在总体上“老师依然是活动中心”[3]。因此需要明确,某种力量对比之演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个中心论”三足鼎立的格局。再者,我们还注意到,对于“学生中心”这种言语声势大而实际影响小的现象,国内学界的解释似喜欢侧重于行动者(主要是指教育实际工作者),强调他们现已原则上接受但在行动上未接受此论。这当然不错,如果要说缺点,那就是忽略了另一方即“学生中心”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包括对“教师中心”大加挞伐是否得当。因此需要明确,必须加以检视的不仅有行动者,还有“学生中心”。相比较而言,特别要加以检视的则是几乎到处都在提倡的“应以‘学生中心’取代‘教师中心’”这一命题。本文设定的研究问题也正在此。我们的检视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涉及“学生中心”的基本含义和功过利弊的论述。这就是说,将从“学生中心”取代“教师中心”所必备的先决条件落笔,追问“学生中心论”准备好了没有?一、“学生中心”的基本含义应予重构“应以‘学生中心’取代‘教师中心’”这一命题,首先要求我们驻足思忖:何谓“学生中心”,有关的论述是否就其基本含义达成了共识?舍此,所谓“取代”似就无从说起。的确,现在关于“学生中心”的基本含义倒也并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在已久的主旨相通的一个论述交集区已将“学生中心”视为一种教学理念。它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教育革新运动,明确反对“教师中心”和“知识(教材)中心”的教学理念,集中指向中小学课堂教学,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要特征,并以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为首要目标。更何况对“学生中心”教学理念的基本含义也已有所揭示。韦钰即指出:“教育要以学生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