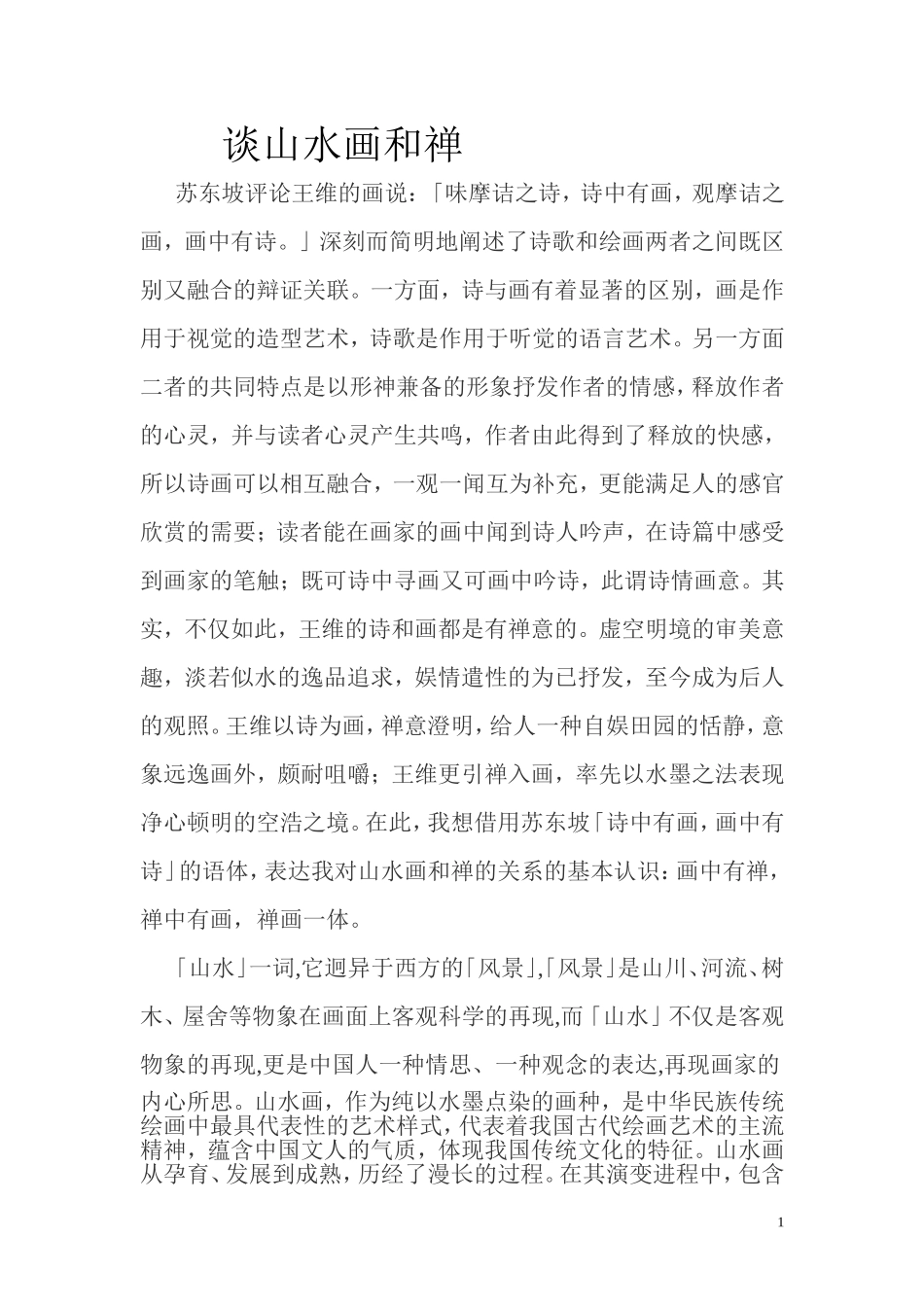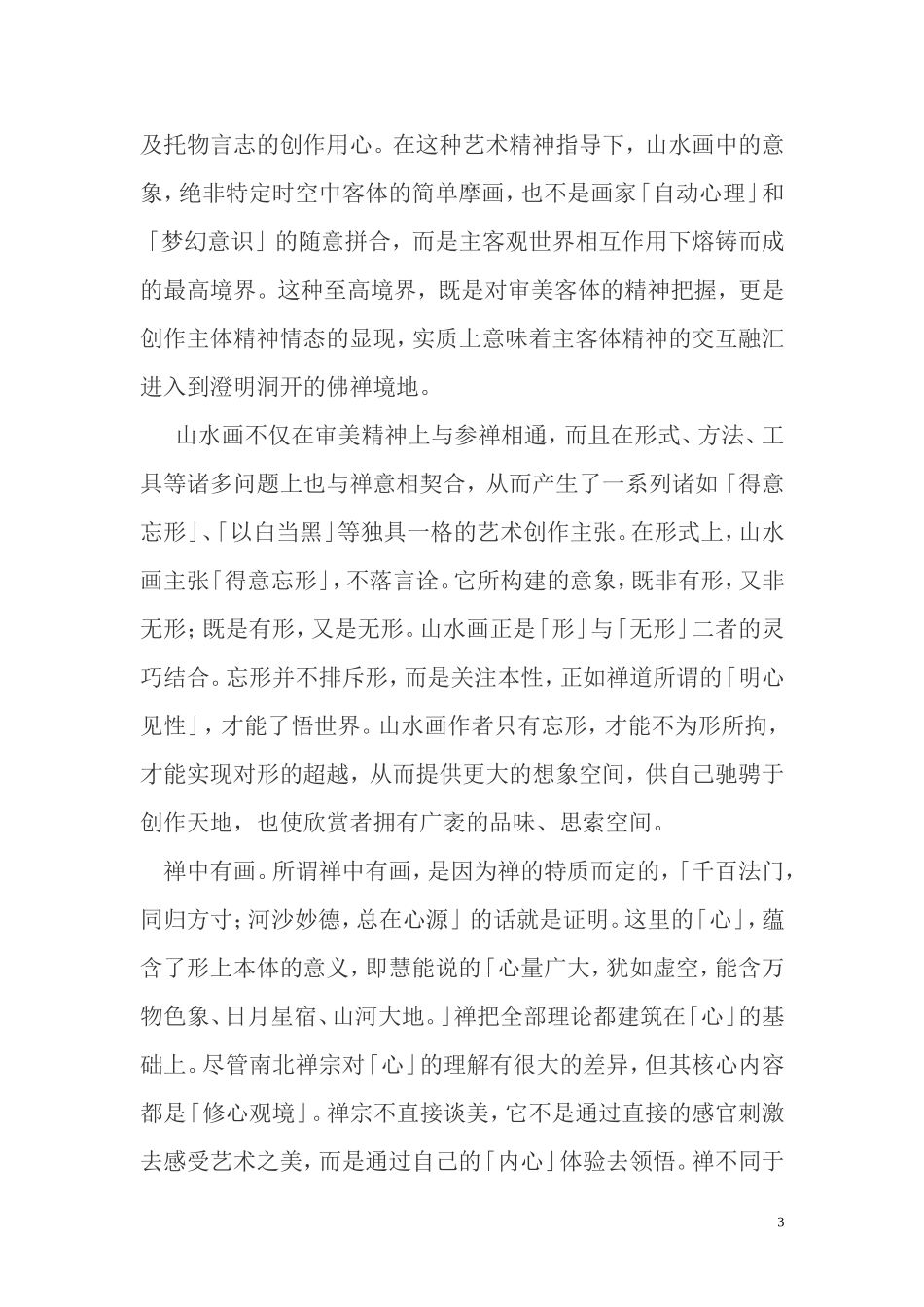1谈山水画和禅苏东坡评论王维的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深刻而简明地阐述了诗歌和绘画两者之间既区别又融合的辩证关联。一方面,诗与画有着显著的区别,画是作用于视觉的造型艺术,诗歌是作用于听觉的语言艺术。另一方面二者的共同特点是以形神兼备的形象抒发作者的情感,释放作者的心灵,并与读者心灵产生共鸣,作者由此得到了释放的快感,所以诗画可以相互融合,一观一闻互为补充,更能满足人的感官欣赏的需要;读者能在画家的画中闻到诗人吟声,在诗篇中感受到画家的笔触;既可诗中寻画又可画中吟诗,此谓诗情画意。其实,不仅如此,王维的诗和画都是有禅意的。虚空明境的审美意趣,淡若似水的逸品追求,娱情遣性的为已抒发,至今成为后人的观照。王维以诗为画,禅意澄明,给人一种自娱田园的恬静,意象远逸画外,颇耐咀嚼;王维更引禅入画,率先以水墨之法表现净心顿明的空浩之境。在此,我想借用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语体,表达我对山水画和禅的关系的基本认识:画中有禅,禅中有画,禅画一体。「山水」一词,它迥异于西方的「风景」,「风景」是山川、河流、树木、屋舍等物象在画面上客观科学的再现,而「山水」不仅是客观物象的再现,更是中国人一种情思、一种观念的表达,再现画家的内心所思。山水画,作为纯以水墨点染的画种,是中华民族传统绘画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样式,代表着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主流精神,蕴含中国文人的气质,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山水画从孕育、发展到成熟,历经了漫长的过程。在其演变进程中,包含2着艺术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哲学的滋养、天才的创造、时代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变革等,但仅仅就山水画所浸润的理念来看我感到,山水画所体现的形式、所涵蓄的一切都与禅密不可分。禅,梵语(dhyana)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以思想生起变化,发动意念起作用;也就是运用思想、发挥智慧的一种外静内动的行为。其思想渊源于古代印度,以瑜伽(yaoga)精神集中的方法,来体悟宇宙的智慧。所以至今禅没有一种明确的定义。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是错」。「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以心传心。禅没有是与不是、高与低、好与坏。禅的体验,非知识、非理论,是超越知识思维、超越历史事实,而注重实证的。宗白华先生说过:「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底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禅宗属于宗教,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禅更是一种人生哲学、心灵哲学,其「如梦如幻」的人生观,足以解脱人们灵与肉的苦恼困境,而参禅入定的内心体验,可以进入艺术创造所需的心醉神迷的境界。画中有禅。北宋画家、山水画理论家郭熙《山水训》:「真山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是从一个画家的视角借用雾气的不同特点来描写四季山峦景色,更为重要的是,四季山峦景色被赋予了自然的情怀、情感和精神气质。所谓画中有禅,正是山水画中这种对画家精神和格调的自然而本意的反映,以及山水画中蕴含的意境、禅意。山水画能够依附水墨,彰显画家自我性情,同时又使万物气象性情凸现。禅宗本有净性自悟说,它强调人的真如本性顿现,就能同时包容万事万物,也就成为洁净法身。山水画大抵强调直观与感悟,注重体验,超越表象,主张超脱,物我合一,注重修养,讲求气骨,形成其宏观求整的思维方式,情景交融的意象构建,以3及托物言志的创作用心。在这种艺术精神指导下,山水画中的意象,绝非特定时空中客体的简单摩画,也不是画家「自动心理」和「梦幻意识」的随意拼合,而是主客观世界相互作用下熔铸而成的最高境界。这种至高境界,既是对审美客体的精神把握,更是创作主体精神情态的显现,实质上意味着主客体精神的交互融汇进入到澄明洞开的佛禅境地。山水画不仅在审美精神上与参禅相通,而且在形式、方法、工具等诸多问题上也与禅意相契合,从而产生了一系列诸如「得意忘形」、「以白当黑」等独具一格的艺术创作主张。在形式上,山水画主张「得意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