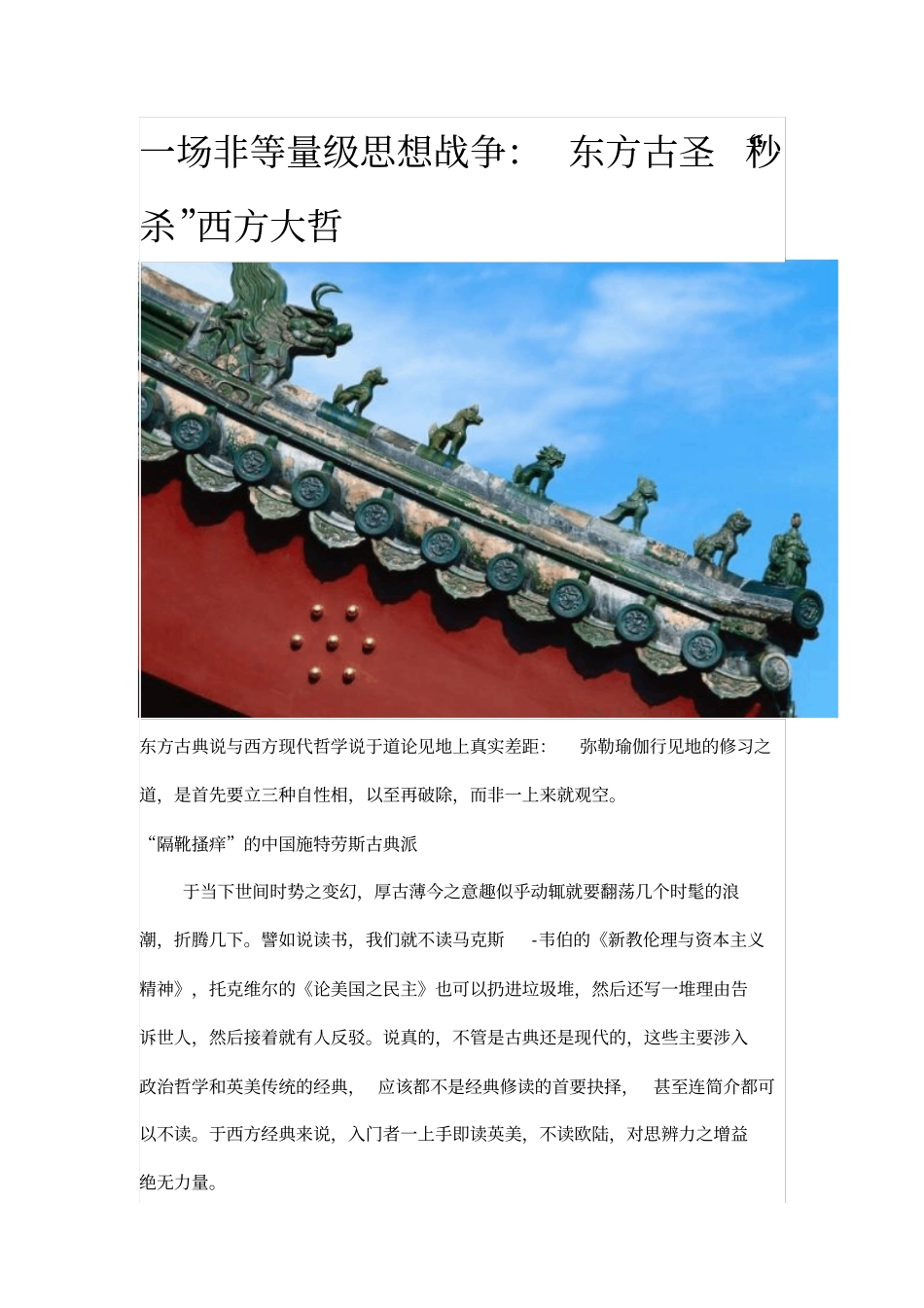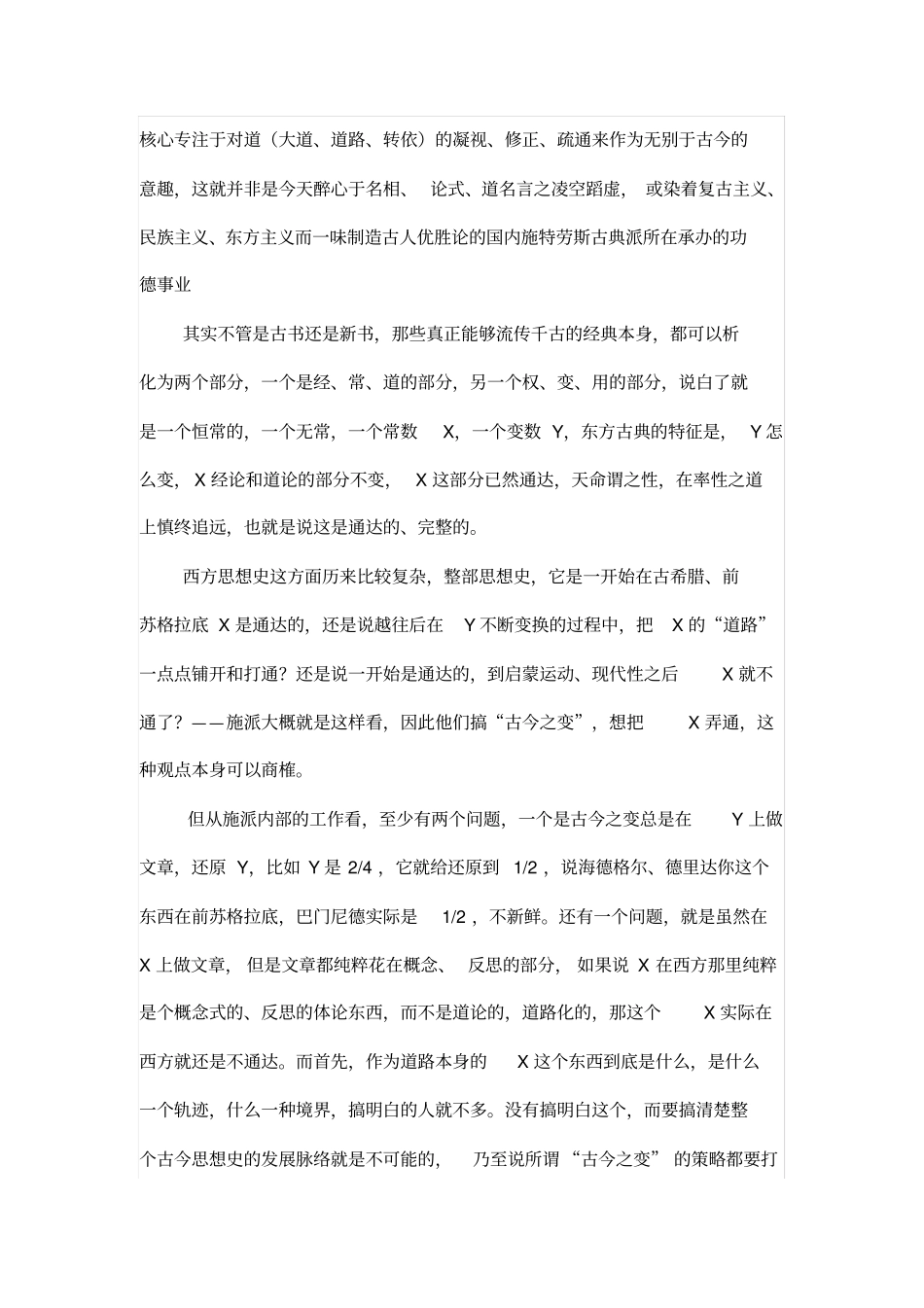一场非等量级思想战争:东方古圣“秒杀”西方大哲东方古典说与西方现代哲学说于道论见地上真实差距:弥勒瑜伽行见地的修习之道,是首先要立三种自性相,以至再破除,而非一上来就观空。“隔靴搔痒”的中国施特劳斯古典派于当下世间时势之变幻,厚古薄今之意趣似乎动辄就要翻荡几个时髦的浪潮,折腾几下。譬如说读书,我们就不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之民主》也可以扔进垃圾堆,然后还写一堆理由告诉世人,然后接着就有人反驳。说真的,不管是古典还是现代的,这些主要涉入政治哲学和英美传统的经典,应该都不是经典修读的首要抉择,甚至连简介都可以不读。于西方经典来说,入门者一上手即读英美,不读欧陆,对思辨力之增益绝无力量。我自觉这些对人类平面世界之关注论义的所谓经典,结其所欲谈论的,无非就是这平面世界的无常、生住坏灭之遍计所执相而已。而按《入楞伽经》所云,那可周遍一切蕴、处、界之“真实”;或如《解深密经》所云,周遍轮回涅槃二界“了知一切清净相法”;再依世亲释论《辨中边论》所云,离无二有无之“真如”、“胜义性”、“诸法空相”——这些亦概括其涵指可谓之探究人类“心性”之究竟,同一宇宙“法界”之实相究极的超越生死之法,却在今天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的高歌猛进,以及哲学学院工业生产的阴霾深渊之中,被斥之为“宗教娱乐”式的循规蹈矩、咿咿呀呀的“精神寄托”,或者被荒芜漠远为异域原始的边缘呓语。由此今天的人类却不得不重新追求何为哲学的问题。在究竟思想的意义上可谓之“哲学”的人类真实事业,首要的不是关于政治的“天命发送”,更不是仅在逻辑、名相的推理、辨别、分析的理性、比量的虚幻网络中构建起的人文社科化的哲学,而应是在古希腊和现象学还原视域之中被追问的关于On、Sein的存在学(Ontologia)问题,亦即还原之“溯源”的问题。于所缘世间表象的外境,层层趋向内在真实的明见性还原。此在深微奥古之东方思想经典中更包含有甚深广大之通达的见地:龙树中观以四重缘起(业因缘起、相依缘起、相对缘起、相碍缘起)说空性了义真实、最高见地之如来藏体性,亦有弥勒瑜伽行(唯识古学)以法相、唯识、如来藏三种见地任运成就“入无分别界”,宁玛派大圆满亦有三虚空禅定(外空、内空、密空)等以为上达内自证智境⋯⋯;老庄亦以坐忘大道(大、逝、远、反)入神解之境——一个止观、坐忘的证量、修证问题。如此这样说下去,好像非得要与刘小枫、甘阳的时髦亲热起来。但如果说,核心专注于对道(大道、道路、转依)的凝视、修正、疏通来作为无别于古今的意趣,这就并非是今天醉心于名相、论式、道名言之凌空蹈虚,或染着复古主义、民族主义、东方主义而一味制造古人优胜论的国内施特劳斯古典派所在承办的功德事业其实不管是古书还是新书,那些真正能够流传千古的经典本身,都可以析化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经、常、道的部分,另一个权、变、用的部分,说白了就是一个恒常的,一个无常,一个常数X,一个变数Y,东方古典的特征是,Y怎么变,X经论和道论的部分不变,X这部分已然通达,天命谓之性,在率性之道上慎终追远,也就是说这是通达的、完整的。西方思想史这方面历来比较复杂,整部思想史,它是一开始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X是通达的,还是说越往后在Y不断变换的过程中,把X的“道路”一点点铺开和打通?还是说一开始是通达的,到启蒙运动、现代性之后X就不通了?——施派大概就是这样看,因此他们搞“古今之变”,想把X弄通,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商榷。但从施派内部的工作看,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古今之变总是在Y上做文章,还原Y,比如Y是2/4,它就给还原到1/2,说海德格尔、德里达你这个东西在前苏格拉底,巴门尼德实际是1/2,不新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在X上做文章,但是文章都纯粹花在概念、反思的部分,如果说X在西方那里纯粹是个概念式的、反思的体论东西,而不是道论的,道路化的,那这个X实际在西方就还是不通达。而首先,作为道路本身的X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一个轨迹,什么一种境界,搞明白的人就不多。没有搞明白这个,而要搞清楚整个古今思想史的发展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