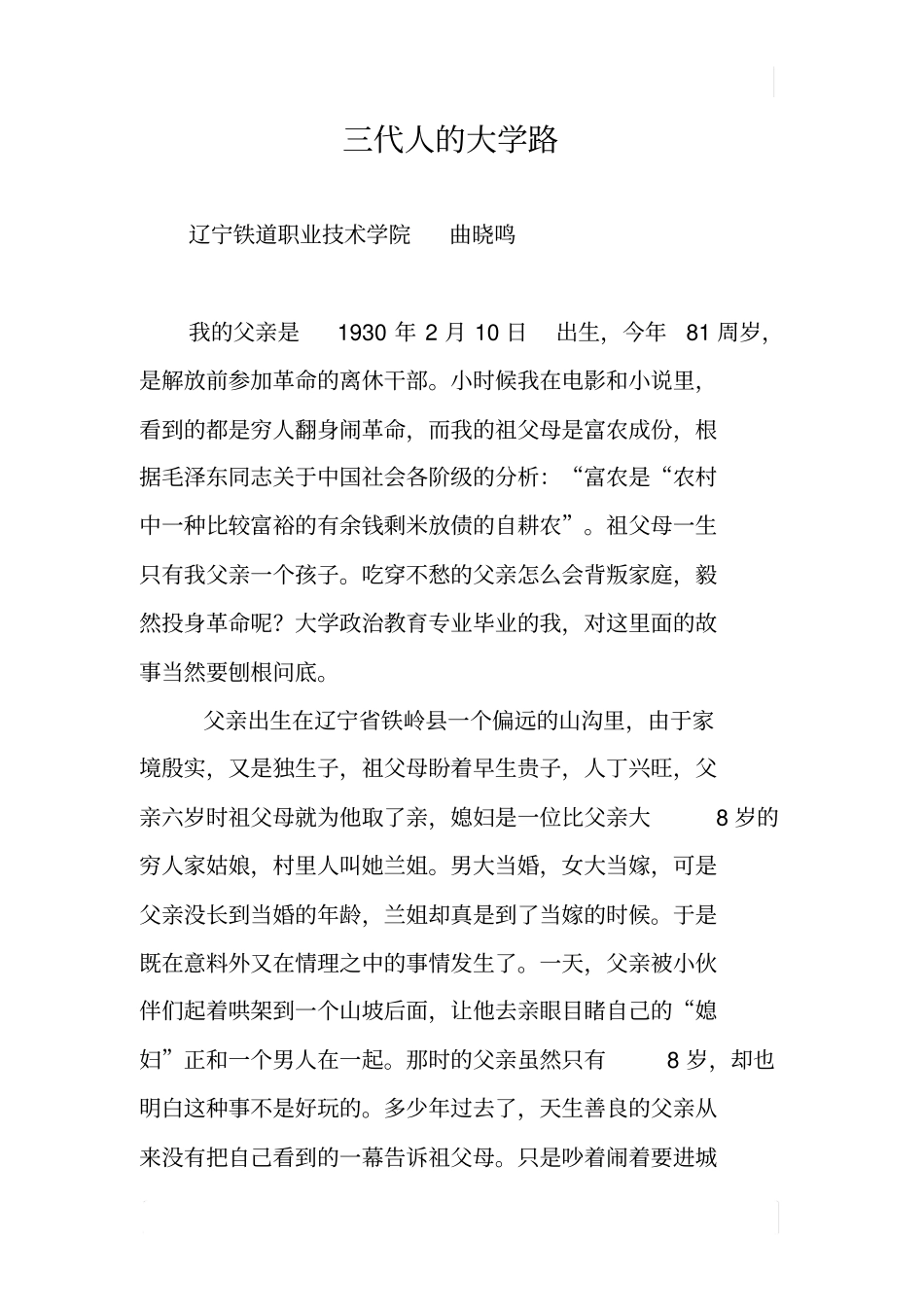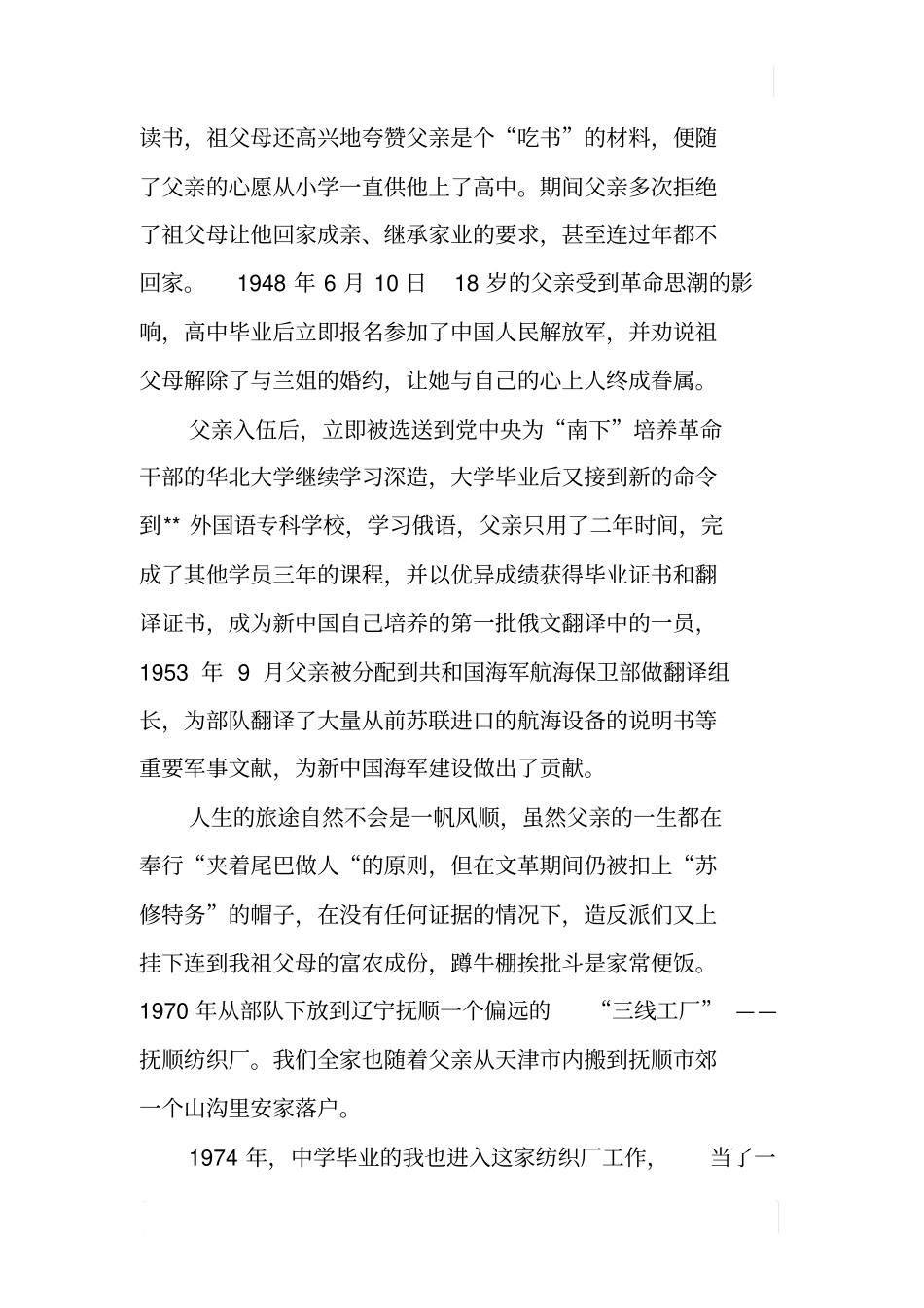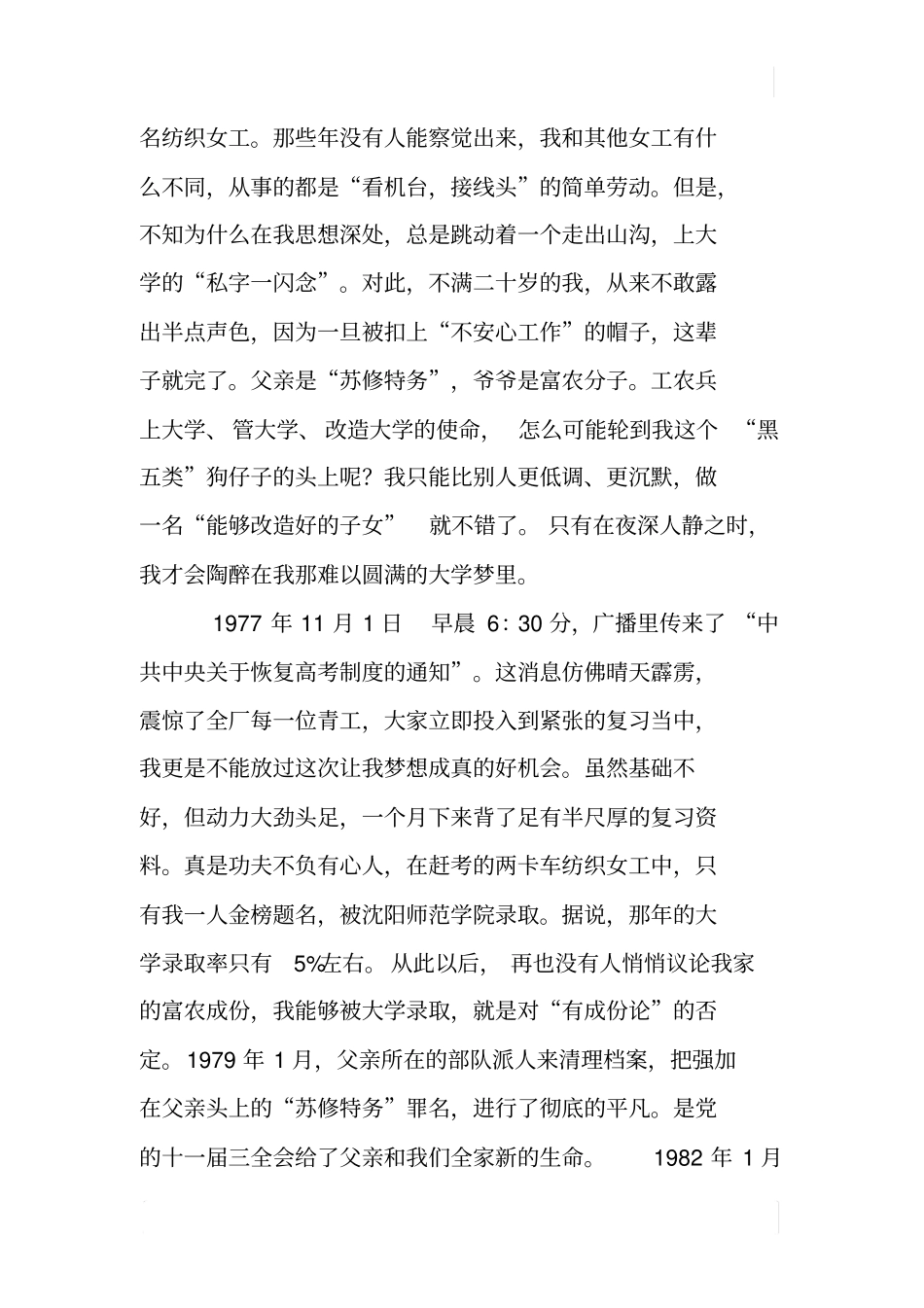三代人的大学路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曲晓鸣我的父亲是1930年2月10日出生,今年81周岁,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小时候我在电影和小说里,看到的都是穷人翻身闹革命,而我的祖父母是富农成份,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富农是“农村中一种比较富裕的有余钱剩米放债的自耕农”。祖父母一生只有我父亲一个孩子。吃穿不愁的父亲怎么会背叛家庭,毅然投身革命呢?大学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的我,对这里面的故事当然要刨根问底。父亲出生在辽宁省铁岭县一个偏远的山沟里,由于家境殷实,又是独生子,祖父母盼着早生贵子,人丁兴旺,父亲六岁时祖父母就为他取了亲,媳妇是一位比父亲大8岁的穷人家姑娘,村里人叫她兰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父亲没长到当婚的年龄,兰姐却真是到了当嫁的时候。于是既在意料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发生了。一天,父亲被小伙伴们起着哄架到一个山坡后面,让他去亲眼目睹自己的“媳妇”正和一个男人在一起。那时的父亲虽然只有8岁,却也明白这种事不是好玩的。多少年过去了,天生善良的父亲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到的一幕告诉祖父母。只是吵着闹着要进城读书,祖父母还高兴地夸赞父亲是个“吃书”的材料,便随了父亲的心愿从小学一直供他上了高中。期间父亲多次拒绝了祖父母让他回家成亲、继承家业的要求,甚至连过年都不回家。1948年6月10日18岁的父亲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高中毕业后立即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劝说祖父母解除了与兰姐的婚约,让她与自己的心上人终成眷属。父亲入伍后,立即被选送到党中央为“南下”培养革命干部的华北大学继续学习深造,大学毕业后又接到新的命令到**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父亲只用了二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学员三年的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获得毕业证书和翻译证书,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俄文翻译中的一员,1953年9月父亲被分配到共和国海军航海保卫部做翻译组长,为部队翻译了大量从前苏联进口的航海设备的说明书等重要军事文献,为新中国海军建设做出了贡献。人生的旅途自然不会是一帆风顺,虽然父亲的一生都在奉行“夹着尾巴做人“的原则,但在文革期间仍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造反派们又上挂下连到我祖父母的富农成份,蹲牛棚挨批斗是家常便饭。1970年从部队下放到辽宁抚顺一个偏远的“三线工厂”——抚顺纺织厂。我们全家也随着父亲从天津市内搬到抚顺市郊一个山沟里安家落户。1974年,中学毕业的我也进入这家纺织厂工作,当了一名纺织女工。那些年没有人能察觉出来,我和其他女工有什么不同,从事的都是“看机台,接线头”的简单劳动。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我思想深处,总是跳动着一个走出山沟,上大学的“私字一闪念”。对此,不满二十岁的我,从来不敢露出半点声色,因为一旦被扣上“不安心工作”的帽子,这辈子就完了。父亲是“苏修特务”,爷爷是富农分子。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使命,怎么可能轮到我这个“黑五类”狗仔子的头上呢?我只能比别人更低调、更沉默,做一名“能够改造好的子女”就不错了。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我才会陶醉在我那难以圆满的大学梦里。1977年11月1日早晨6:30分,广播里传来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这消息仿佛晴天霹雳,震惊了全厂每一位青工,大家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当中,我更是不能放过这次让我梦想成真的好机会。虽然基础不好,但动力大劲头足,一个月下来背了足有半尺厚的复习资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赶考的两卡车纺织女工中,只有我一人金榜题名,被沈阳师范学院录取。据说,那年的大学录取率只有5%左右。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悄悄议论我家的富农成份,我能够被大学录取,就是对“有成份论”的否定。1979年1月,父亲所在的部队派人来清理档案,把强加在父亲头上的“苏修特务”罪名,进行了彻底的平凡。是党的十一届三全会给了父亲和我们全家新的生命。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并有了自己幸福的三口之家。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我的女儿又顺利考上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她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所在的高中也不是重点。但她却赶上了祖国繁荣昌盛的好时代。随着国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