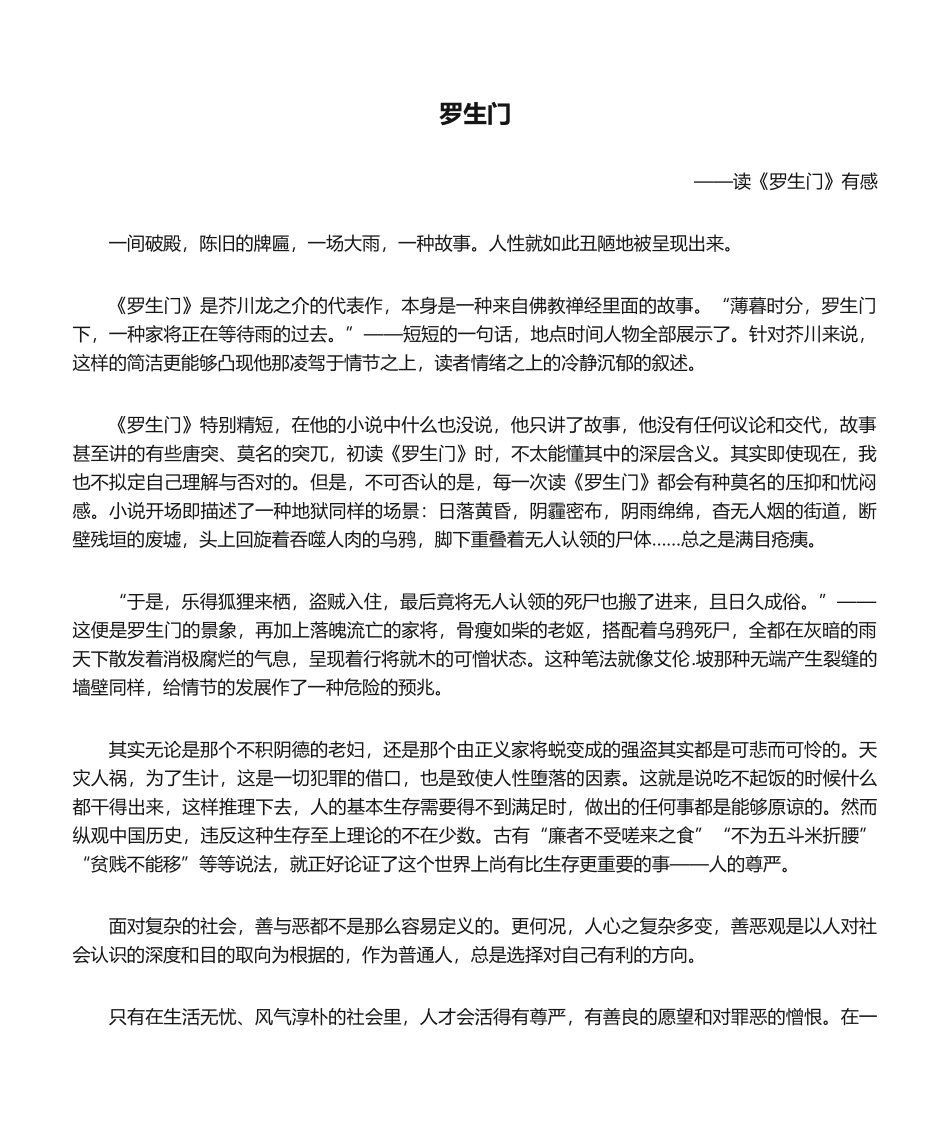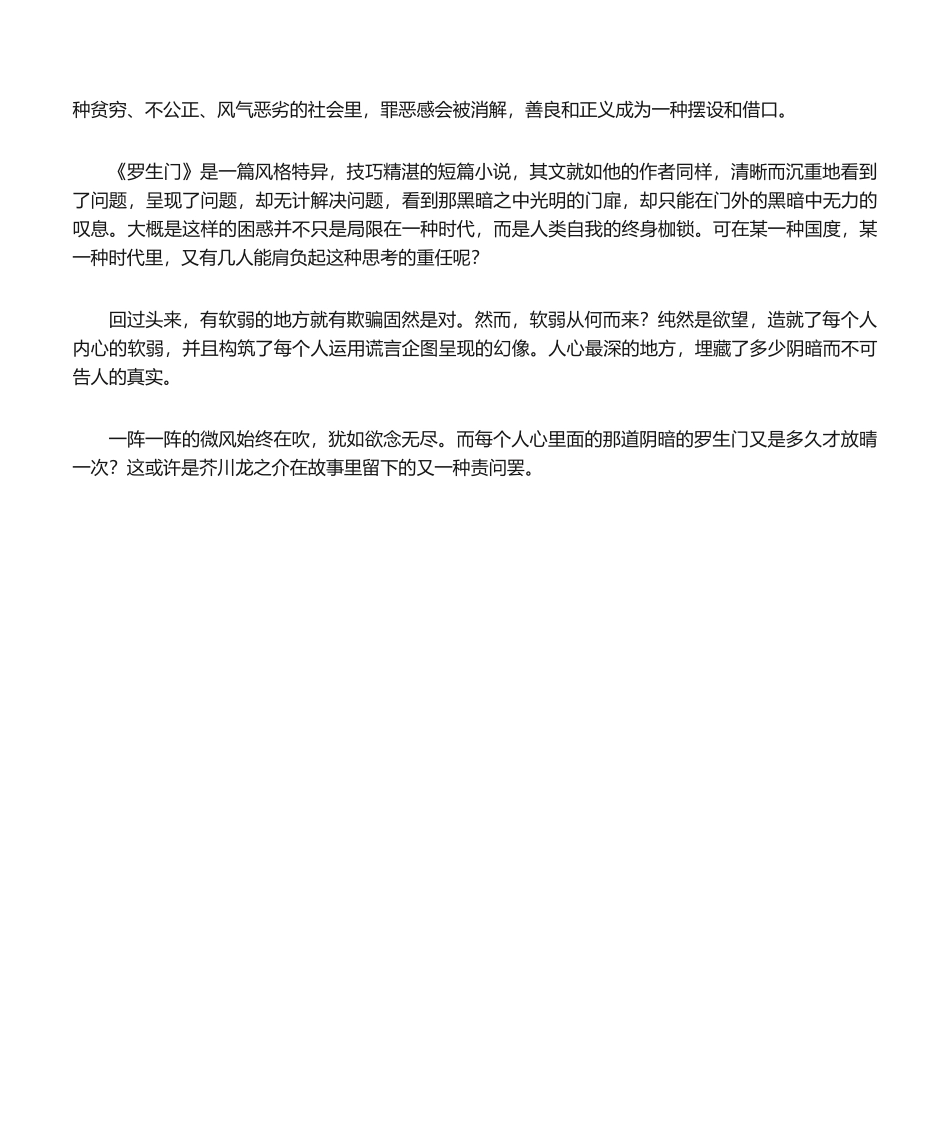罗生门——读《罗生门》有感一间破殿,陈旧的牌匾,一场大雨,一种故事。人性就如此丑陋地被呈现出来。《罗生门》是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本身是一种来自佛教禅经里面的故事。“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一种家将正在等待雨的过去。”——短短的一句话,地点时间人物全部展示了。针对芥川来说,这样的简洁更能够凸现他那凌驾于情节之上,读者情绪之上的冷静沉郁的叙述。《罗生门》特别精短,在他的小说中什么也没说,他只讲了故事,他没有任何议论和交代,故事甚至讲的有些唐突、莫名的突兀,初读《罗生门》时,不太能懂其中的深层含义。其实即使现在,我也不拟定自己理解与否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一次读《罗生门》都会有种莫名的压抑和忧闷感。小说开场即描述了一种地狱同样的场景:日落黄昏,阴霾密布,阴雨绵绵,杳无人烟的街道,断壁残垣的废墟,头上回旋着吞噬人肉的乌鸦,脚下重叠着无人认领的尸体……总之是满目疮痍。“于是,乐得狐狸来栖,盗贼入住,最后竟将无人认领的死尸也搬了进来,且日久成俗。”——这便是罗生门的景象,再加上落魄流亡的家将,骨瘦如柴的老妪,搭配着乌鸦死尸,全都在灰暗的雨天下散发着消极腐烂的气息,呈现着行将就木的可憎状态。这种笔法就像艾伦.坡那种无端产生裂缝的墙壁同样,给情节的发展作了一种危险的预兆。其实无论是那个不积阴德的老妇,还是那个由正义家将蜕变成的强盗其实都是可悲而可怜的。天灾人祸,为了生计,这是一切犯罪的借口,也是致使人性堕落的因素。这就是说吃不起饭的时候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样推理下去,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做出的任何事都是能够原谅的。然而纵观中国历史,违反这种生存至上理论的不在少数。古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贫贱不能移”等等说法,就正好论证了这个世界上尚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事——人的尊严。面对复杂的社会,善与恶都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更何况,人心之复杂多变,善恶观是以人对社会认识的深度和目的取向为根据的,作为普通人,总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只有在生活无忧、风气淳朴的社会里,人才会活得有尊严,有善良的愿望和对罪恶的憎恨。在一种贫穷、不公正、风气恶劣的社会里,罪恶感会被消解,善良和正义成为一种摆设和借口。《罗生门》是一篇风格特异,技巧精湛的短篇小说,其文就如他的作者同样,清晰而沉重地看到了问题,呈现了问题,却无计解决问题,看到那黑暗之中光明的门扉,却只能在门外的黑暗中无力的叹息。大概是这样的困惑并不只是局限在一种时代,而是人类自我的终身枷锁。可在某一种国度,某一种时代里,又有几人能肩负起这种思考的重任呢?回过头来,有软弱的地方就有欺骗固然是对。然而,软弱从何而来?纯然是欲望,造就了每个人内心的软弱,并且构筑了每个人运用谎言企图呈现的幻像。人心最深的地方,埋藏了多少阴暗而不可告人的真实。一阵一阵的微风始终在吹,犹如欲念无尽。而每个人心里面的那道阴暗的罗生门又是多久才放晴一次?这或许是芥川龙之介在故事里留下的又一种责问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