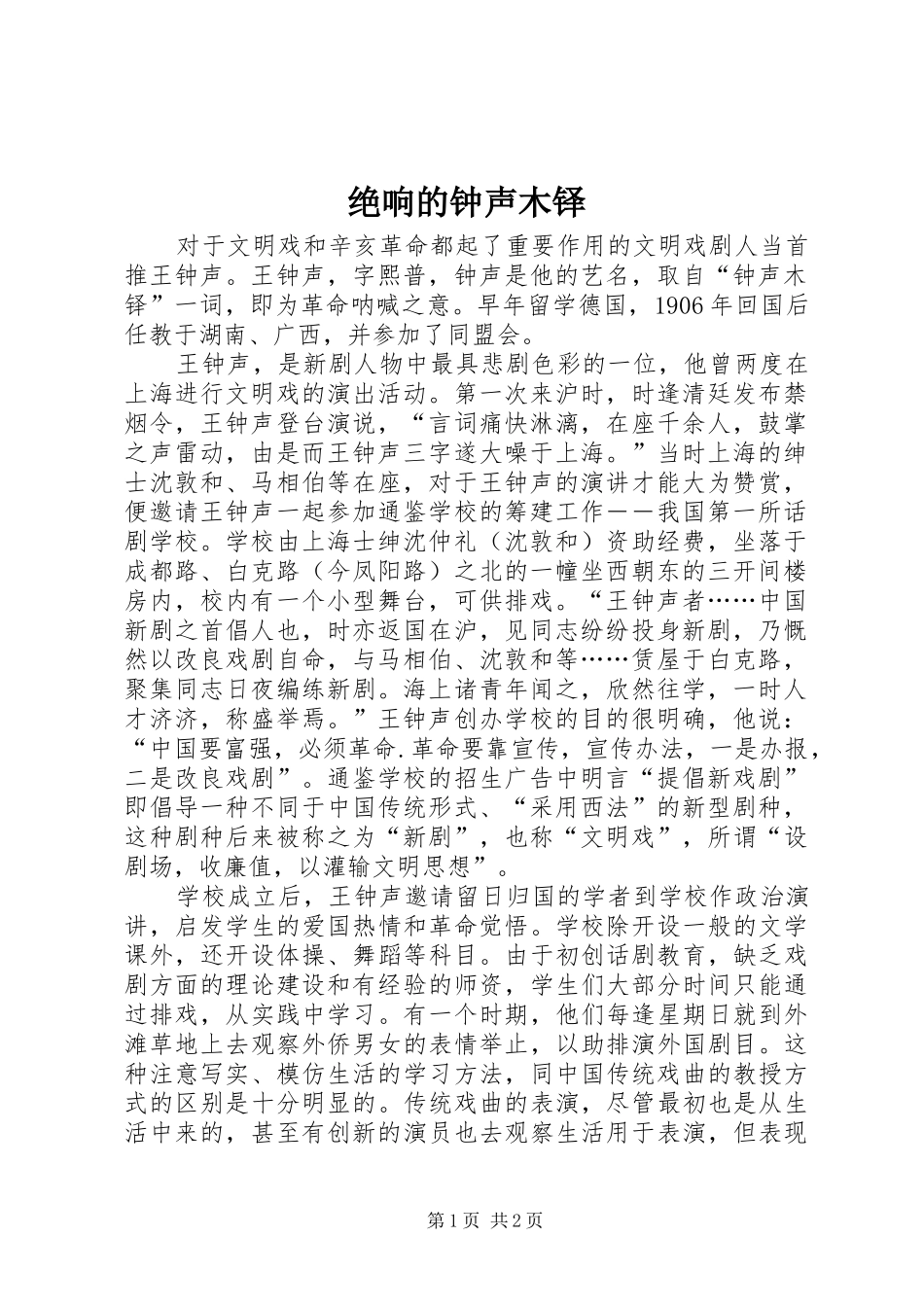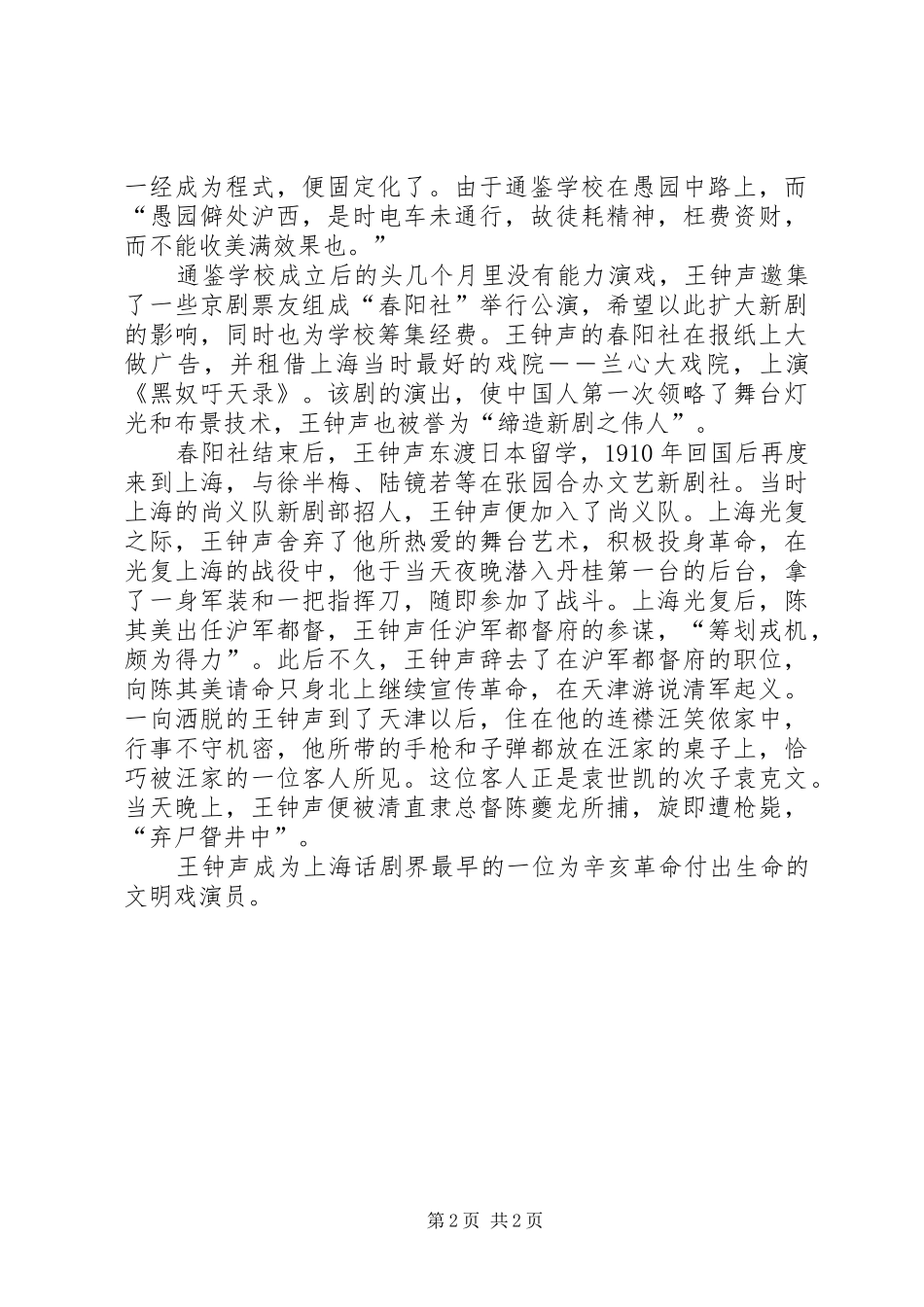绝响的钟声木铎对于文明戏和辛亥革命都起了重要作用的文明戏剧人当首推王钟声。王钟声,字熙普,钟声是他的艺名,取自“钟声木铎”一词,即为革命呐喊之意。早年留学德国,1906年回国后任教于湖南、广西,并参加了同盟会。王钟声,是新剧人物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一位,他曾两度在上海进行文明戏的演出活动。第一次来沪时,时逢清廷发布禁烟令,王钟声登台演说,“言词痛快淋漓,在座千余人,鼓掌之声雷动,由是而王钟声三字遂大噪于上海。”当时上海的绅士沈敦和、马相伯等在座,对于王钟声的演讲才能大为赞赏,便邀请王钟声一起参加通鉴学校的筹建工作――我国第一所话剧学校。学校由上海士绅沈仲礼(沈敦和)资助经费,坐落于成都路、白克路(今凤阳路)之北的一幢坐西朝东的三开间楼房内,校内有一个小型舞台,可供排戏。“王钟声者……中国新剧之首倡人也,时亦返国在沪,见同志纷纷投身新剧,乃慨然以改良戏剧自命,与马相伯、沈敦和等……赁屋于白克路,聚集同志日夜编练新剧。海上诸青年闻之,欣然往学,一时人才济济,称盛举焉。”王钟声创办学校的目的很明确,他说:“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通鉴学校的招生广告中明言“提倡新戏剧”即倡导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形式、“采用西法”的新型剧种,这种剧种后来被称之为“新剧”,也称“文明戏”,所谓“设剧场,收廉值,以灌输文明思想”。学校成立后,王钟声邀请留日归国的学者到学校作政治演讲,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学校除开设一般的文学课外,还开设体操、舞蹈等科目。由于初创话剧教育,缺乏戏剧方面的理论建设和有经验的师资,学生们大部分时间只能通过排戏,从实践中学习。有一个时期,他们每逢星期日就到外滩草地上去观察外侨男女的表情举止,以助排演外国剧目。这种注意写实、模仿生活的学习方法,同中国传统戏曲的教授方式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传统戏曲的表演,尽管最初也是从生活中来的,甚至有创新的演员也去观察生活用于表演,但表现第1页共2页一经成为程式,便固定化了。由于通鉴学校在愚园中路上,而“愚园僻处沪西,是时电车未通行,故徒耗精神,枉费资财,而不能收美满效果也。”通鉴学校成立后的头几个月里没有能力演戏,王钟声邀集了一些京剧票友组成“春阳社”举行公演,希望以此扩大新剧的影响,同时也为学校筹集经费。王钟声的春阳社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并租借上海当时最好的戏院――兰心大戏院,上演《黑奴吁天录》。该剧的演出,使中国人第一次领略了舞台灯光和布景技术,王钟声也被誉为“缔造新剧之伟人”。春阳社结束后,王钟声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回国后再度来到上海,与徐半梅、陆镜若等在张园合办文艺新剧社。当时上海的尚义队新剧部招人,王钟声便加入了尚义队。上海光复之际,王钟声舍弃了他所热爱的舞台艺术,积极投身革命,在光复上海的战役中,他于当天夜晚潜入丹桂第一台的后台,拿了一身军装和一把指挥刀,随即参加了战斗。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王钟声任沪军都督府的参谋,“筹划戎机,颇为得力”。此后不久,王钟声辞去了在沪军都督府的职位,向陈其美请命只身北上继续宣传革命,在天津游说清军起义。一向洒脱的王钟声到了天津以后,住在他的连襟汪笑侬家中,行事不守机密,他所带的手枪和子弹都放在汪家的桌子上,恰巧被汪家的一位客人所见。这位客人正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当天晚上,王钟声便被清直隶总督陈夔龙所捕,旋即遭枪毙,“弃尸眢井中”。王钟声成为上海话剧界最早的一位为辛亥革命付出生命的文明戏演员。第2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