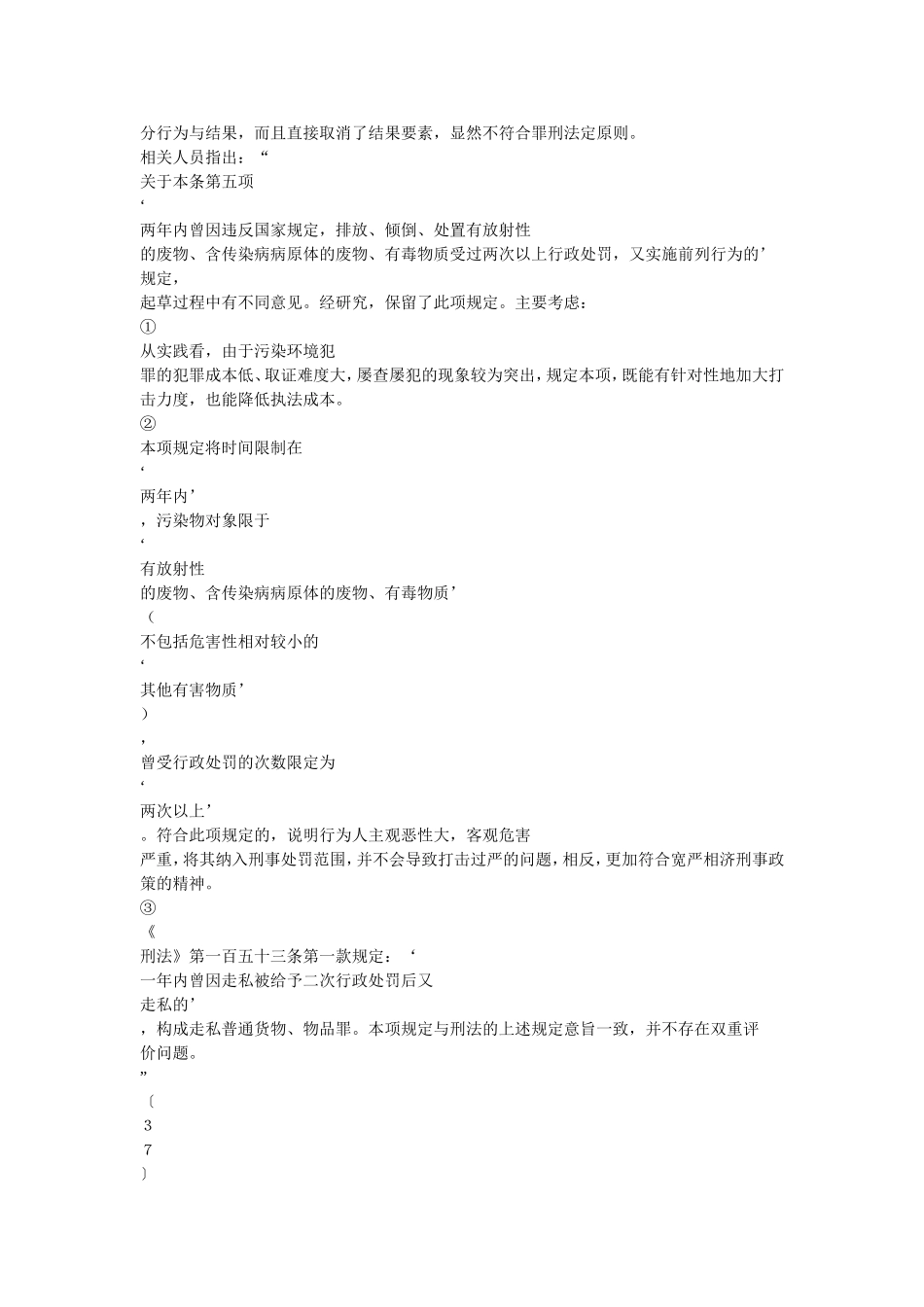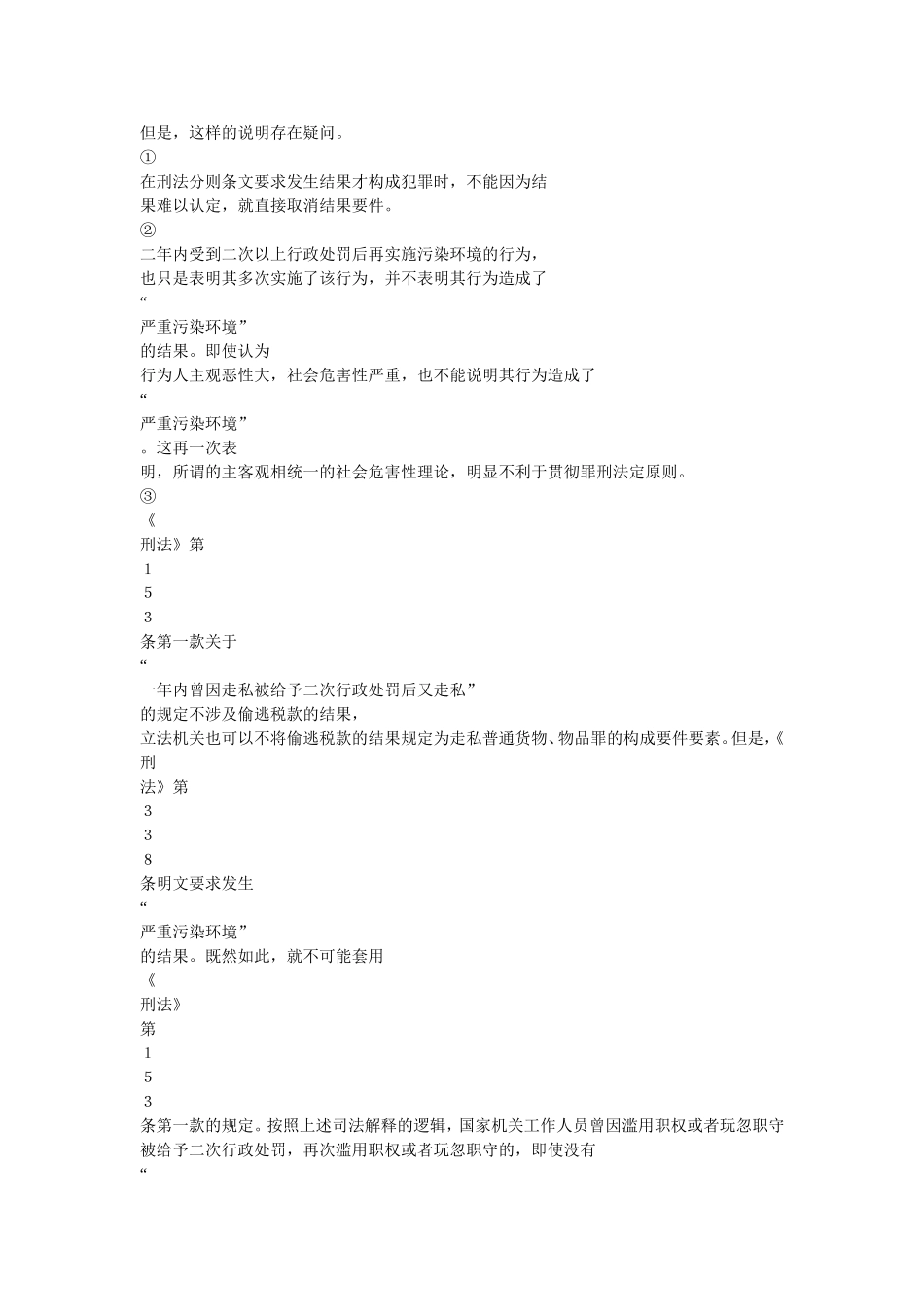分行为与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相关人员指出:“关于本条第五项‘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规定,起草过程中有不同意见。经研究,保留了此项规定。主要考虑:①从实践看,由于污染环境犯罪的犯罪成本低、取证难度大,屡查屡犯的现象较为突出,规定本项,既能有针对性地加大打击力度,也能降低执法成本。②本项规定将时间限制在‘两年内’,污染物对象限于‘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不包括危害性相对较小的‘其他有害物质’),曾受行政处罚的次数限定为‘两次以上’。符合此项规定的,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客观危害严重,将其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并不会导致打击过严的问题,相反,更加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③《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本项规定与刑法的上述规定意旨一致,并不存在双重评价问题。”〔37〕但是,这样的说明存在疑问。①在刑法分则条文要求发生结果才构成犯罪时,不能因为结果难以认定,就直接取消结果要件。②二年内受到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再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也只是表明其多次实施了该行为,并不表明其行为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即使认为行为人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也不能说明其行为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这再一次表明,所谓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明显不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③《刑法》第153条第一款关于“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规定不涉及偷逃税款的结果,立法机关也可以不将偷逃税款的结果规定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刑法》第338条明文要求发生“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套用《刑法》第153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逻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曾因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再次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即使没有“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成立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一般公民曾因失火(未构成犯罪)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再次失火的,即使没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也要认定为失火罪。这显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再如,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月16日《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拒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符合本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一)造成劳动者或者其被赡养人、被扶养人、被抚养人的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重大疾病无法及时医治或者失学的;(二)对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的;(三)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其中的第(二)项规定,也是直接将行为认定为结果,还可能导致罪数认定的困惑。事实上,行为人对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手段行为。如果承认牵连犯的概念,那么,当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的行为造成伤害等结果因而构成其他犯罪时,便成立牵连犯;如果不承认牵连犯的概念,或者认为上述行为不存在牵连关系,那么,当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的行为造成伤害等结果构成其他犯罪时,便应数罪并罚。在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暴力威胁的行为没有造成他人身体伤害·22·或者财产损害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其造成严重后果,并不妥当。(三)混淆犯罪形态故意犯罪存在既遂与未遂、中止、预备形态,形态不同明显影响量刑,甚至影响定罪〔38〕。所以,定罪量刑时必须明确区分故意犯罪形态。既不能将未遂形态提升为犯罪既遂处罚,也不能将犯罪预备提升为犯罪未遂处理,更不能将犯罪预备、中止提升为犯罪既遂处罚。但是,在这一方面,近年来的司法解释存在疑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0月20日《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