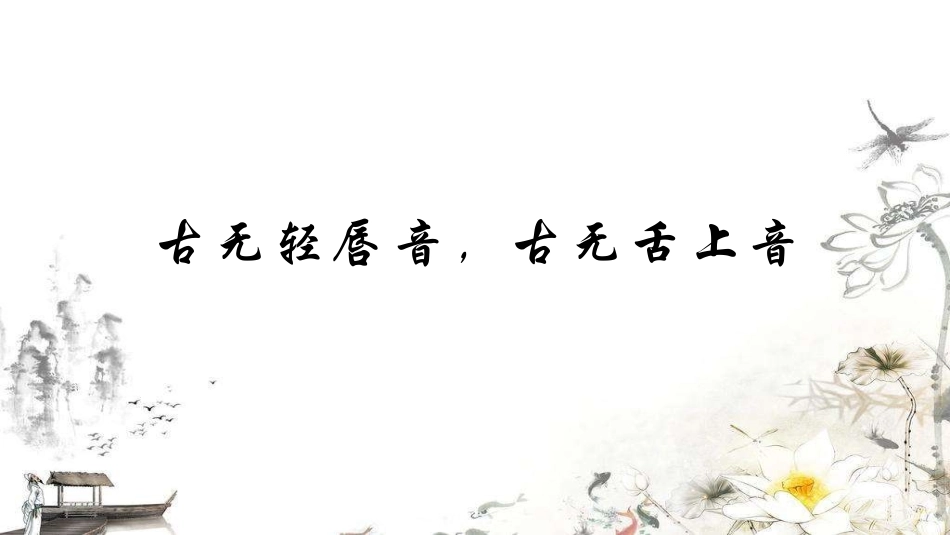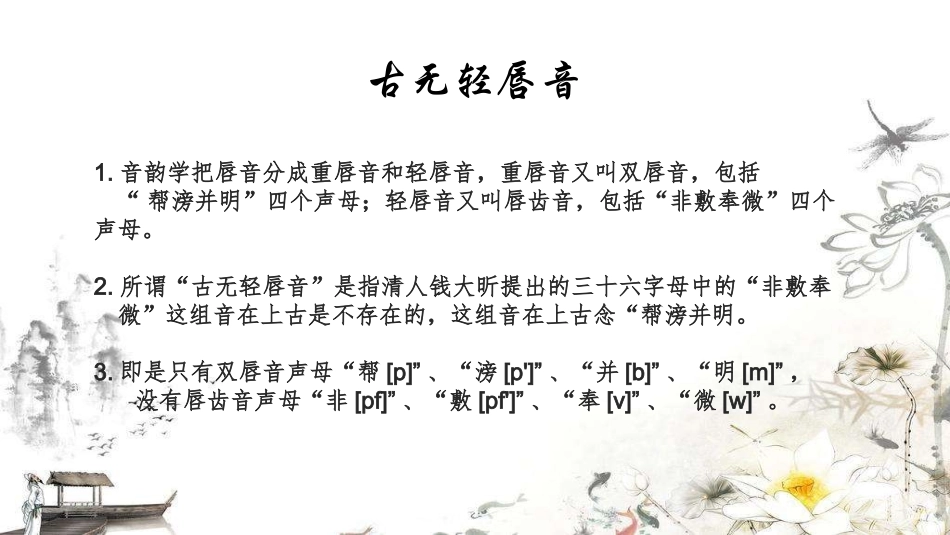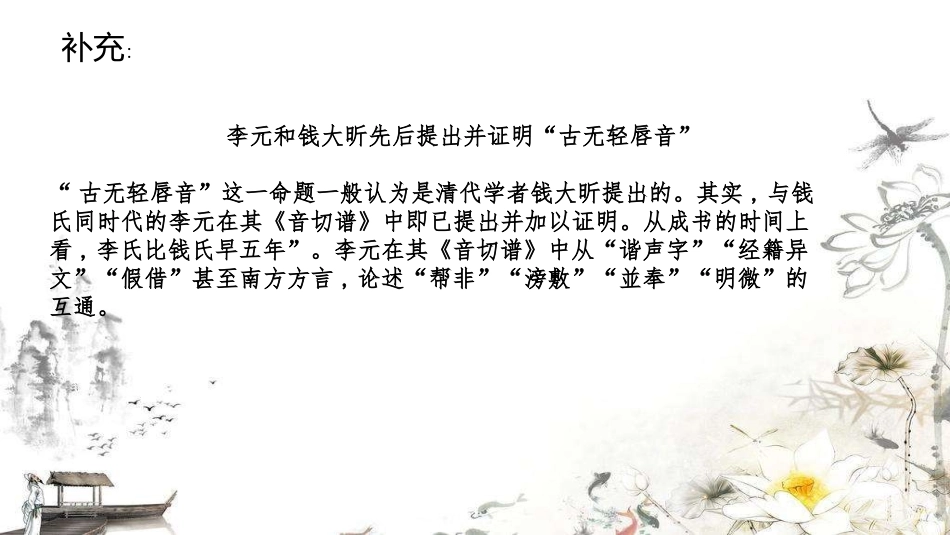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1.音韵学把唇音分成重唇音和轻唇音,重唇音又叫双唇音,包括“帮滂并明”四个声母;轻唇音又叫唇齿音,包括“非敷奉微”四个声母。2.所谓“古无轻唇音”是指清人钱大昕提出的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这组音在上古是不存在的,这组音在上古念“帮滂并明。3.即是只有双唇音声母“帮[p]”、“滂[p']”、“并[b]”、“明[m]”,没有唇齿音声母“非[pf]”、“敷[pf']”、“奉[v]”、“微[w]”。补充:李元和钱大昕先后提出并证明“古无轻唇音”“古无轻唇音”这一命题一般认为是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的。其实,与钱氏同时代的李元在其《音切谱》中即已提出并加以证明。从成书的时间上看,李氏比钱氏早五年”。李元在其《音切谱》中从“谐声字”“经籍异文”“假借”甚至南方方言,论述“帮非”“滂敷”“並奉”“明微”的互通。材料举例1.从古书异文上看2.从声训上看3.从古注上看4.从古今字及通假字上看5.其他古书异文•古代“伏牺”有多种写法。《易经·系辞下》作“包牺”,《说文解字叙》、《经典释文》作“庖牺”,可见“伏”这个轻唇音与重唇音“包、庖”古音同,都读重唇音。•“匍匐”二字,是双声连绵词,在上古也有多种写法。《诗·邶风·谷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礼记·檀弓下》引作“扶服”。《左传·昭公十三年》有“奉壶饮冰,以蒲伏焉”。《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作“扶伏而击之,折轸”。《史记·苏秦列传》有“嫂委虵蒲服,以面掩地”。《中山狼传》“先生匍匐以进,跽而言。”也有作“俯伏”的。这些“匍匐”的异文,上古都是同音字,都读重音。声训•声训是拿同音或音近而意义又有关联的字来解释另一个字。•《说文》:“马,武也。”(马是武备之一,古代战争离不开马)•《说文》:“畐(fu2),满也。”(古代吃饱就是有畐(福)了)•《广雅》(三国魏时张揖所撰):“匪,彼也。”•《释名》(东汉末刘熙撰):“法,逼也。”•《毛传》:“莫(“暮”本字),晚也。”以上例字都是由于声母在上古相同,而以为训。可见,马-武,畐-满,匪-彼,法-逼,莫-晚。声母彼此是相同的,在上古都读重唇音。古注•古注即古书的注释。•《大戴礼记·曾子之事》:“君子终身守此勿勿。”旧注:“勿勿犹勉勉。”“勿”即重唇“勉”。•《汉书·陈汤传》:“御史大夫繁延寿。”颜师古注:“繁,蒲胡反。”《广韵》繁作“薄波切”。三国时有繁钦,繁作pó,读重唇音。•《诗经·周颂·敬之》:“佛时仔肩(群臣辅佐我担大任)。”《经典释文》:“佛,郑音弼,辅也。”(郑音弼是东汉郑玄给“佛”注音,读作弼)。古今字和通假字•《史记·魏世家》:“中旗冯(凭)琴而对。”《春秋后语》(晋·孔衍·国别体)假借为“伏琴”。•《尚书·禹贡》:“至于陪尾”,《史记》借做“负尾”,《汉书》借做“倍尾”。•《庄子·逍遥游》:“其名曰鹏”。《释文》:“崔音凤,云‘鹏即古凤字’。”(崔音凤,崔譔为《庄子》作注时的注音)•《宋玉对楚王问》:“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与《庄子·逍遥游》说正同,可知凤即鹏。其他•鳆鱼——鲍鱼•船帆——船篷,落帆——落篷•负债——背债,负义——背义,《释名》:“负,背也”•吴方言中:蚊读如门,亡读如芒,晚读如莽,皆为重唇音。•客家方言中:肥读作pui(二声),无读作毛。从以上材料看,“非敷奉微”这组轻唇音在上古归为“帮滂并明。补充:古无轻唇音之“古”•古无轻唇音是何时产生的,“古无轻唇音”的“古”究竟是什么时段?钱大昕是从泛时角度提出“古无轻唇音”的,他所利用的文献材料也是泛时性的,没有进行阶段性分析。•然而通语的轻唇音何时从重唇音分化出来,音韵学家的看法尚不一致。•高本汉(1994)认为轻唇音从重唇音分化出来的时代“一般认为是在唐初”。•张清常(1963)认为“轻唇从重唇里面分化出来,虽然起源较早,可以推溯到汉魏六朝,但是完全彻底分家,似乎到了北宋之初才得到韵学家的承认”。•王力(1985)认为,隋唐时代,唇音还没有分化为重唇(双唇)轻唇(唇齿),轻重唇的分化始自晚唐五代。“唇音分化为重唇(双唇)轻唇(唇齿),是从这个时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