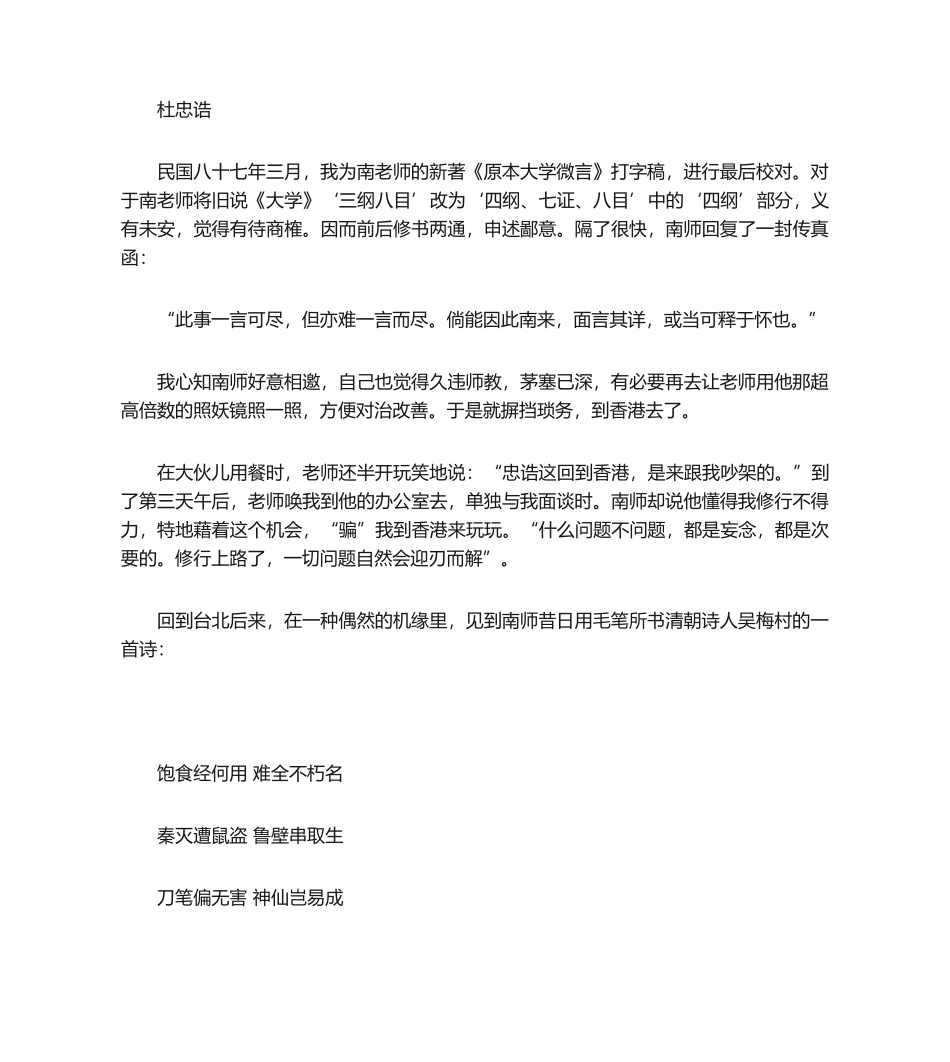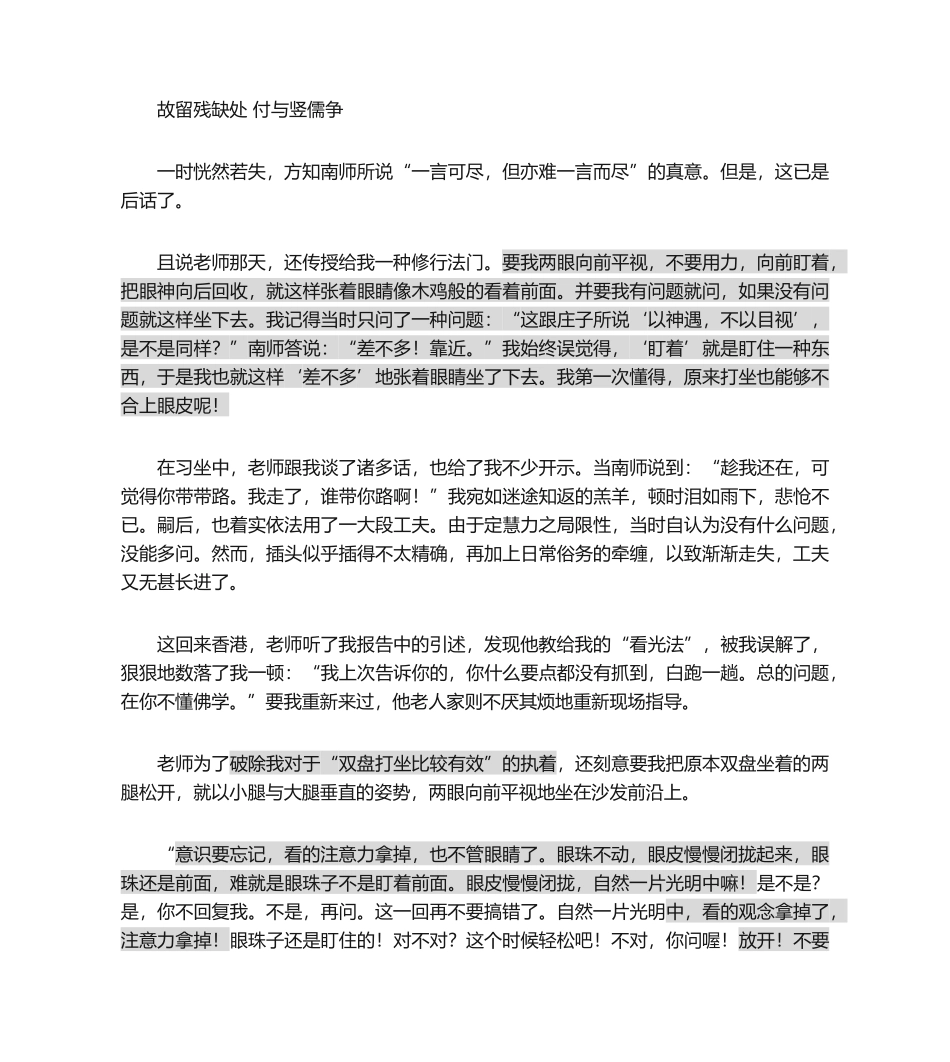杜忠诰民国八十七年三月,我为南老师的新著《原本大学微言》打字稿,进行最后校对。对于南老师将旧说《大学》‘三纲八目’改为‘四纲、七证、八目’中的‘四纲’部分,义有未安,觉得有待商榷。因而前后修书两通,申述鄙意。隔了很快,南师回复了一封传真函: “此事一言可尽,但亦难一言而尽。倘能因此南来,面言其详,或当可释于怀也。” 我心知南师好意相邀,自己也觉得久违师教,茅塞已深,有必要再去让老师用他那超高倍数的照妖镜照一照,方便对治改善。于是就摒挡琐务,到香港去了。 在大伙儿用餐时,老师还半开玩笑地说:“忠诰这回到香港,是来跟我吵架的。”到了第三天午后,老师唤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单独与我面谈时。南师却说他懂得我修行不得力,特地藉着这个机会,“骗”我到香港来玩玩。“什么问题不问题,都是妄念,都是次要的。修行上路了,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回到台北后来,在一种偶然的机缘里,见到南师昔日用毛笔所书清朝诗人吴梅村的一首诗: 饱食经何用 难全不朽名 秦灭遭鼠盗 鲁壁串取生 刀笔偏无害 神仙岂易成 故留残缺处 付与竖儒争 一时恍然若失,方知南师所说“一言可尽,但亦难一言而尽”的真意。但是,这已是后话了。 且说老师那天,还传授给我一种修行法门。要我两眼向前平视,不要用力,向前盯着,把眼神向后回收,就这样张着眼睛像木鸡般的看着前面。并要我有问题就问,如果没有问题就这样坐下去。我记得当时只问了一种问题:“这跟庄子所说‘以神遇,不以目视’,是不是同样?”南师答说:“差不多!靠近。”我始终误觉得,‘盯着’就是盯住一种东西,于是我也就这样‘差不多’地张着眼睛坐了下去。我第一次懂得,原来打坐也能够不合上眼皮呢! 在习坐中,老师跟我谈了诸多话,也给了我不少开示。当南师说到:“趁我还在,可觉得你带带路。我走了,谁带你路啊!”我宛如迷途知返的羔羊,顿时泪如雨下,悲怆不已。嗣后,也着实依法用了一大段工夫。由于定慧力之局限性,当时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没能多问。然而,插头似乎插得不太精确,再加上日常俗务的牵缠,以致渐渐走失,工夫又无甚长进了。 这回来香港,老师听了我报告中的引述,发现他教给我的“看光法”,被我误解了,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我上次告诉你的,你什么要点都没有抓到,白跑一趟。总的问题,在你不懂佛学。”要我重新来过,他老人家则不厌其烦地重新现场指导。 老师为了破除我对于“双盘打坐比较有效”的执着,还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