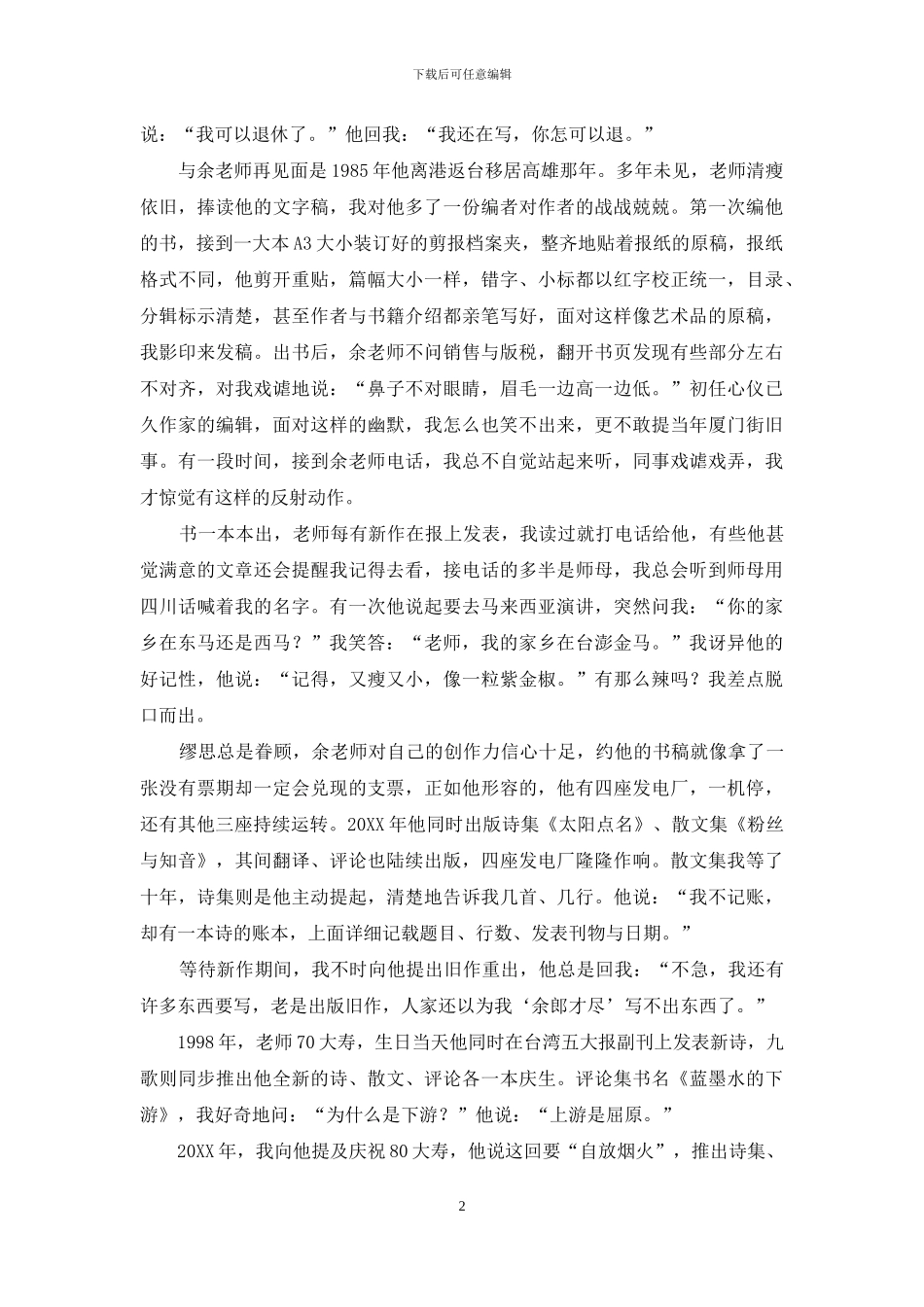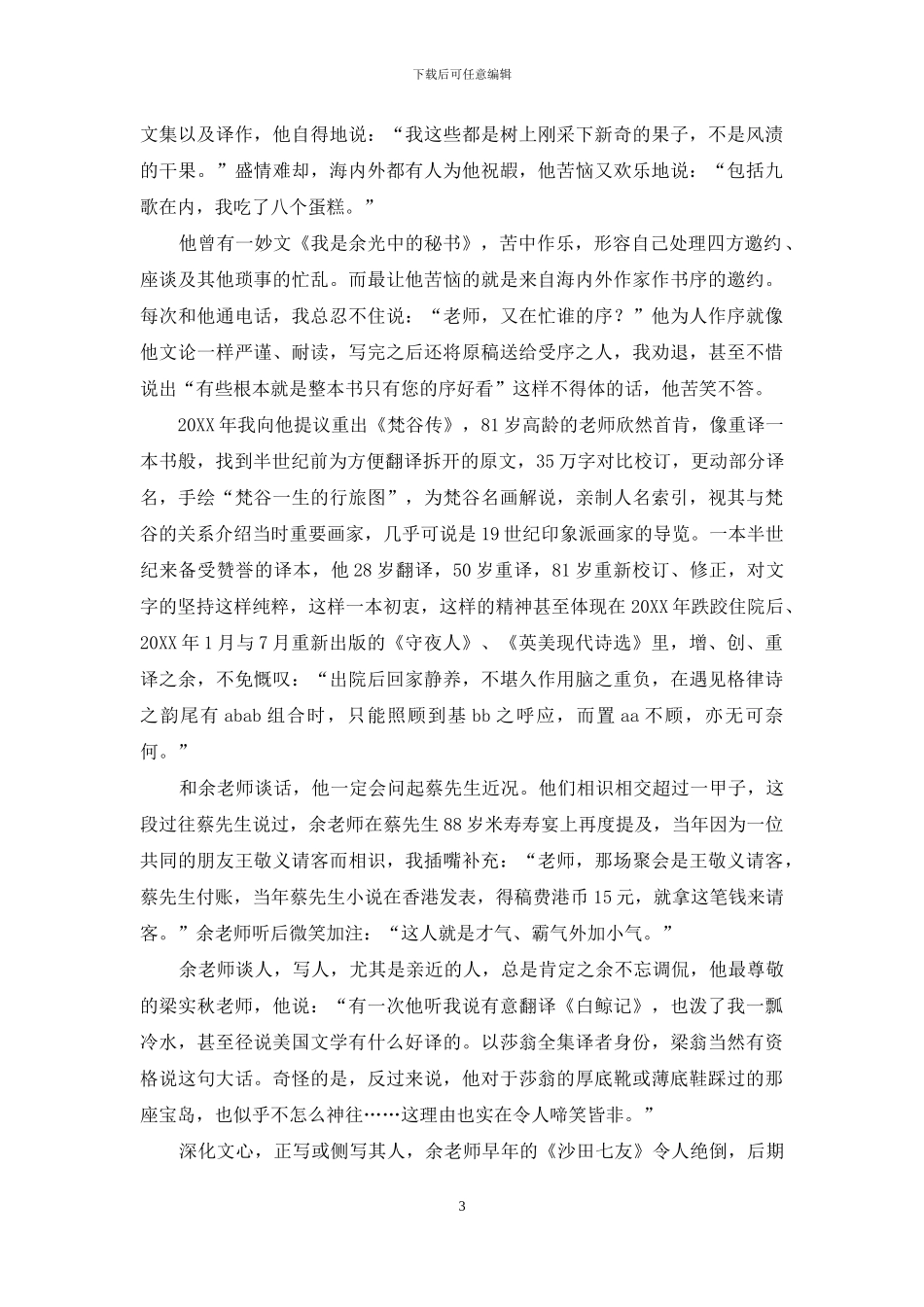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当夜色降临,星光升起当夜色降临,星光升起 演讲是下午两点到四点,依惯例会后为读者签名,由于等候签名的队伍太长,我们离开时将近六点,信步走到一间印度小馆,推门而入,檀香味西塔琴音乐声迎面而来,余老师低咕一句:“Ravi ShanKar。”师母点餐,他就近在柜台边拿起摆在台前的 CD,摘下眼镜细读上面的小字。一看即知是印度人的老板过来攀谈,老师回座,师母问他聊了什么,他说:“他问我是诗人还是哲学家?”我好奇他怎么回答?余老师说:“我笑而不答。”我说:“老师,您应该说我两者都是。”他一径“笑而不答”。 Ravi ShanKar,余老师译成拉维·仙客,而不是大家熟知的拉维·香卡。我知道这个名字是读了他那篇写拉维·仙客为东巴难民募款的慈善演奏会《苦雨就要下降》,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开始听巴布·狄伦,余老师这么形容狄伦:“他是最活泼最狂放的摇滚乐坛上一尊最严肃最沉默的史芬克狮。现代酒神的孩子们唱起歌来,他是唯一不醉的歌者”,读那篇文章时我大三。 那年,我和一群来自马来西亚写诗的朋友,像朝圣般进了位于台北市厦门街的余府,当时余老师在香港任教,港、台两地跑,我们这群人,任何议题都可以引“一千个故事是一個故事,那主题永远是一个主题”加注,聚会时有人一唱“琴声疏疏”,就有人接着唱“注不盈清冷的下午”,现在我们要去见写下这些句子的本尊余光中了,兴奋不在话下。初见面,只觉他像最亲切的老师,说话不快,声音不大,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想用笔记下来,我想这就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吧。然而当他朗诵“民歌”时,那声音,时而高亢雄浑时而低吟近乎无声,无声处宁静得似有轰雷在远方。眼前这位瘦小又温文儒雅的师长根本就是拿着指挥棒呼风唤雨的小巨人,撒豆成兵,天女散花,指挥棒一点,天地就抽换另一幕景象,我都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那时我只是小跟班,也写不出好诗,我想我不可能会再有机会这样近距离接近这位小巨人了。然而,一饮一啄,自有天听。我学诗不成,大学毕业后在九歌与蔡文甫先生学编辑,而且一学就超过 35 年。做满 30 年时,我对余老师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说:“我可以退休了。”他回我:“我还在写,你怎可以退。” 与余老师再见面是 1985 年他离港返台移居高雄那年。多年未见,老师清瘦依旧,捧读他的文字稿,我对他多了一份编者对作者的战战兢兢。第一次编他的书,接到一大本 A3 大小装订好的剪报档案夹,整齐地贴着报纸的原稿,报纸格式不同,他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