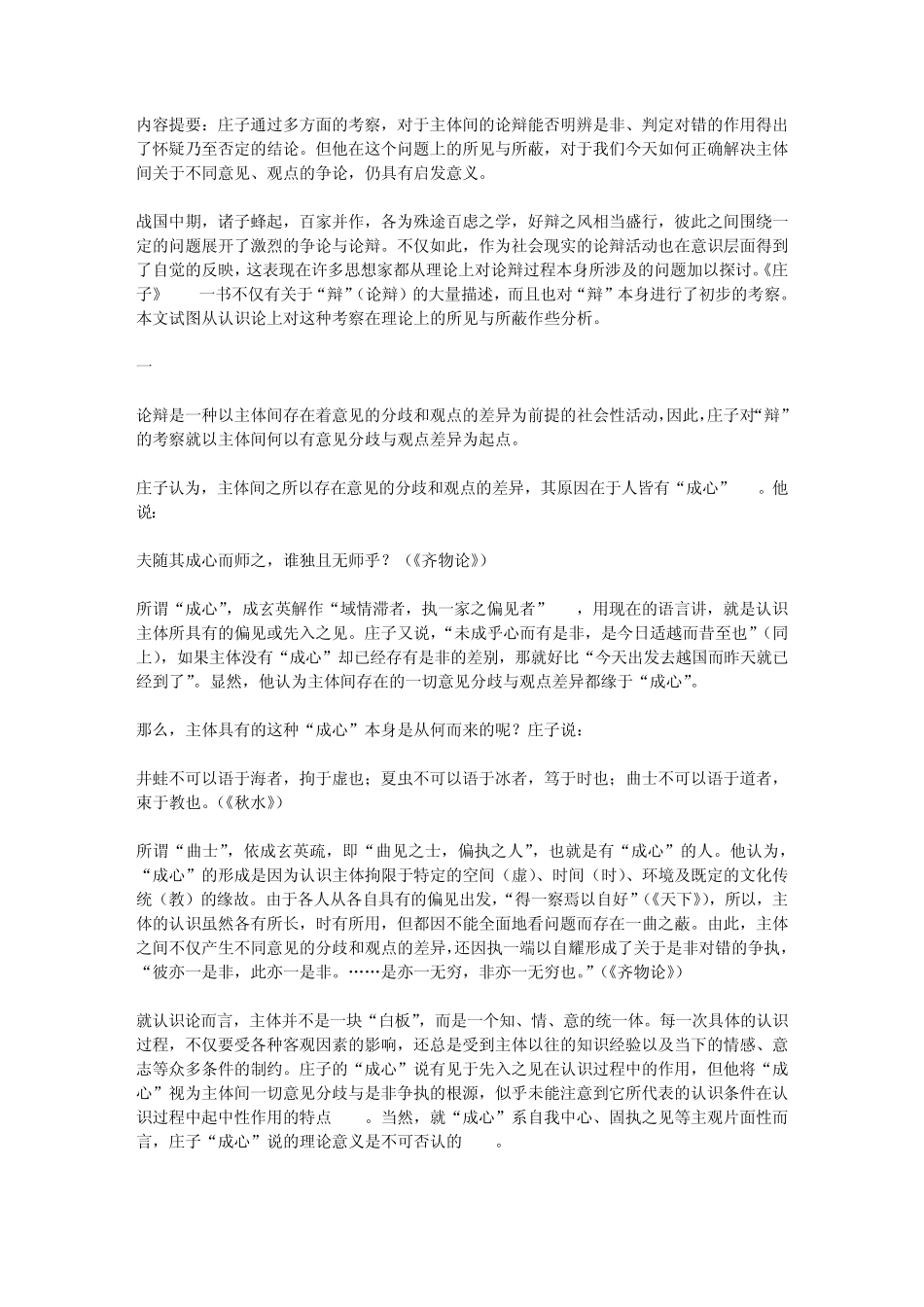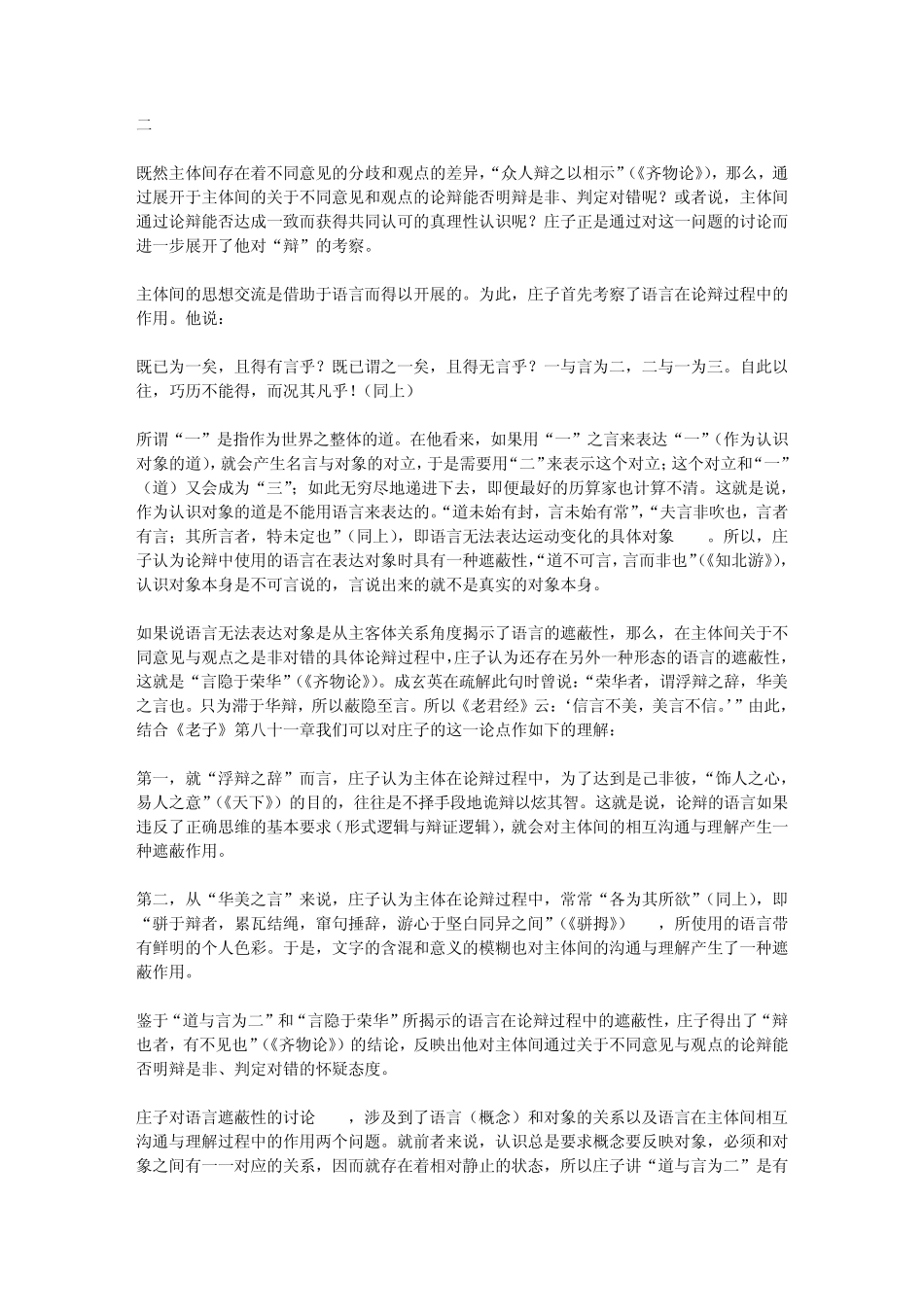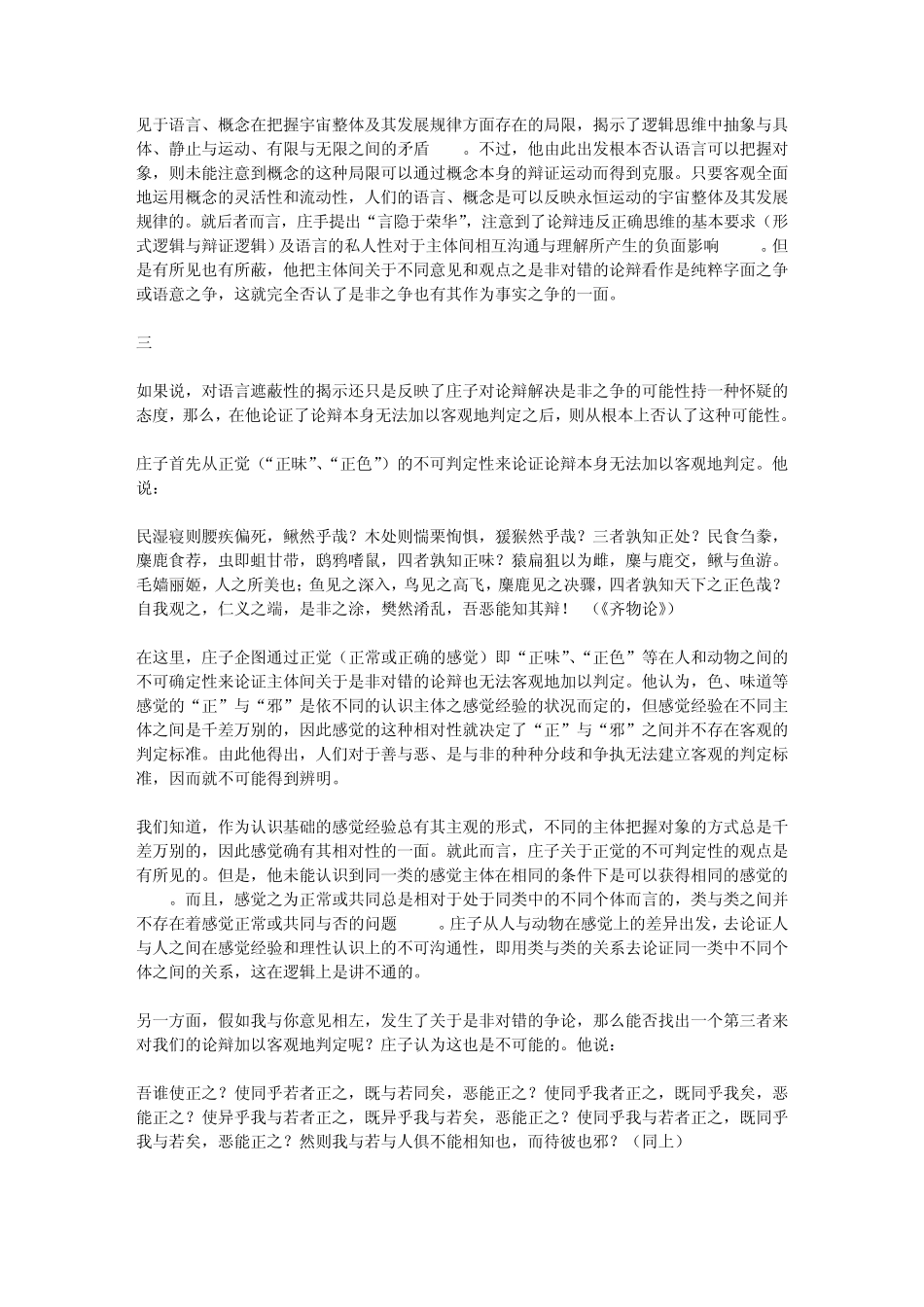内容提要:庄子通过多方面的考察,对于主体间的论辩能否明辨是非、判定对错的作用得出了怀疑乃至否定的结论。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见与所蔽,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解决主体间关于不同意见、观点的争论,仍具有启发意义。 战国中期,诸子蜂起,百家并作,各为殊途百虑之学,好辩之风相当盛行,彼此之间围绕一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论辩。不仅如此,作为社会现实的论辩活动也在意识层面得到了自觉的反映,这表现在许多思想家都从理论上对论辩过程本身所涉及的问题加以探讨。《庄子》[1] 一书不仅有关于“辩”(论辩)的大量描述,而且也对“辩”本身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本文试图从认识论上对这种考察在理论上的所见与所蔽作些分析。 一 论辩是一种以主体间存在着意见的分歧和观点的差异为前提的社会性活动,因此,庄子对“辩”的考察就以主体间何以有意见分歧与观点差异为起点。 庄子认为,主体间之所以存在意见的分歧和观点的差异,其原因在于人皆有“成心”[2]。他说: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齐物论》) 所谓“成心”,成玄英解作“域情滞者,执一家之偏见者”[3],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认识主体所具有的偏见或先入之见。庄子又说,“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同上),如果主体没有“成心”却已经存有是非的差别,那就好比“今天出发去越国而昨天就已经到了”。显然,他认为主体间存在的一切意见分歧与观点差异都缘于“成心”。 那么,主体具有的这种“成心”本身是从何而来的呢?庄子说: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 所谓“曲士”,依成玄英疏,即“曲见之士,偏执之人”,也就是有“成心”的人。他认为,“成心”的形成是因为认识主体拘限于特定的空间(虚)、时间(时)、环境及既定的文化传统(教)的缘故。由于各人从各自具有的偏见出发,“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所以,主体的认识虽然各有所长,时有所用,但都因不能全面地看问题而存在一曲之蔽。由此,主体之间不仅产生不同意见的分歧和观点的差异,还因执一端以自耀形成了关于是非对错的争执,“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齐物论》) 就认识论而言,主体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一个知、情、意的统一体。每一次具体的认识过程,不仅要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还总是受到主体以往的知识经验以及当下的情感、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