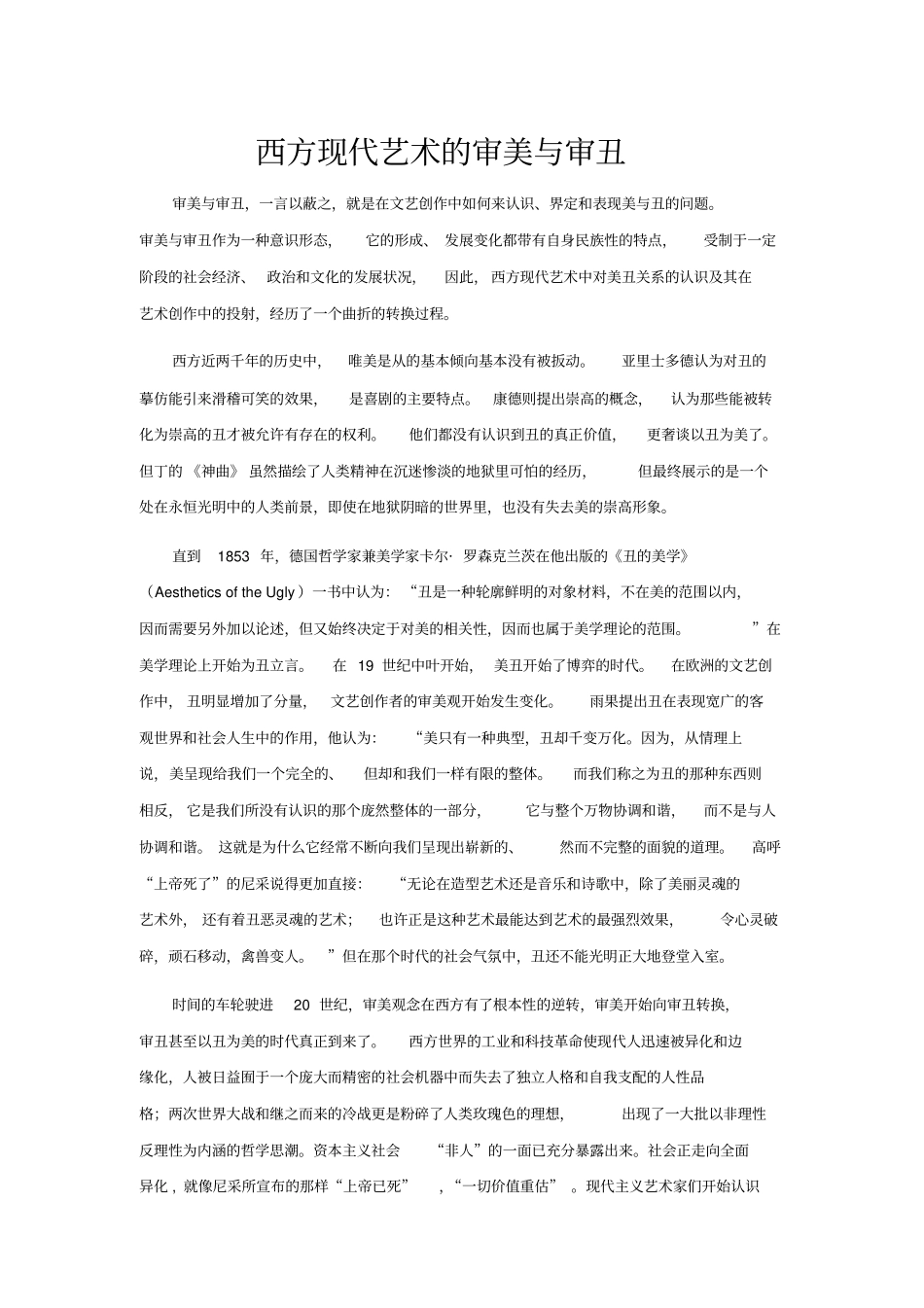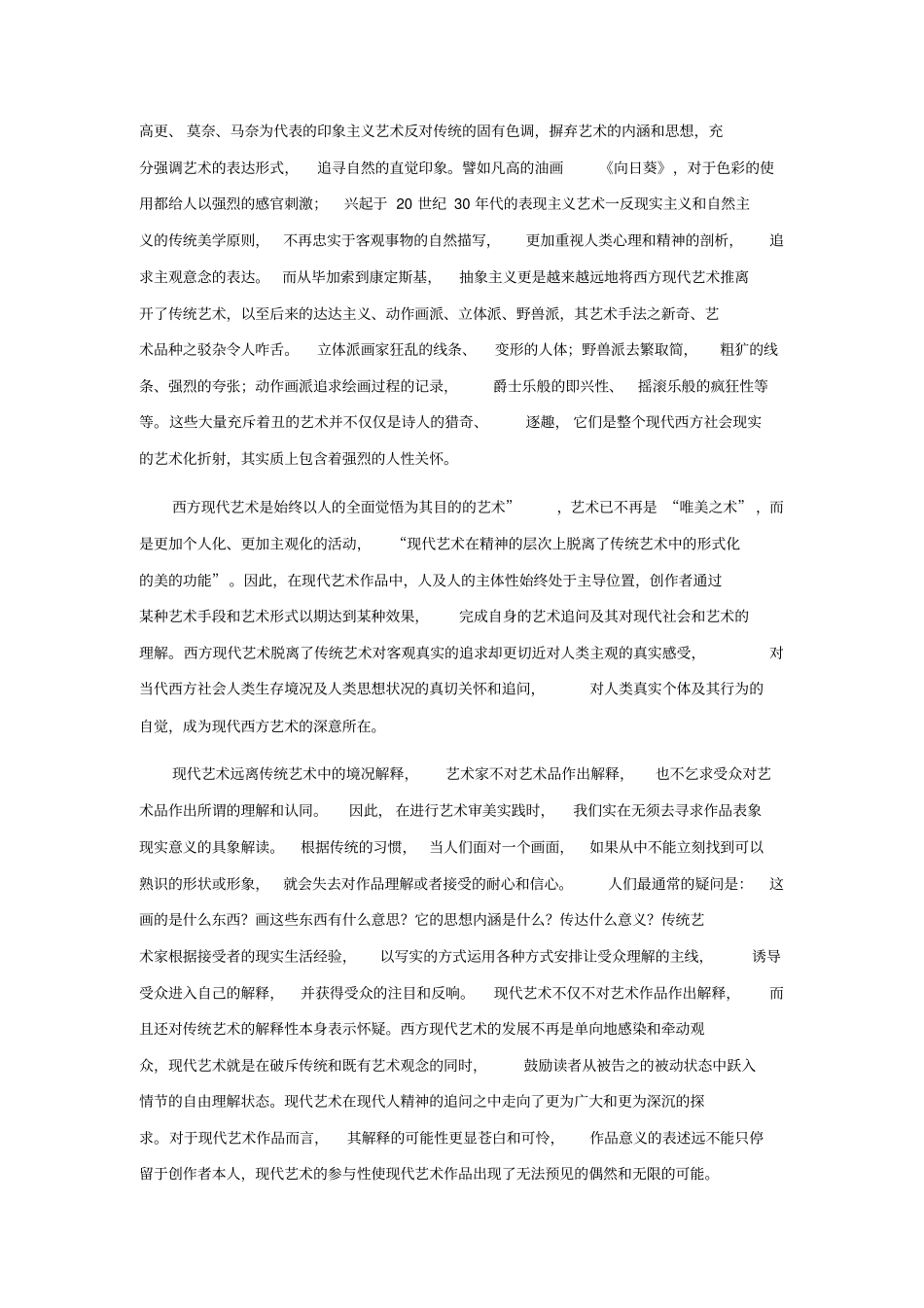西方现代艺术的审美与审丑审美与审丑,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文艺创作中如何来认识、界定和表现美与丑的问题。审美与审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形成、 发展变化都带有自身民族性的特点,受制于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状况,因此, 西方现代艺术中对美丑关系的认识及其在艺术创作中的投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转换过程。西方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唯美是从的基本倾向基本没有被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丑的摹仿能引来滑稽可笑的效果,是喜剧的主要特点。康德则提出崇高的概念,认为那些能被转化为崇高的丑才被允许有存在的权利。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丑的真正价值,更奢谈以丑为美了。但丁的 《神曲》 虽然描绘了人类精神在沉迷惨淡的地狱里可怕的经历,但最终展示的是一个处在永恒光明中的人类前景,即使在地狱阴暗的世界里,也没有失去美的崇高形象。直到1853 年,德国哲学家兼美学家卡尔· 罗森克兰茨在他出版的《丑的美学》(Aesthetics of the Ugly )一书中认为: “丑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对象材料,不在美的范围以内,因而需要另外加以论述,但又始终决定于对美的相关性,因而也属于美学理论的范围。”在美学理论上开始为丑立言。在 19 世纪中叶开始, 美丑开始了博弈的时代。在欧洲的文艺创作中, 丑明显增加了分量,文艺创作者的审美观开始发生变化。雨果提出丑在表现宽广的客观世界和社会人生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因为,从情理上说,美呈现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但却和我们一样有限的整体。而我们称之为丑的那种东西则相反, 它是我们所没有认识的那个庞然整体的一部分,它与整个万物协调和谐,而不是与人协调和谐。 这就是为什么它经常不断向我们呈现出崭新的、然而不完整的面貌的道理。高呼“上帝死了”的尼采说得更加直接:“无论在造型艺术还是音乐和诗歌中,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 还有着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顽石移动,禽兽变人。”但在那个时代的社会气氛中,丑还不能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时间的车轮驶进20 世纪,审美观念在西方有了根本性的逆转,审美开始向审丑转换,审丑甚至以丑为美的时代真正到来了。西方世界的工业和科技革命使现代人迅速被异化和边缘化,人被日益囿于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社会机器中而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我支配的人性品格;两次世界大战和继之而来的冷战更是粉碎了人类玫瑰色的理想,出现了一大批以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