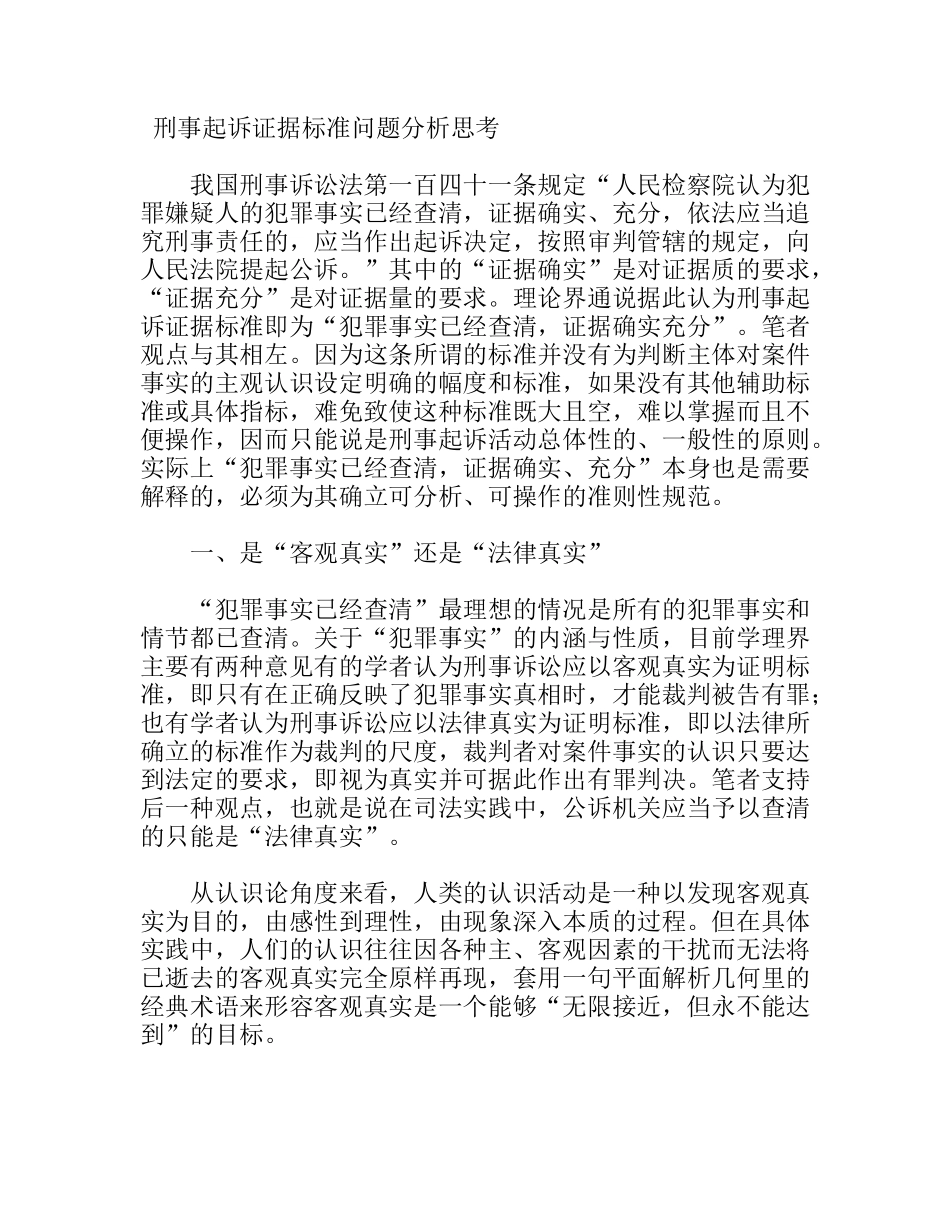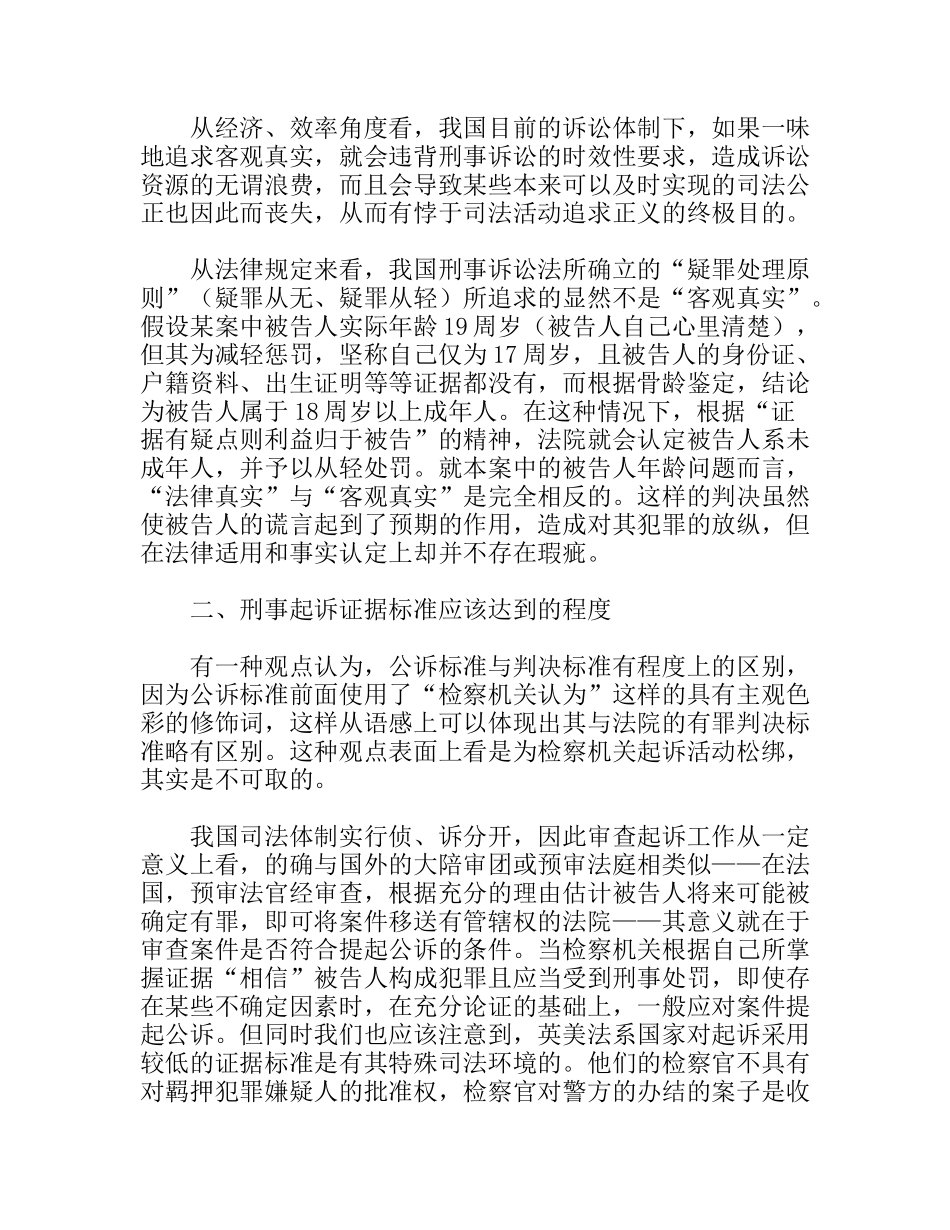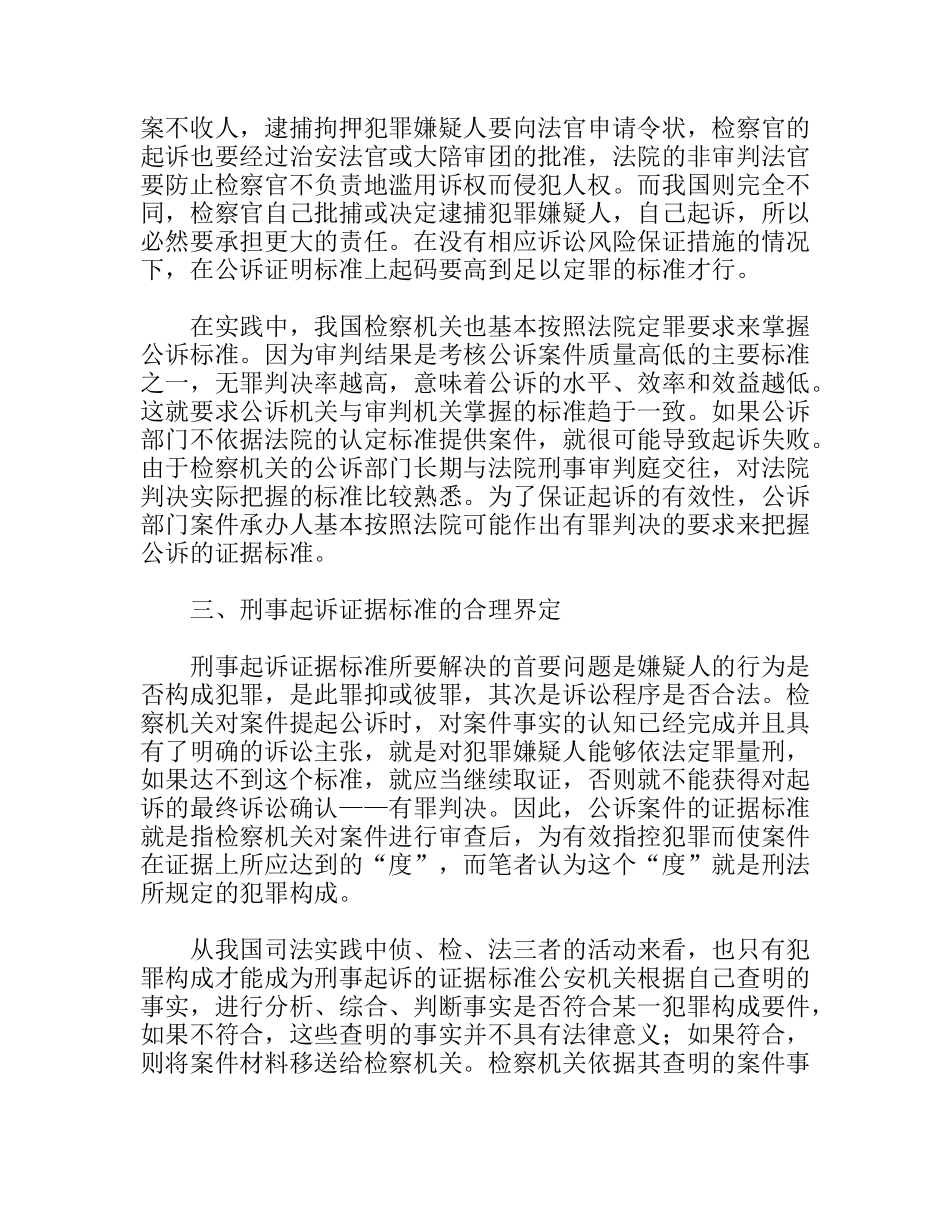刑事起诉证据标准问题分析思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的“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理论界通说据此认为刑事起诉证据标准即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笔者观点与其相左。因为这条所谓的标准并没有为判断主体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设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如果没有其他辅助标准或具体指标,难免致使这种标准既大且空,难以掌握而且不便操作,因而只能说是刑事起诉活动总体性的、一般性的原则。实际上“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必须为其确立可分析、可操作的准则性规范。一、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的犯罪事实和情节都已查清。关于“犯罪事实”的内涵与性质,目前学理界主要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客观真实为证明标准,即只有在正确反映了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有罪;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法律真实为证明标准,即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法定的要求,即视为真实并可据此作出有罪判决。笔者支持后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应当予以查清的只能是“法律真实”。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种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深入本质的过程。但在具体实践中,人们的认识往往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将已逝去的客观真实完全原样再现,套用一句平面解析几何里的经典术语来形容客观真实是一个能够“无限接近,但永不能达到”的目标。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我国目前的诉讼体制下,如果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就会违背刑事诉讼的时效性要求,造成诉讼资源的无谓浪费,而且会导致某些本来可以及时实现的司法公正也因此而丧失,从而有悖于司法活动追求正义的终极目的。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处理原则”(疑罪从无、疑罪从轻)所追求的显然不是“客观真实”。假设某案中被告人实际年龄19周岁(被告人自己心里清楚),但其为减轻惩罚,坚称自己仅为17周岁,且被告人的身份证、户籍资料、出生证明等等证据都没有,而根据骨龄鉴定,结论为被告人属于18周岁以上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证据有疑点则利益归于被告”的精神,法院就会认定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并予以从轻处罚。就本案中的被告人年龄问题而言,“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判决虽然使被告人的谎言起到了预期的作用,造成对其犯罪的放纵,但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却并不存在瑕疵。二、刑事起诉证据标准应该达到的程度有一种观点认为,公诉标准与判决标准有程度上的区别,因为公诉标准前面使用了“检察机关认为”这样的具有主观色彩的修饰词,这样从语感上可以体现出其与法院的有罪判决标准略有区别。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为检察机关起诉活动松绑,其实是不可取的。我国司法体制实行侦、诉分开,因此审查起诉工作从一定意义上看,的确与国外的大陪审团或预审法庭相类似——在法国,预审法官经审查,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将来可能被确定有罪,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其意义就在于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当检察机关根据自己所掌握证据“相信”被告人构成犯罪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即使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一般应对案件提起公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英美法系国家对起诉采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是有其特殊司法环境的。他们的检察官不具有对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批准权,检察官对警方的办结的案子是收案不收人,逮捕拘押犯罪嫌疑人要向法官申请令状,检察官的起诉也要经过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的批准,法院的非审判法官要防止检察官不负责地滥用诉权而侵犯人权。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检察官自己批捕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自己起诉,所以必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没有相应诉讼风险保证措施的情况下,在公诉证明标准上起码要高到足以定罪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