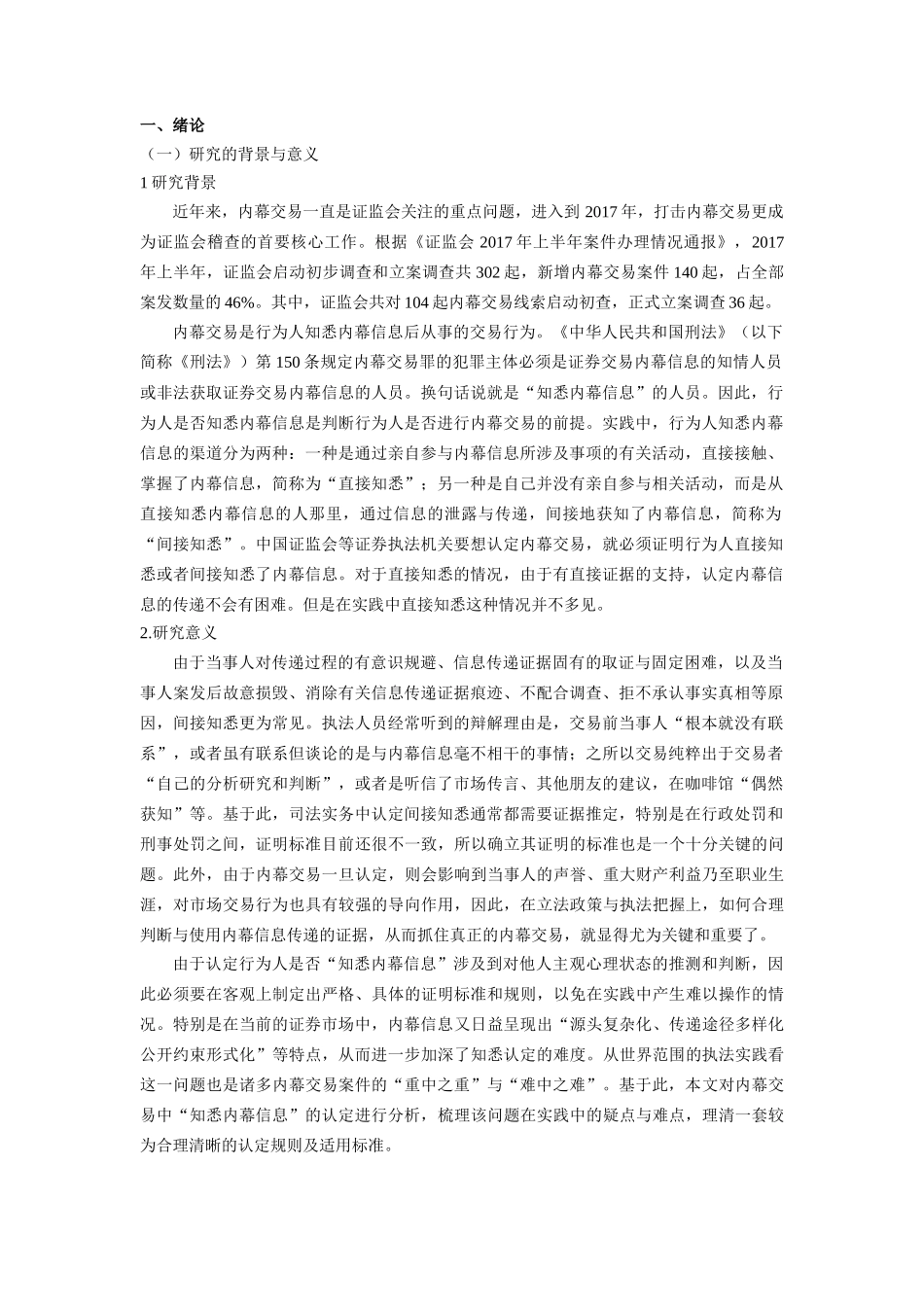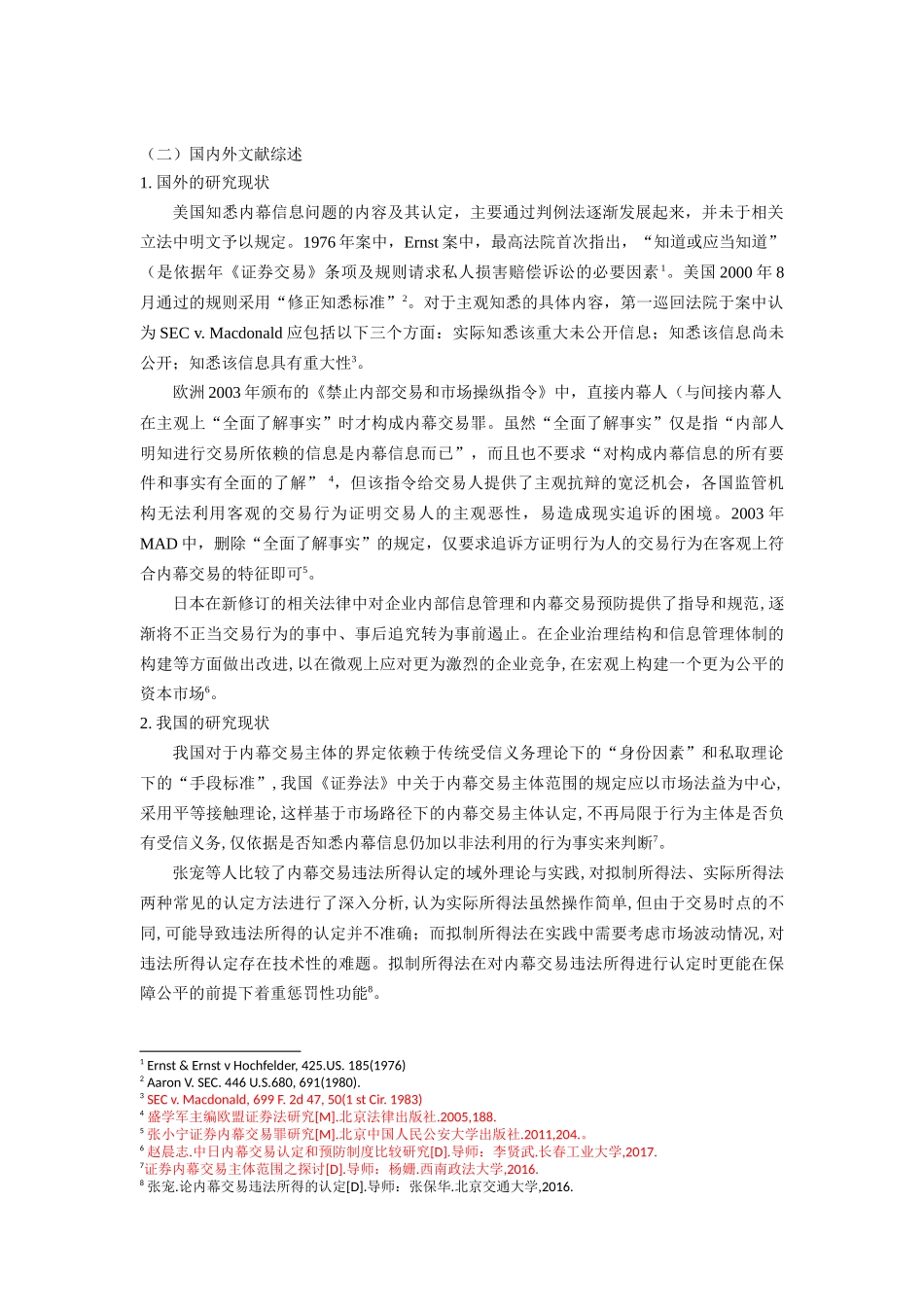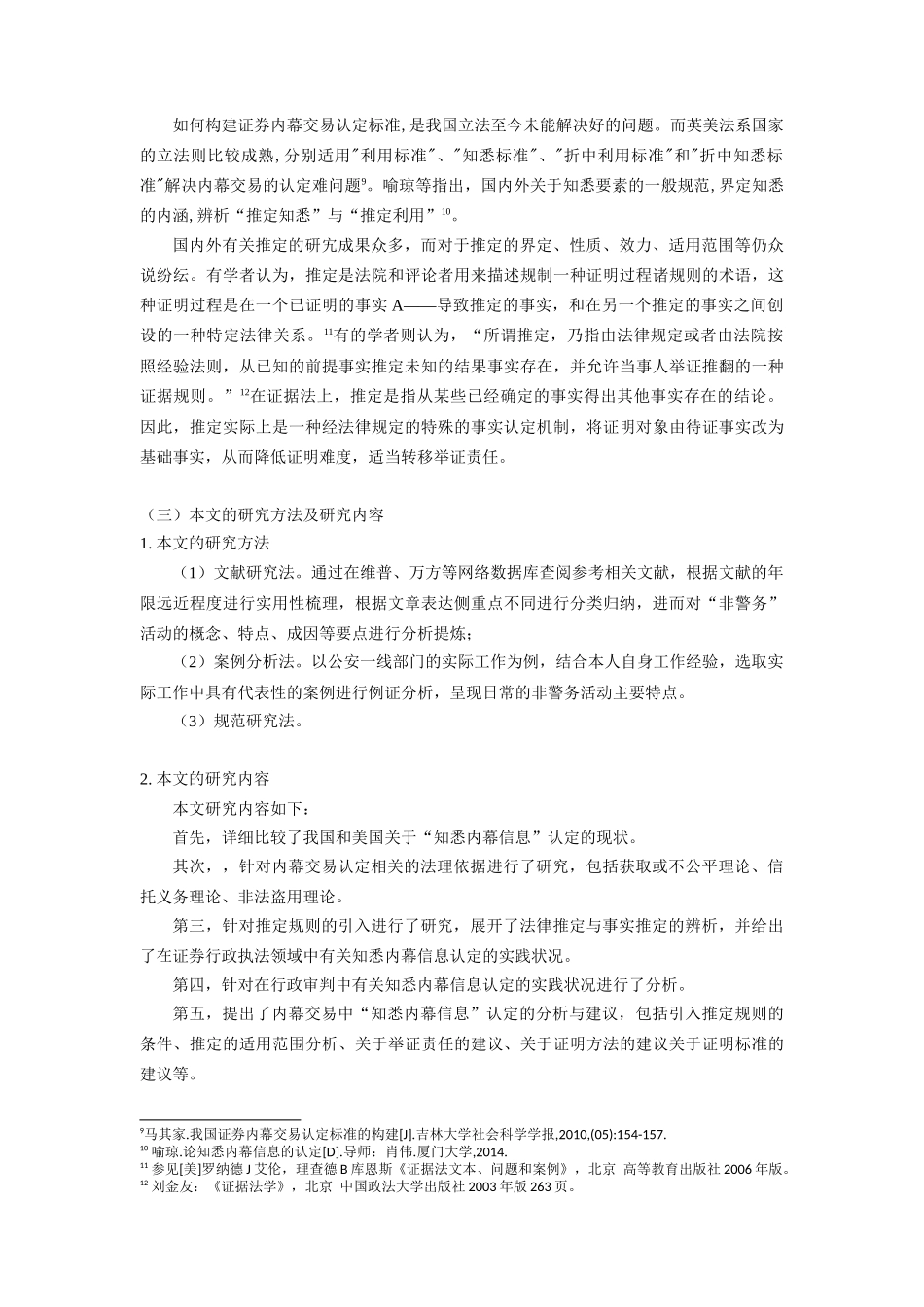一、绪论(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1 研究背景近年来,内幕交易一直是证监会关注的重点问题,进入到 2017 年,打击内幕交易更成为证监会稽查的首要核心工作。根据《证监会 2017 年上半年案件办理情况通报》,2017年上半年,证监会启动初步调查和立案调查共 302 起,新增内幕交易案件 140 起,占全部案发数量的 46%。其中,证监会共对 104 起内幕交易线索启动初查,正式立案调查 36 起。内幕交易是行为人知悉内幕信息后从事的交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 150 条规定内幕交易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换句话说就是“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因此,行为人是否知悉内幕信息是判断行为人是否进行内幕交易的前提。实践中,行为人知悉内幕信息的渠道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亲自参与内幕信息所涉及事项的有关活动,直接接触、掌握了内幕信息,简称为“直接知悉”;另一种是自己并没有亲自参与相关活动,而是从直接知悉内幕信息的人那里,通过信息的泄露与传递,间接地获知了内幕信息,简称为“间接知悉”。中国证监会等证券执法机关要想认定内幕交易,就必须证明行为人直接知悉或者间接知悉了内幕信息。对于直接知悉的情况,由于有直接证据的支持,认定内幕信息的传递不会有困难。但是在实践中直接知悉这种情况并不多见。2.研究意义由于当事人对传递过程的有意识规避、信息传递证据固有的取证与固定困难,以及当事人案发后故意损毁、消除有关信息传递证据痕迹、不配合调查、拒不承认事实真相等原因,间接知悉更为常见。执法人员经常听到的辩解理由是,交易前当事人“根本就没有联系”,或者虽有联系但谈论的是与内幕信息毫不相干的事情;之所以交易纯粹出于交易者“自己的分析研究和判断”,或者是听信了市场传言、其他朋友的建议,在咖啡馆“偶然获知”等。基于此,司法实务中认定间接知悉通常都需要证据推定,特别是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间,证明标准目前还很不一致,所以确立其证明的标准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此外,由于内幕交易一旦认定,则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声誉、重大财产利益乃至职业生涯,对市场交易行为也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因此,在立法政策与执法把握上,如何合理判断与使用内幕信息传递的证据,从而抓住真正的内幕交易,就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了。由于认定行为人是否“知悉内幕信息”涉及到对他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推测和判断,因此必须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