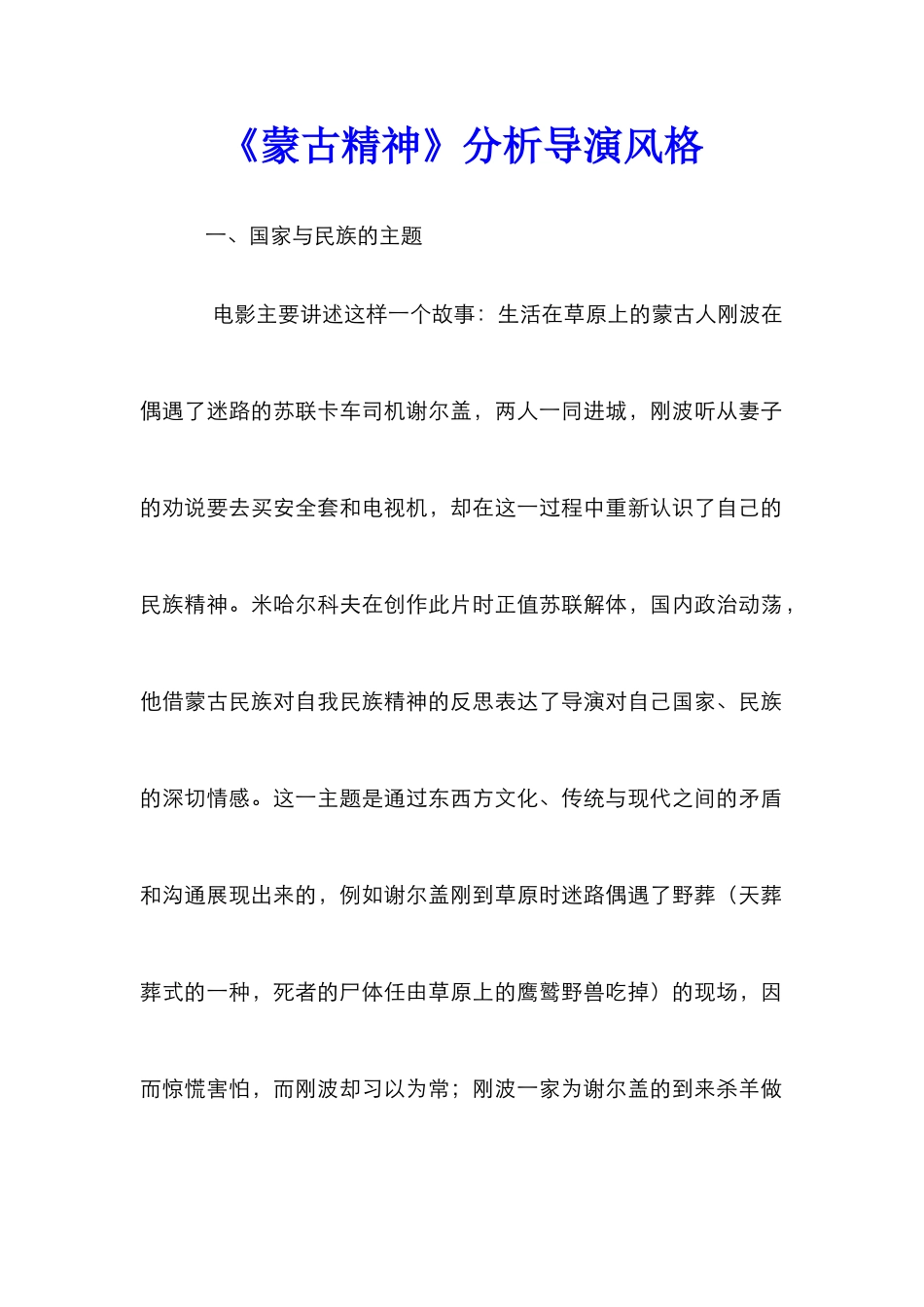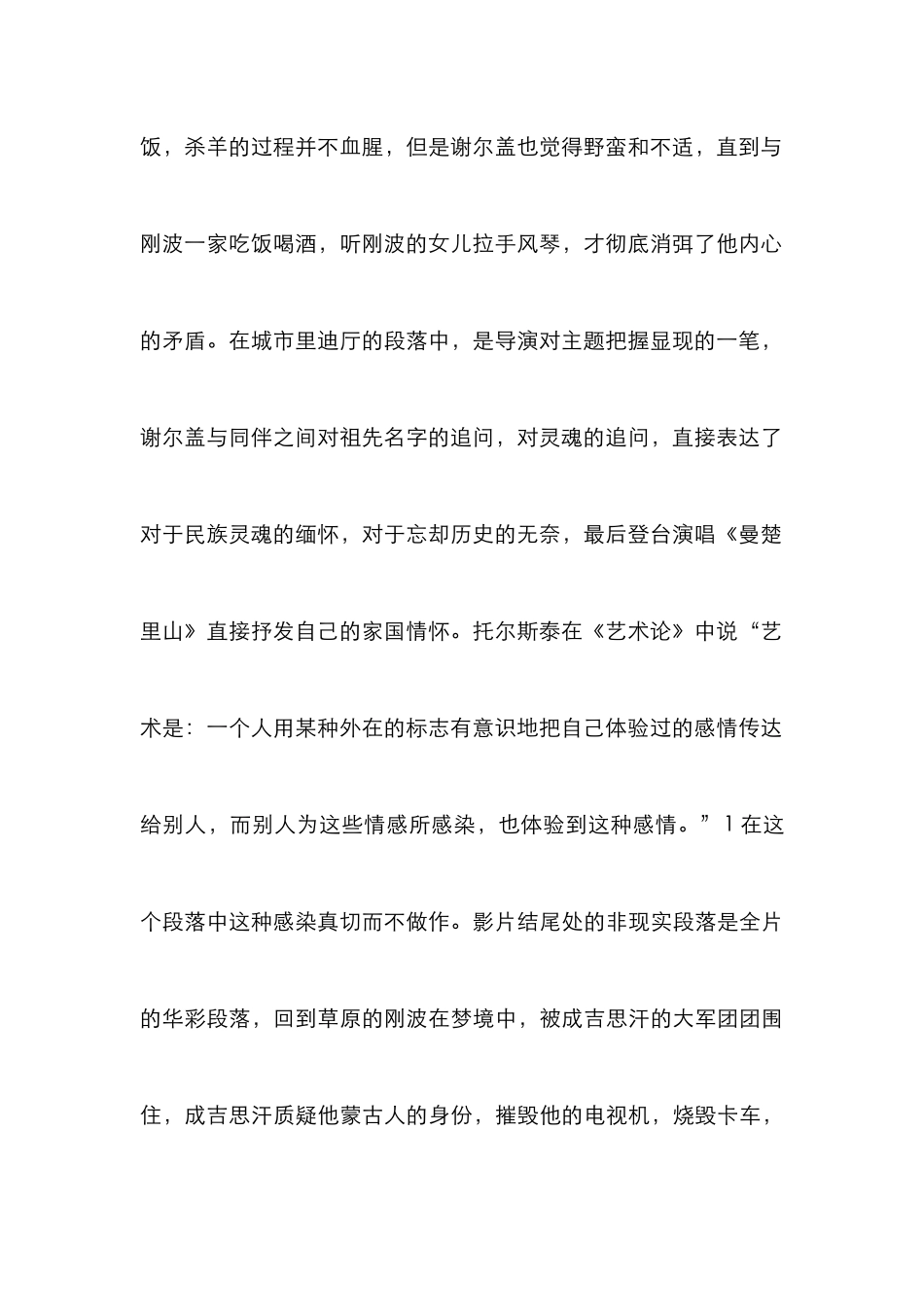《蒙古精神》分析导演风格 一、国家与民族的主题 电影主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刚波在偶遇了迷路的苏联卡车司机谢尔盖,两人一同进城,刚波听从妻子的劝说要去买安全套和电视机,却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米哈尔科夫在创作此片时正值苏联解体,国内政治动荡,他借蒙古民族对自我民族精神的反思表达了导演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深切情感。这一主题是通过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沟通展现出来的,例如谢尔盖刚到草原时迷路偶遇了野葬(天葬葬式的一种,死者的尸体任由草原上的鹰鹫野兽吃掉)的现场,因而惊慌害怕,而刚波却习以为常;刚波一家为谢尔盖的到来杀羊做饭,杀羊的过程并不血腥,但是谢尔盖也觉得野蛮和不适,直到与刚波一家吃饭喝酒,听刚波的女儿拉手风琴,才彻底消弭了他内心的矛盾。在城市里迪厅的段落中,是导演对主题把握显现的一笔,谢尔盖与同伴之间对祖先名字的追问,对灵魂的追问,直接表达了对于民族灵魂的缅怀,对于忘却历史的无奈,最后登台演唱《曼楚里山》直接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说“艺术是: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情感所感染,也体验到这种感情。”1 在这个段落中这种感染真切而不做作。影片结尾处的非现实段落是全片的华彩段落,回到草原的刚波在梦境中,被成吉思汗的大军团团围住,成吉思汗质疑他蒙古人的身份,摧毁他的电视机,烧毁卡车,惩处他丢弃了自己的传统。刚波醒来后跳着蒙古博克,奔向彩虹。导演曾说“很早前,我就想拍一部中国内蒙的影片……蒙古人曾经统治俄罗斯二百七十多年,我们的血液中早就混有蒙古人的血。”蒙古帝国和苏联都曾经煊赫一时,然后就像草原最终逃脱不了被现代文明淹没一样,导演自己的祖国也崩溃瓦解,他用这样一部挽歌来哀叹自己无以寄予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在米哈尔科夫的纪录片《安娜成长篇》中,当将要出国上学的安娜被问到故乡意味着什么时,她流泪了。这种情感在《蒙古精神》中同样表露无遗。 二、纪实美学形态与超现实主义 《蒙古精神》充满了诗意,影片开场就出现了剧作任务,即妻子帕格玛在生了三个孩子之后不想再生孩子了,让刚波去城里买安全套。谢尔盖这个人物的出现打断了这一切,开始用大量记录形态的镜头展示草原的民俗与风情,例如刚波抓羊、杀羊的段落,基本采纳了“抓取”镜头的方式,而不是一般剧情片中“定制”镜头的方式。进城之后的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