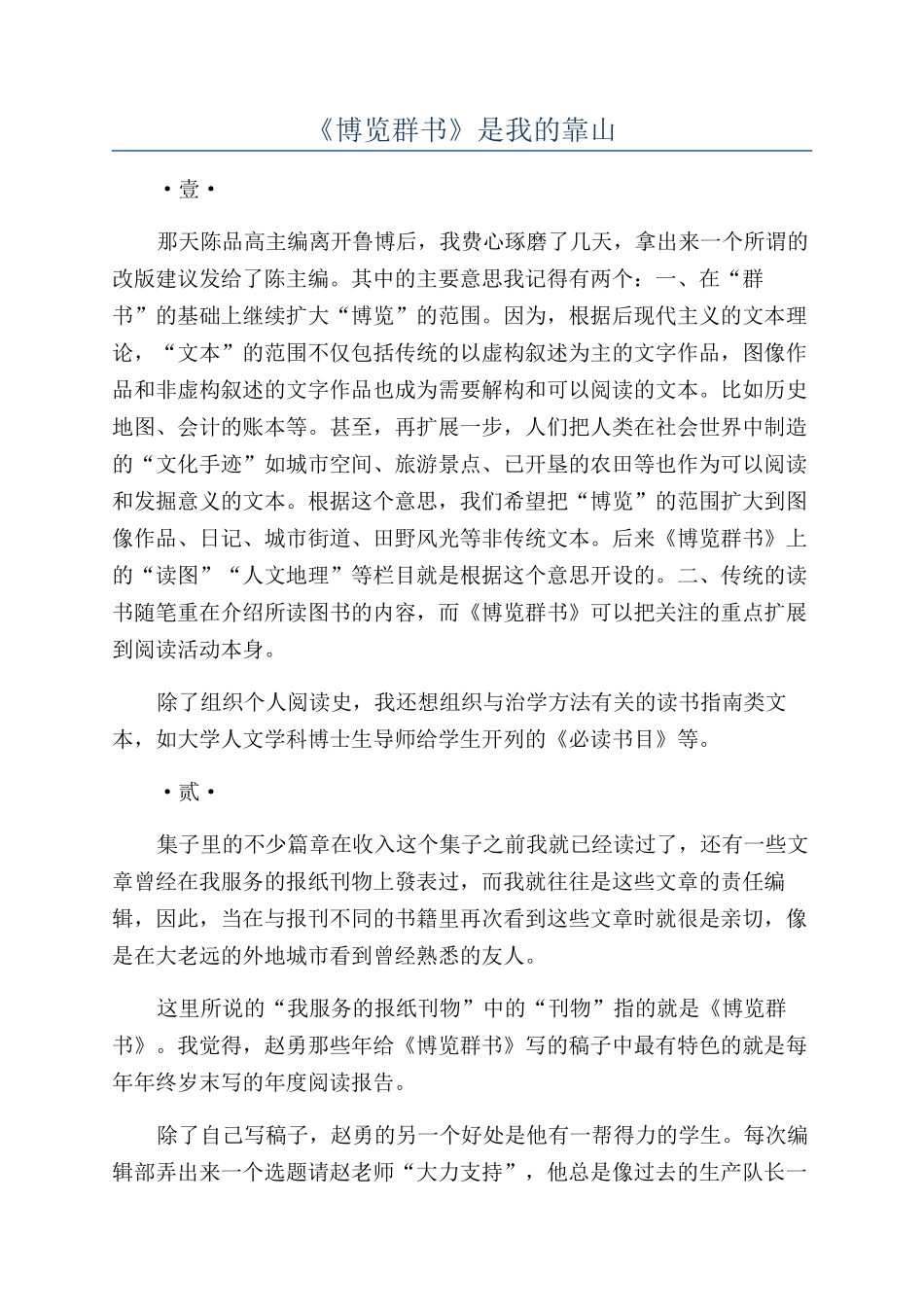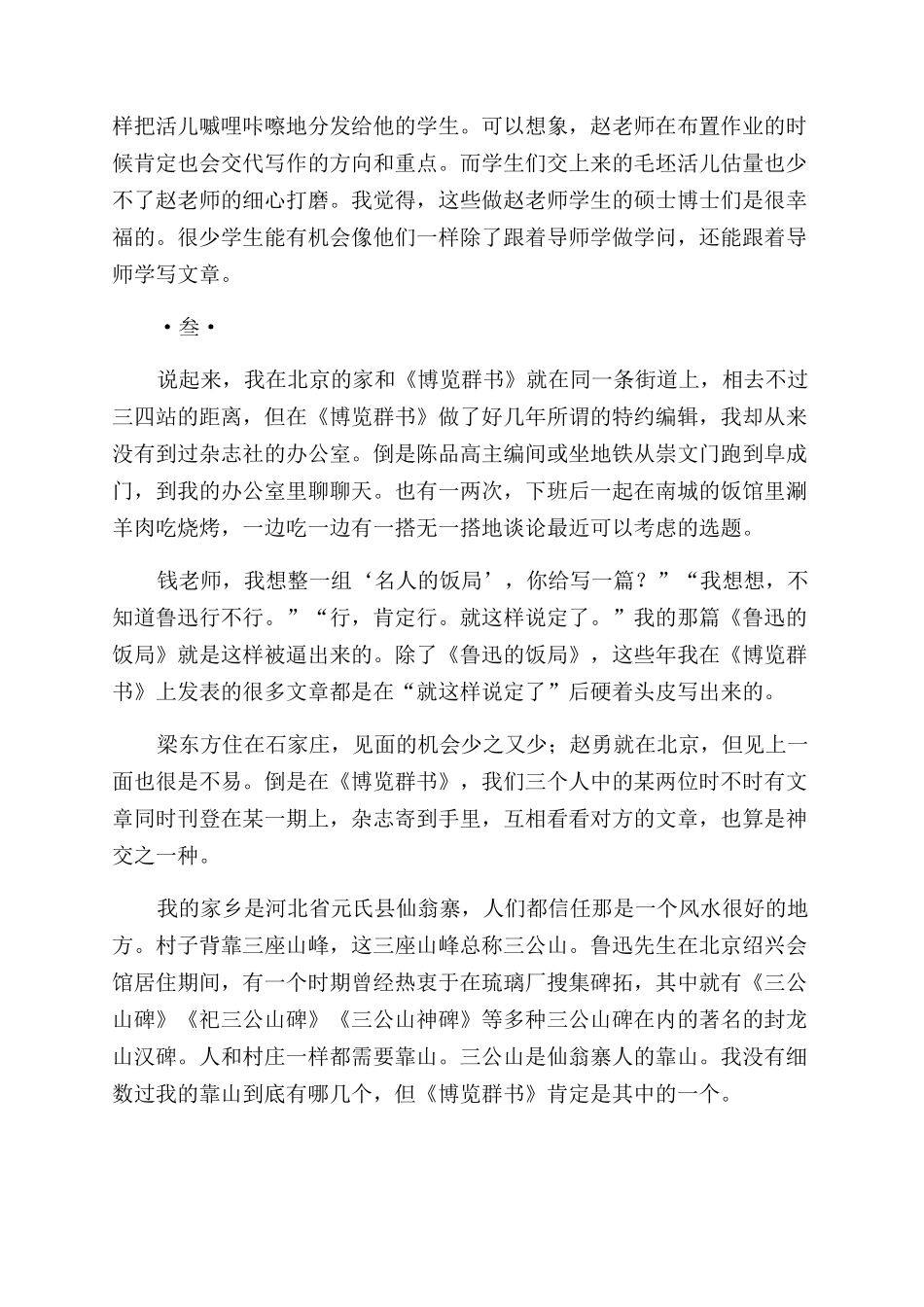《博览群书》是我的靠山·壹·那天陈品高主编离开鲁博后,我费心琢磨了几天,拿出来一个所谓的改版建议发给了陈主编。其中的主要意思我记得有两个:一、在“群书”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博览”的范围。因为,根据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文本”的范围不仅包括传统的以虚构叙述为主的文字作品,图像作品和非虚构叙述的文字作品也成为需要解构和可以阅读的文本。比如历史地图、会计的账本等。甚至,再扩展一步,人们把人类在社会世界中制造的“文化手迹”如城市空间、旅游景点、已开垦的农田等也作为可以阅读和发掘意义的文本。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希望把“博览”的范围扩大到图像作品、日记、城市街道、田野风光等非传统文本。后来《博览群书》上的“读图”“人文地理”等栏目就是根据这个意思开设的。二、传统的读书随笔重在介绍所读图书的内容,而《博览群书》可以把关注的重点扩展到阅读活动本身。除了组织个人阅读史,我还想组织与治学方法有关的读书指南类文本,如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生导师给学生开列的《必读书目》等。·贰·集子里的不少篇章在收入这个集子之前我就已经读过了,还有一些文章曾经在我服务的报纸刊物上發表过,而我就往往是这些文章的责任编辑,因此,当在与报刊不同的书籍里再次看到这些文章时就很是亲切,像是在大老远的外地城市看到曾经熟悉的友人。这里所说的“我服务的报纸刊物”中的“刊物”指的就是《博览群书》。我觉得,赵勇那些年给《博览群书》写的稿子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每年年终岁末写的年度阅读报告。除了自己写稿子,赵勇的另一个好处是他有一帮得力的学生。每次编辑部弄出来一个选题请赵老师“大力支持”,他总是像过去的生产队长一样把活儿嘁哩咔嚓地分发给他的学生。可以想象,赵老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肯定也会交代写作的方向和重点。而学生们交上来的毛坯活儿估量也少不了赵老师的细心打磨。我觉得,这些做赵老师学生的硕士博士们是很幸福的。很少学生能有机会像他们一样除了跟着导师学做学问,还能跟着导师学写文章。·叁·说起来,我在北京的家和《博览群书》就在同一条街道上,相去不过三四站的距离,但在《博览群书》做了好几年所谓的特约编辑,我却从来没有到过杂志社的办公室。倒是陈品高主编间或坐地铁从崇文门跑到阜成门,到我的办公室里聊聊天。也有一两次,下班后一起在南城的饭馆里涮羊肉吃烧烤,一边吃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谈论最近可以考虑的选题。钱老师,我想整一组‘名人的饭局’,你给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