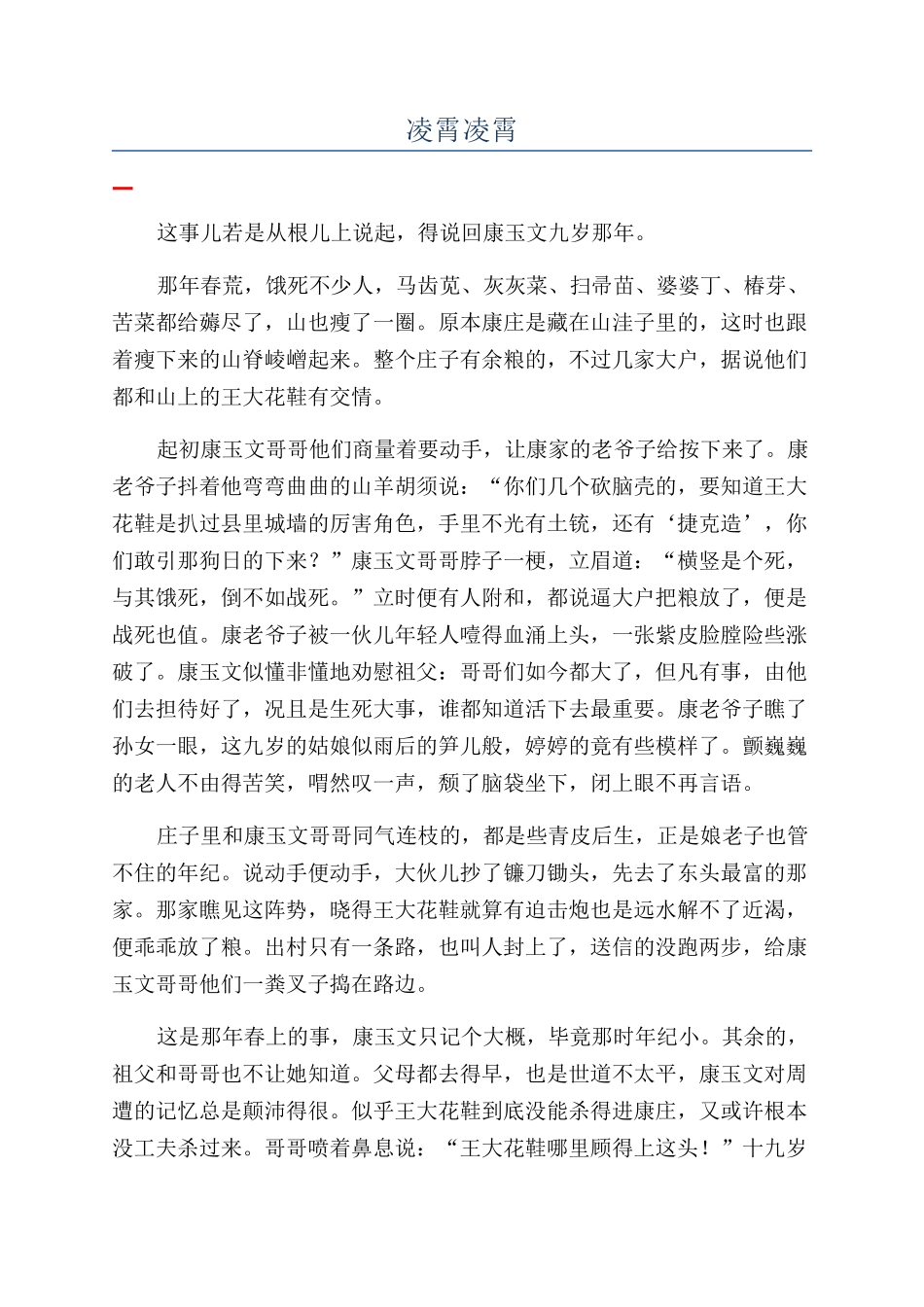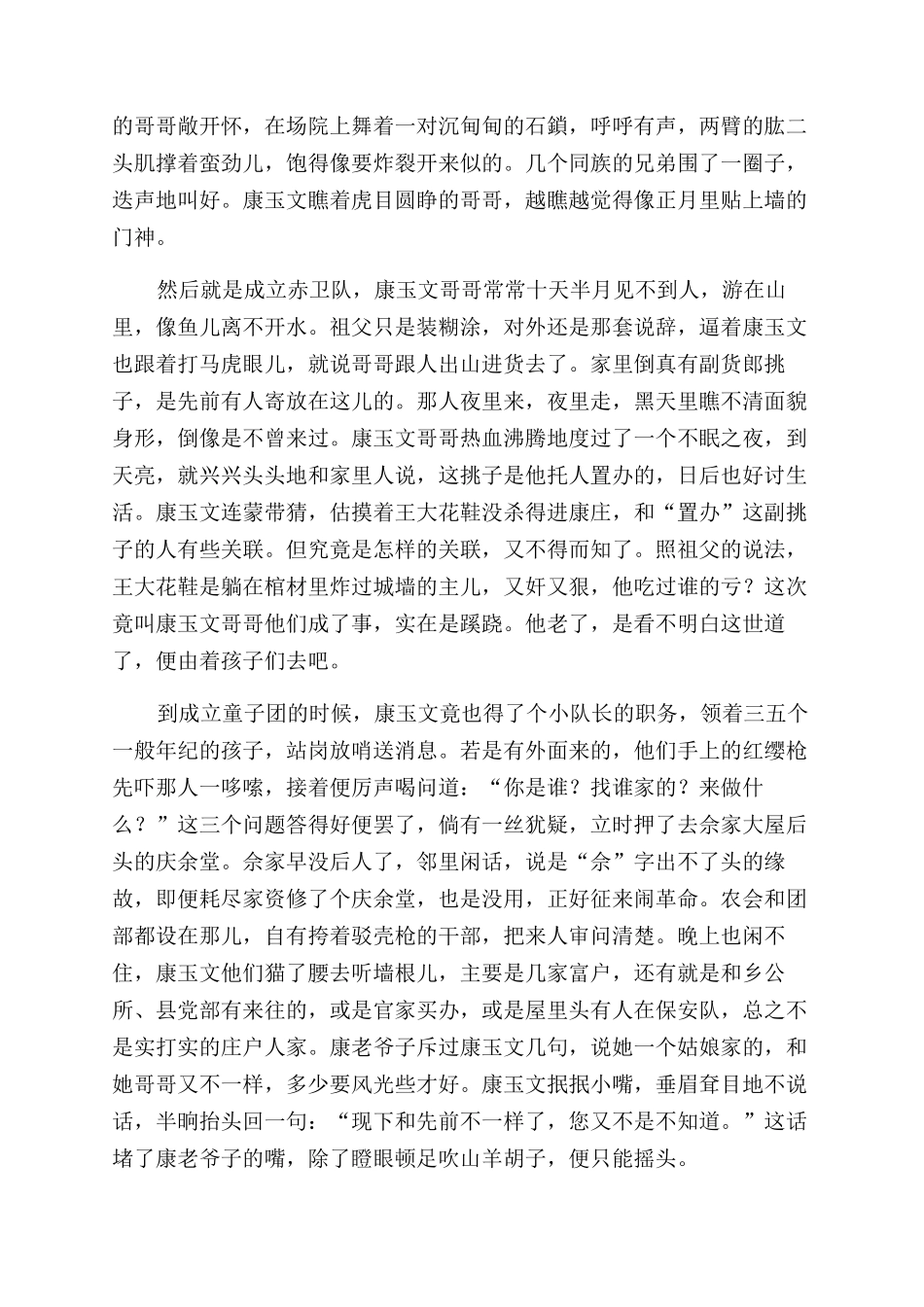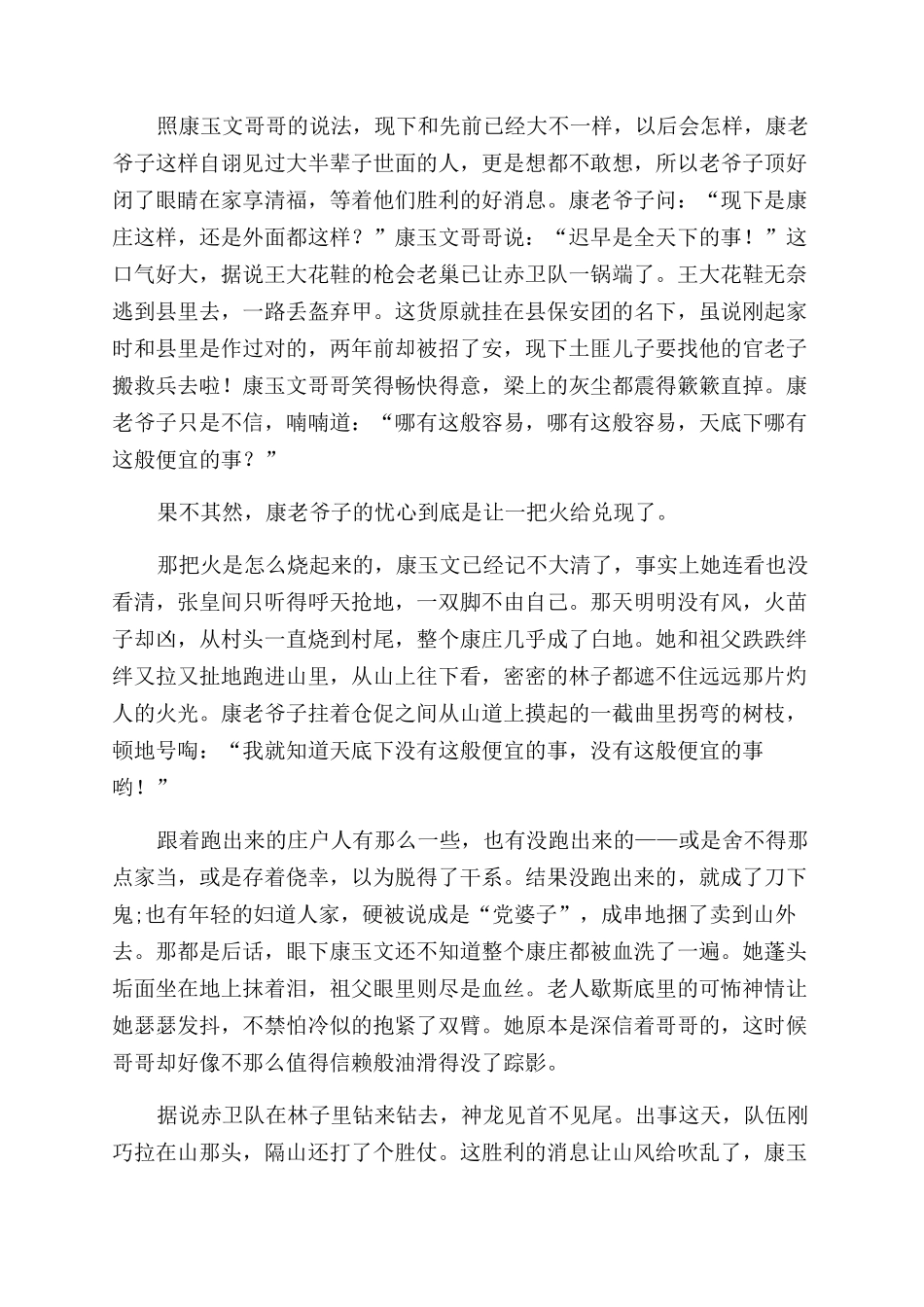凌霄凌霄一这事儿若是从根儿上说起,得说回康玉文九岁那年。那年春荒,饿死不少人,马齿苋、灰灰菜、扫帚苗、婆婆丁、椿芽、苦菜都给薅尽了,山也瘦了一圈。原本康庄是藏在山洼子里的,这时也跟着瘦下来的山脊崚嶒起来。整个庄子有余粮的,不过几家大户,据说他们都和山上的王大花鞋有交情。起初康玉文哥哥他们商量着要动手,让康家的老爷子给按下来了。康老爷子抖着他弯弯曲曲的山羊胡须说:“你们几个砍脑壳的,要知道王大花鞋是扒过县里城墙的厉害角色,手里不光有土铳,还有‘捷克造’,你们敢引那狗日的下来?”康玉文哥哥脖子一梗,立眉道:“横竖是个死,与其饿死,倒不如战死。”立时便有人附和,都说逼大户把粮放了,便是战死也值。康老爷子被一伙儿年轻人噎得血涌上头,一张紫皮脸膛险些涨破了。康玉文似懂非懂地劝慰祖父:哥哥们如今都大了,但凡有事,由他们去担待好了,况且是生死大事,谁都知道活下去最重要。康老爷子瞧了孙女一眼,这九岁的姑娘似雨后的笋儿般,婷婷的竟有些模样了。颤巍巍的老人不由得苦笑,喟然叹一声,颓了脑袋坐下,闭上眼不再言语。庄子里和康玉文哥哥同气连枝的,都是些青皮后生,正是娘老子也管不住的年纪。说动手便动手,大伙儿抄了镰刀锄头,先去了东头最富的那家。那家瞧见这阵势,晓得王大花鞋就算有迫击炮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便乖乖放了粮。出村只有一条路,也叫人封上了,送信的没跑两步,给康玉文哥哥他们一粪叉子捣在路边。这是那年春上的事,康玉文只记个大概,毕竟那时年纪小。其余的,祖父和哥哥也不让她知道。父母都去得早,也是世道不太平,康玉文对周遭的记忆总是颠沛得很。似乎王大花鞋到底没能杀得进康庄,又或许根本没工夫杀过来。哥哥喷着鼻息说:“王大花鞋哪里顾得上这头!”十九岁的哥哥敞开怀,在场院上舞着一对沉甸甸的石鎖,呼呼有声,两臂的肱二头肌撑着蛮劲儿,饱得像要炸裂开来似的。几个同族的兄弟围了一圈子,迭声地叫好。康玉文瞧着虎目圆睁的哥哥,越瞧越觉得像正月里贴上墙的门神。然后就是成立赤卫队,康玉文哥哥常常十天半月见不到人,游在山里,像鱼儿离不开水。祖父只是装糊涂,对外还是那套说辞,逼着康玉文也跟着打马虎眼儿,就说哥哥跟人出山进货去了。家里倒真有副货郎挑子,是先前有人寄放在这儿的。那人夜里来,夜里走,黑天里瞧不清面貌身形,倒像是不曾来过。康玉文哥哥热血沸腾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到天亮,就兴兴头头地和家里人说,这挑子是他托人置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