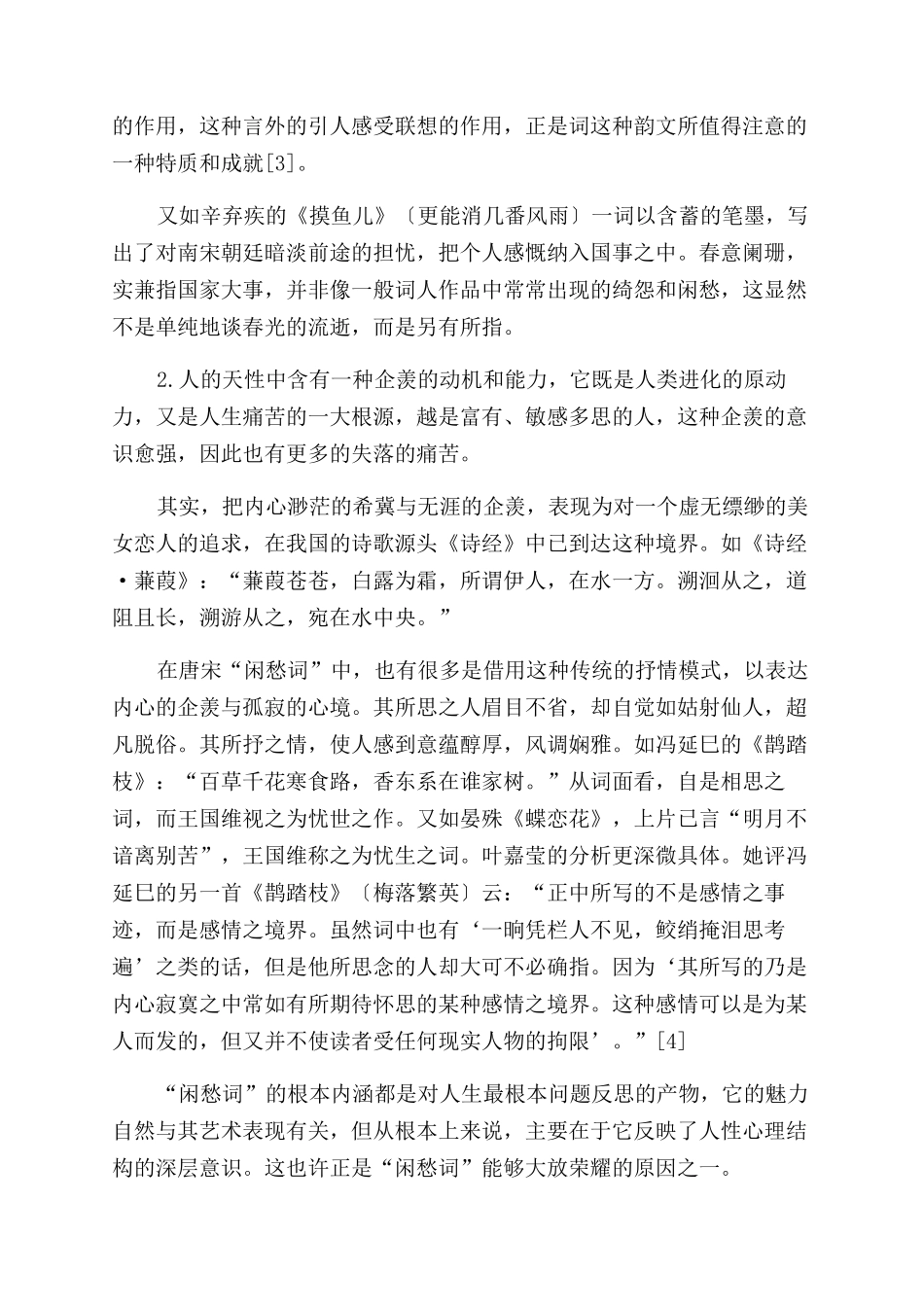唐宋词里话“闲愁摘要:唐宋词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生命力,其内容、题材更多姿多彩。本文从闺情相思、伤春伤别的题材表象,揭示唐宋“闲愁词”中忧生伤世的深层内涵。关键词:唐宋闲愁词闺情相思伤春伤别忧生伤世在唐宋词中,“闲愁”也称“闲情”,如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还称“春愁”、“春恨”。又如李璟的《应天长》:“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摊破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有时候,词人即直接称为“闲愁”,如贺铸的《青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虽用语不同,所表现的却是同样的主题:其意义大约相当或接近于今日的所谓“爱情”[1]。这一点李清照的《一剪梅》“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更是明显的佐证。但唐宋“闲愁词”的主题是否仅此而已?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还反映出以下两个方面的主题:1.“闲愁”作为一种心理意识,是时代环境、个人遭际等多种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唐宋词的“闲愁”主题,往往就存在于另有寄予的伤别之词和近于兴的伤春之词中。这种情绪,正如叶嘉莹评晏殊的《踏莎行》〔细草愁烟〕词云:“可能会有人认为,晏殊这里无非是表现了一种伤春的情绪,欣赏起来,于现实并无怎样重大深远的意义。”当然,我们这里欣赏晏殊的词,并非是要大家同去伤春落泪,而是在晏殊的伤春情绪中,实在是有一种对时间年华流逝的深切的慨叹和惋惜存在,更在极幽微的情思的叙写中,流露出了很深挚又很高远的一份追寻向往的心意。这种情意,虽然外表看来也许只不过是伤春怀人之情而已,但是隐然间却可以使读者的心灵感情感受到提升的作用,这种言外的引人感受联想的作用,正是词这种韵文所值得注意的一种特质和成就[3]。又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词以含蓄的笔墨,写出了对南宋朝廷暗淡前途的担忧,把个人感慨纳入国事之中。春意阑珊,实兼指国家大事,并非像一般词人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绮怨和闲愁,这显然不是单纯地谈春光的流逝,而是另有所指。2.人的天性中含有一种企羡的动机和能力,它既是人类进化的原动力,又是人生痛苦的一大根源,越是富有、敏感多思的人,这种企羡的意识愈强,因此也有更多的失落的痛苦。其实,把内心渺茫的希冀与无涯的企羡,表现为对一个虚无缥缈的美女恋人的追求,在我国的诗歌源头《诗经》中已到达这种境界。如《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