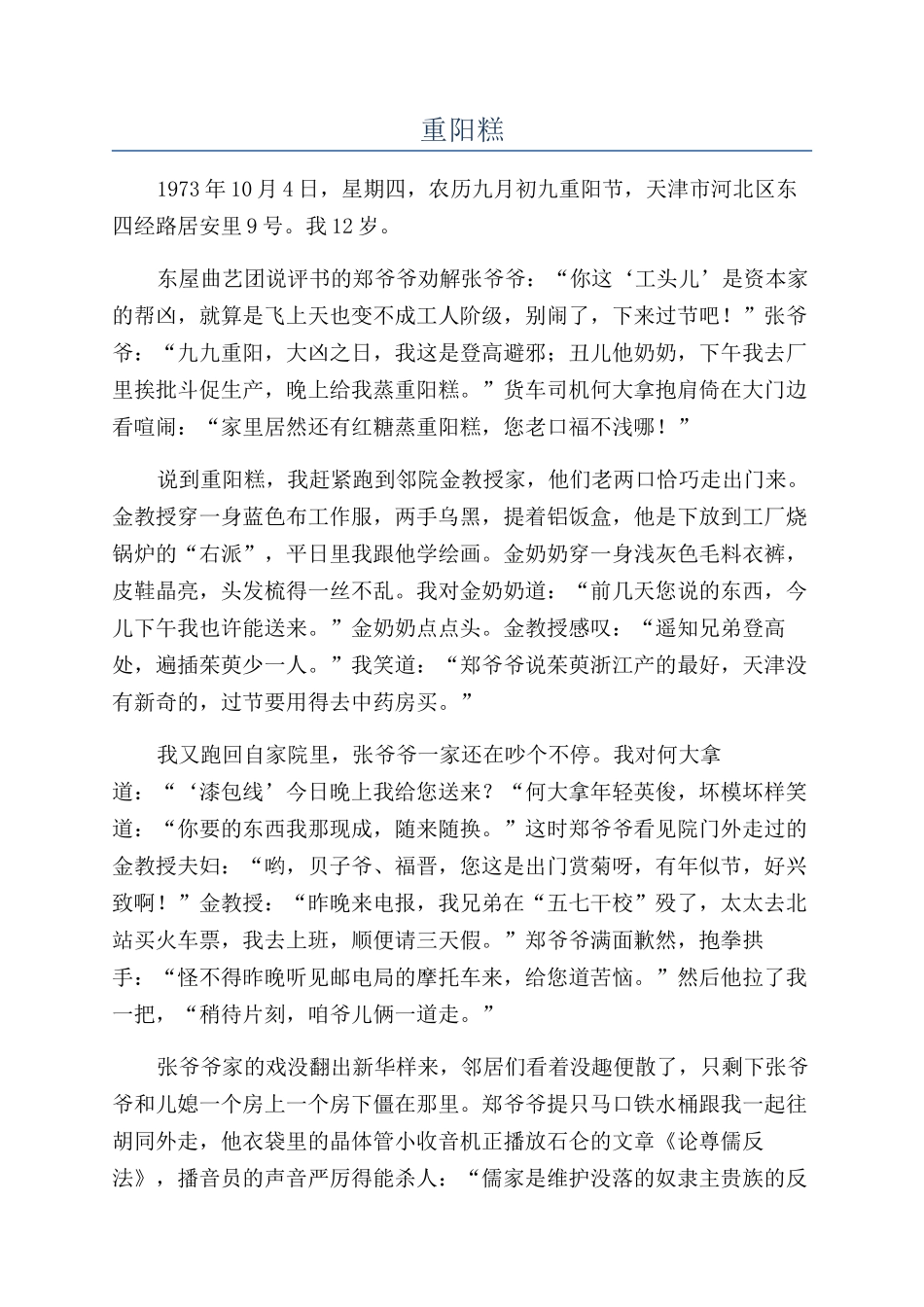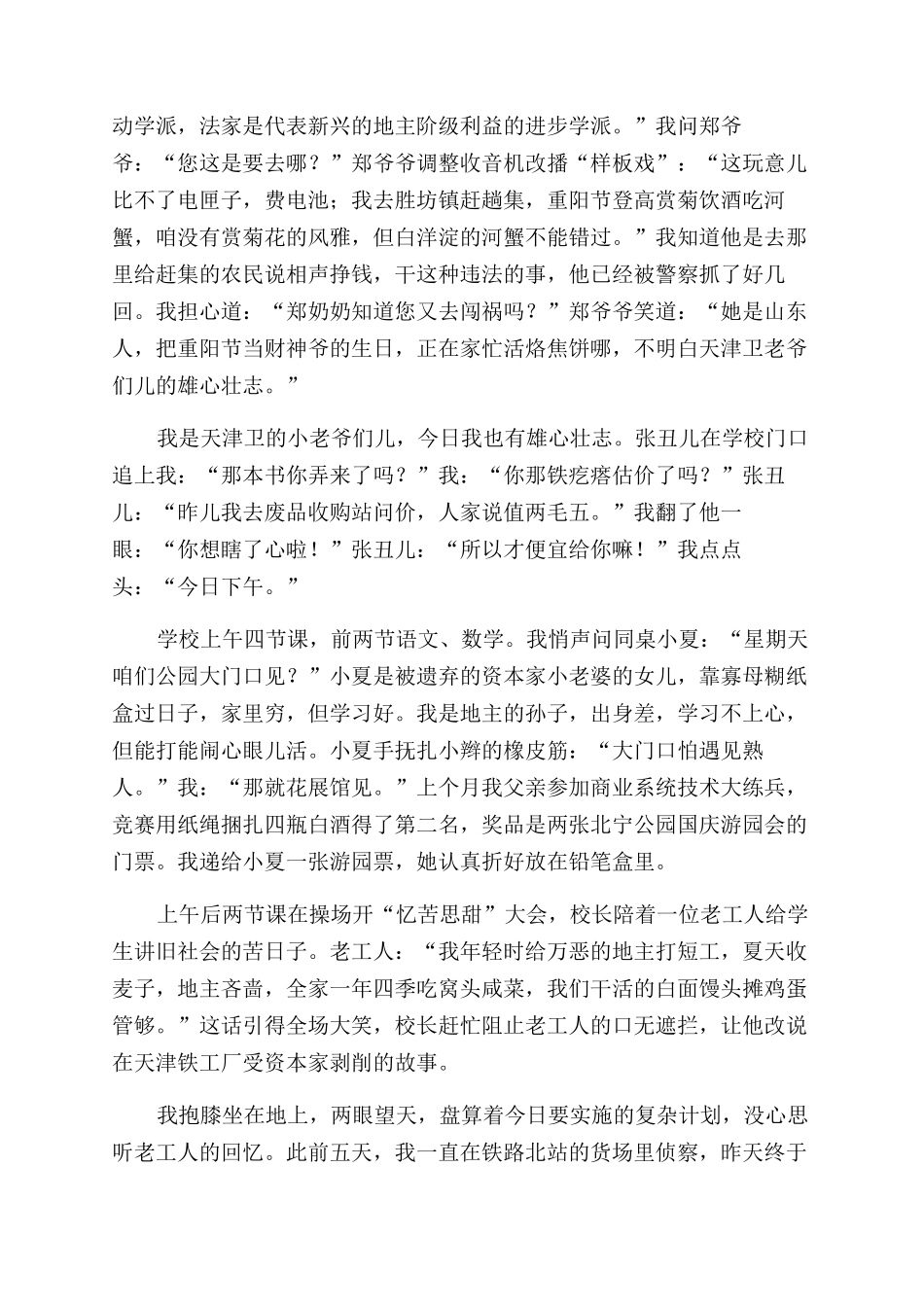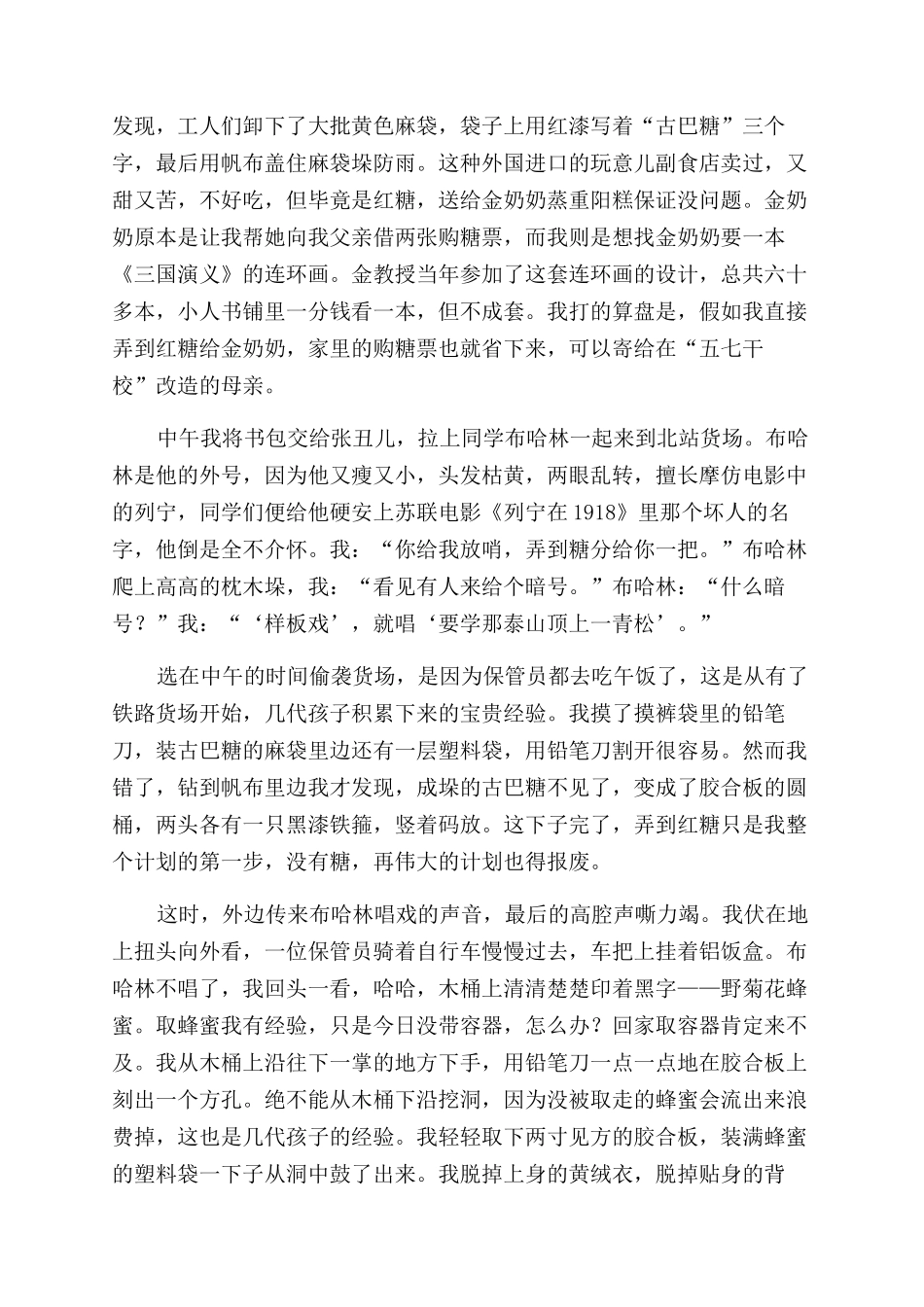重阳糕1973 年 10 月 4 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天津市河北区东四经路居安里 9 号。我 12 岁。东屋曲艺团说评书的郑爷爷劝解张爷爷:“你这‘工头儿’是资本家的帮凶,就算是飞上天也变不成工人阶级,别闹了,下来过节吧!”张爷爷:“九九重阳,大凶之日,我这是登高避邪;丑儿他奶奶,下午我去厂里挨批斗促生产,晚上给我蒸重阳糕。”货车司机何大拿抱肩倚在大门边看喧闹:“家里居然还有红糖蒸重阳糕,您老口福不浅哪!”说到重阳糕,我赶紧跑到邻院金教授家,他们老两口恰巧走出门来。金教授穿一身蓝色布工作服,两手乌黑,提着铝饭盒,他是下放到工厂烧锅炉的“右派”,平日里我跟他学绘画。金奶奶穿一身浅灰色毛料衣裤,皮鞋晶亮,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我对金奶奶道:“前几天您说的东西,今儿下午我也许能送来。”金奶奶点点头。金教授感叹:“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笑道:“郑爷爷说茱萸浙江产的最好,天津没有新奇的,过节要用得去中药房买。”我又跑回自家院里,张爷爷一家还在吵个不停。我对何大拿道:“‘漆包线’今日晚上我给您送来?“何大拿年轻英俊,坏模坏样笑道:“你要的东西我那现成,随来随换。”这时郑爷爷看见院门外走过的金教授夫妇:“哟,贝子爷、福晋,您这是出门赏菊呀,有年似节,好兴致啊!”金教授:“昨晚来电报,我兄弟在“五七干校”殁了,太太去北站买火车票,我去上班,顺便请三天假。”郑爷爷满面歉然,抱拳拱手:“怪不得昨晚听见邮电局的摩托车来,给您道苦恼。”然后他拉了我一把,“稍待片刻,咱爷儿俩一道走。”张爷爷家的戏没翻出新华样来,邻居们看着没趣便散了,只剩下张爷爷和儿媳一个房上一个房下僵在那里。郑爷爷提只马口铁水桶跟我一起往胡同外走,他衣袋里的晶体管小收音机正播放石仑的文章《论尊儒反法》,播音员的声音严厉得能杀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我问郑爷爷:“您这是要去哪?”郑爷爷调整收音机改播“样板戏”:“这玩意儿比不了电匣子,费电池;我去胜坊镇赶趟集,重阳节登高赏菊饮酒吃河蟹,咱没有赏菊花的风雅,但白洋淀的河蟹不能错过。”我知道他是去那里给赶集的农民说相声挣钱,干这种违法的事,他已经被警察抓了好几回。我担心道:“郑奶奶知道您又去闯祸吗?”郑爷爷笑道:“她是山东人,把重阳节当财神爷的生日,正在家忙活烙焦饼哪,不明白天津卫老爷们儿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