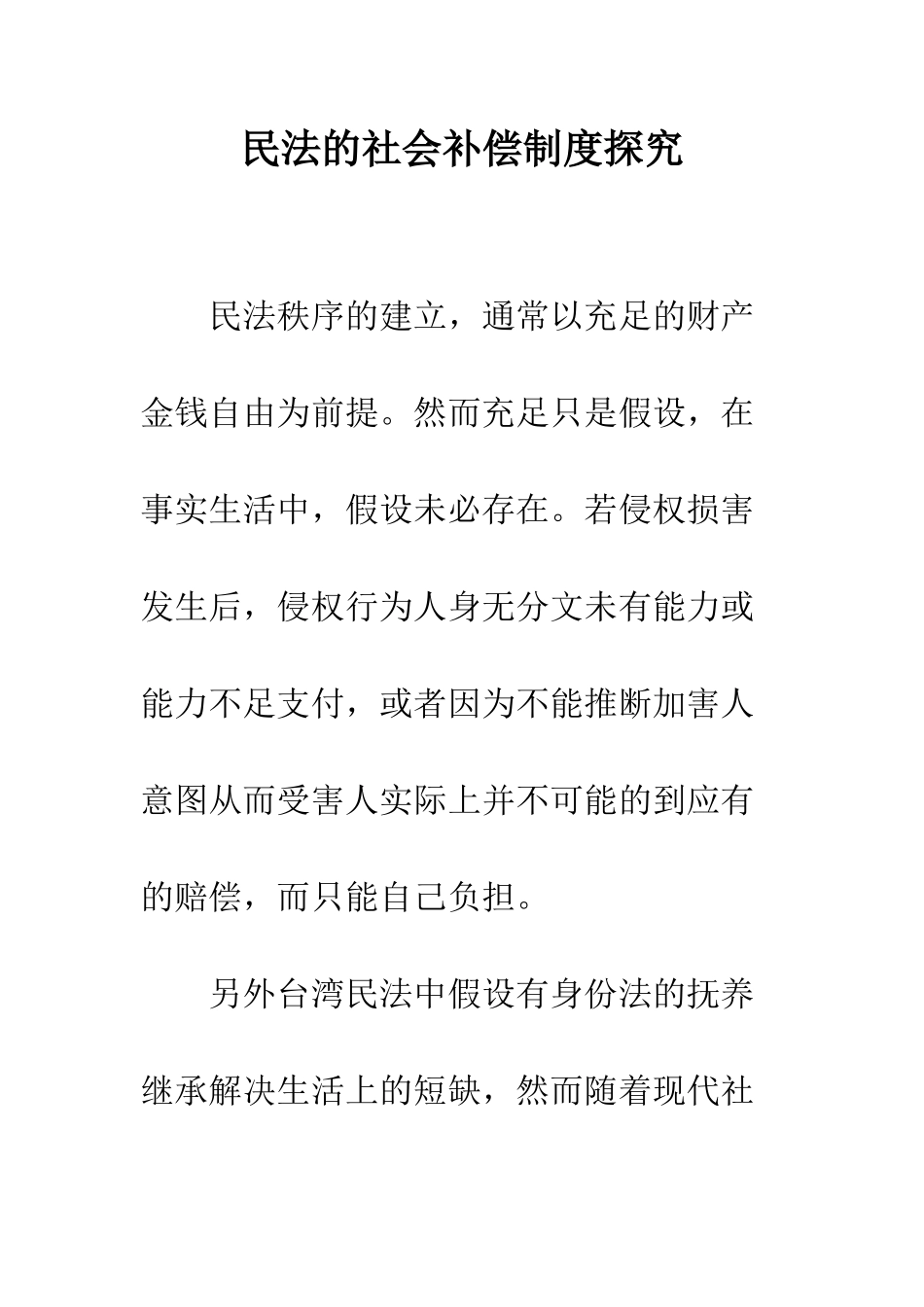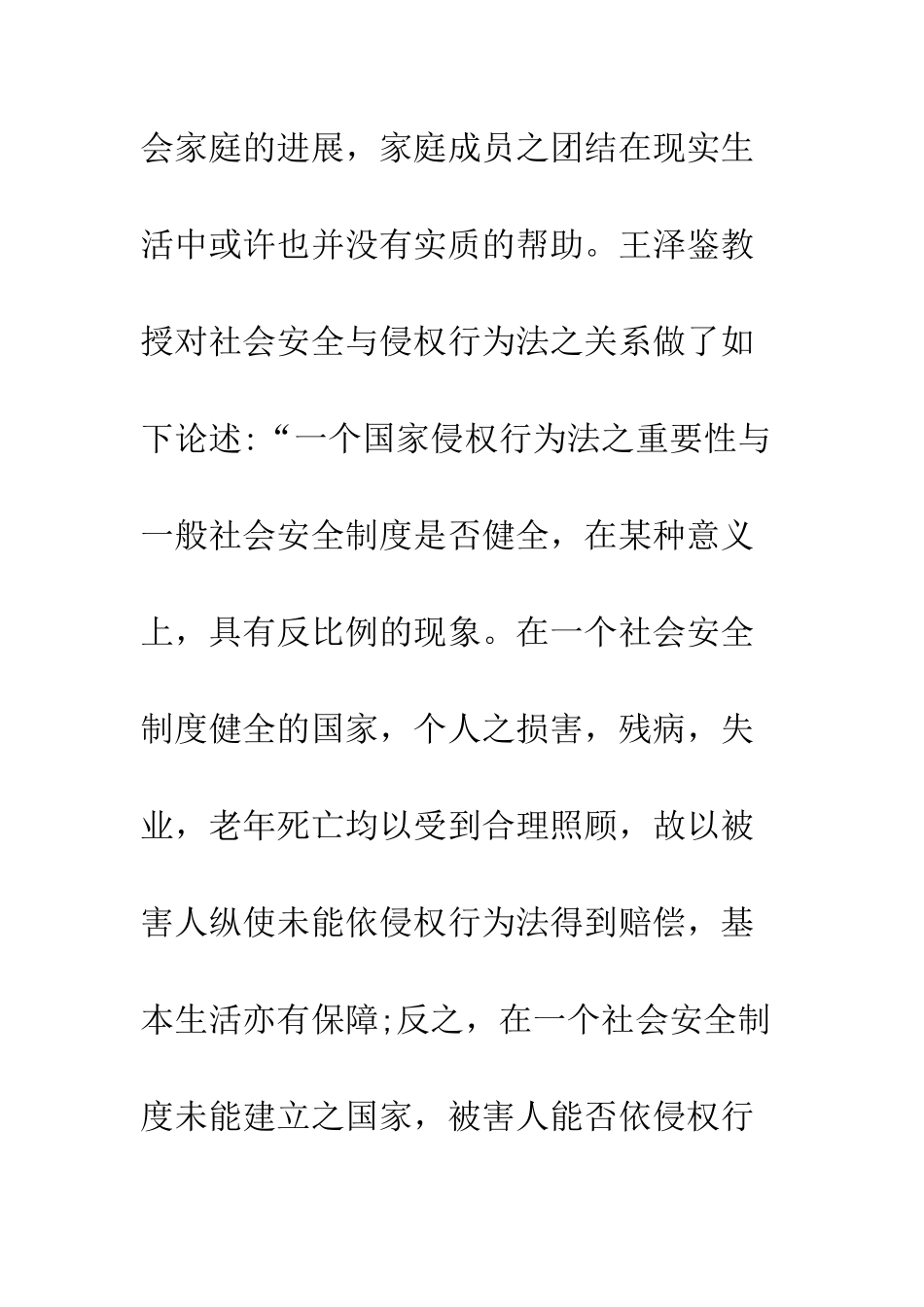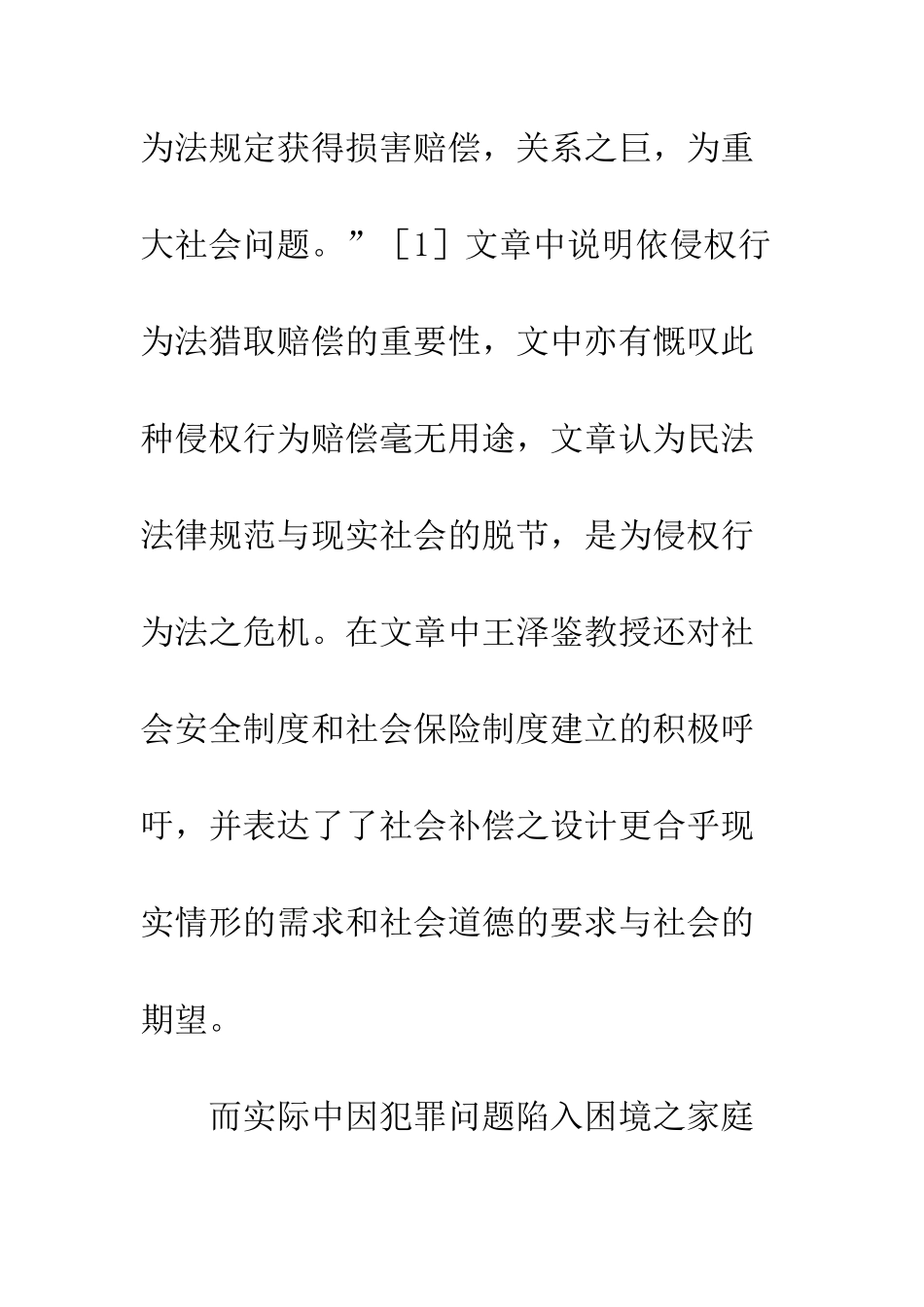民法的社会补偿制度探究 民法秩序的建立,通常以充足的财产金钱自由为前提。然而充足只是假设,在事实生活中,假设未必存在。若侵权损害发生后,侵权行为人身无分文未有能力或能力不足支付,或者因为不能推断加害人意图从而受害人实际上并不可能的到应有的赔偿,而只能自己负担。 另外台湾民法中假设有身份法的抚养继承解决生活上的短缺,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家庭的进展,家庭成员之团结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也并没有实质的帮助。王泽鉴教授对社会安全与侵权行为法之关系做了如下论述:“一个国家侵权行为法之重要性与一般社会安全制度是否健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反比例的现象。在一个社会安全制度健全的国家,个人之损害,残病,失业,老年死亡均以受到合理照顾,故以被害人纵使未能依侵权行为法得到赔偿,基本生活亦有保障;反之,在一个社会安全制度未能建立之国家,被害人能否依侵权行为法规定获得损害赔偿,关系之巨,为重大社会问题。”[1]文章中说明依侵权行为法猎取赔偿的重要性,文中亦有慨叹此种侵权行为赔偿毫无用途,文章认为民法法律规范与现实社会的脱节,是为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在文章中王泽鉴教授还对社会安全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的积极呼吁,并表达了了社会补偿之设计更合乎现实情形的需求和社会道德的要求与社会的期望。 而实际中因犯罪问题陷入困境之家庭对福利服务与社会救助也难以期待。如此而来,犯罪被害人既无法取得应该所获赔偿,亦无法获得社会补偿给付。社会的进展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被害人希望转向依赖亲朋好友慈善机构的帮助时,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得求助于家庭亲朋的想法也愈发遥远。 台湾在侵权行为方面已有社会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 1998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之前,对于被害人的救助补偿制度的协助有劳保私人给付的代位求偿,交通事故的补偿基金,劳灾补偿基金等;另外还有特别法律的制定,如二二八事件补偿条例,白色恐怖补偿条例等特别的法律。对于《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林纪东先生早在1958 年就已引入犯罪被害人补偿的概念,甚至将其定位社会安全制度的一环[2]。即便是仍有反对的声音,如蔡墩铭因反对国家责任说而对此制度有微词[3]。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清,社会补偿是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济善而非单纯所认为的责任归咎。透过社会补偿,我们对于社会的弱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与保护是符合人类道德伦理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需求的。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