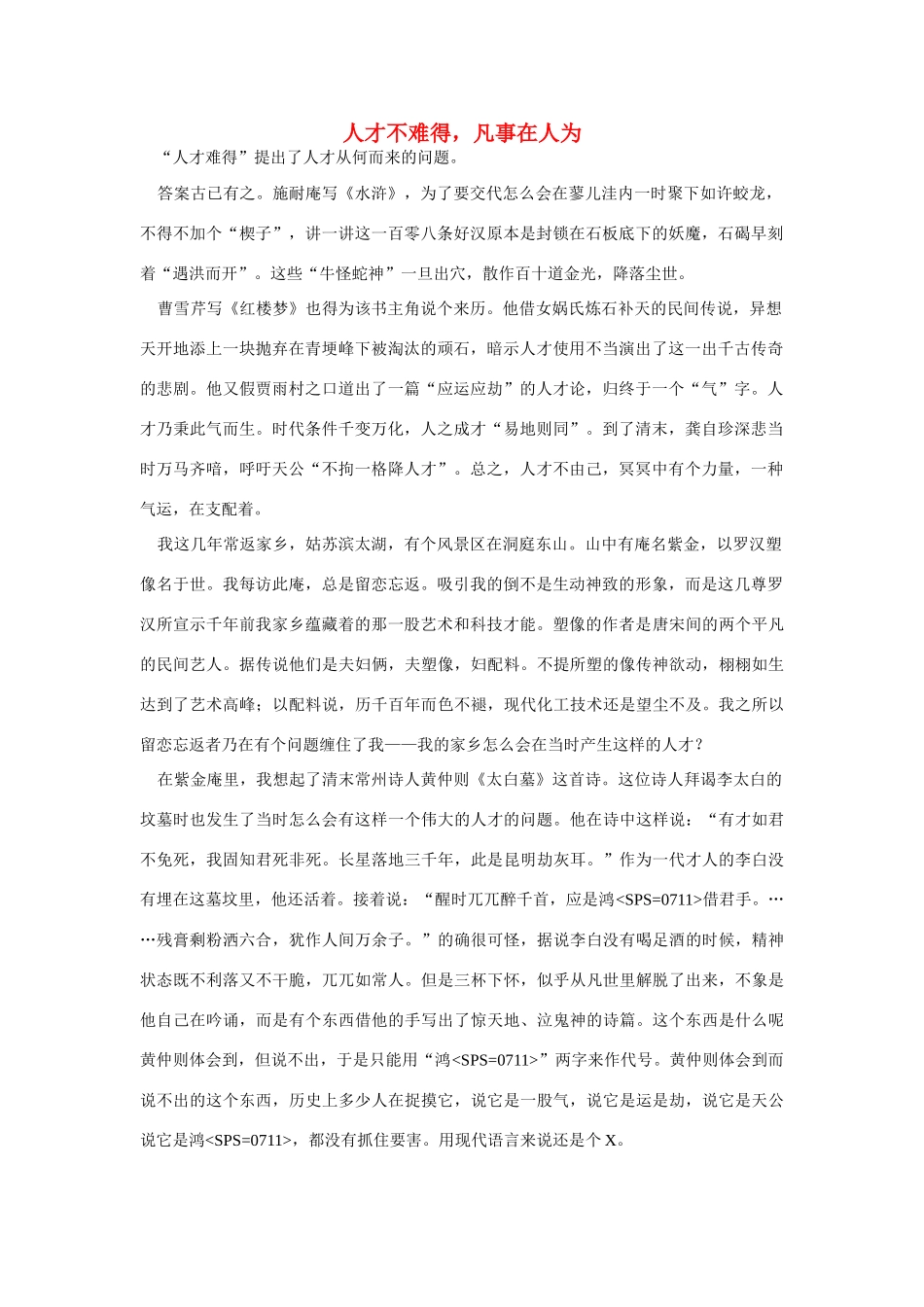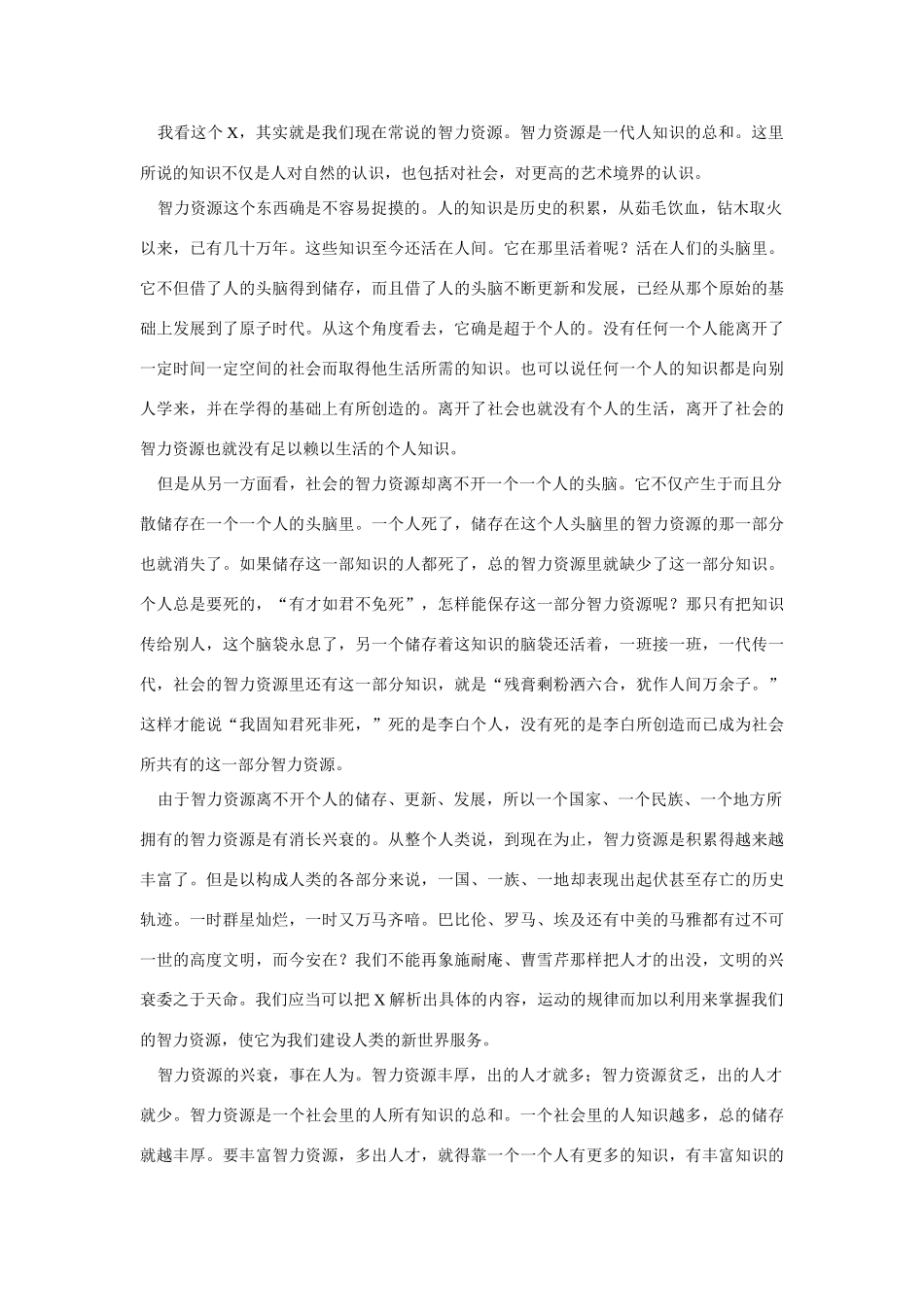人才不难得,凡事在人为 “人才难得”提出了人才从何而来的问题。 答案古已有之。施耐庵写《水浒》,为了要交代怎么会在蓼儿洼内一时聚下如许蛟龙,不得不加个“楔子”,讲一讲这一百零八条好汉原本是封锁在石板底下的妖魔,石碣早刻着“遇洪而开”。这些“牛怪蛇神”一旦出穴,散作百十道金光,降落尘世。 曹雪芹写《红楼梦》也得为该书主角说个来历。他借女娲氏炼石补天的民间传说,异想天开地添上一块抛弃在青埂峰下被淘汰的顽石,暗示人才使用不当演出了这一出千古传奇的悲剧。他又假贾雨村之口道出了一篇“应运应劫”的人才论,归终于一个“气”字。人才乃秉此气而生。时代条件千变万化,人之成才“易地则同”。到了清末,龚自珍深悲当时万马齐喑,呼吁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总之,人才不由己,冥冥中有个力量,一种气运,在支配着。 我这几年常返家乡,姑苏滨太湖,有个风景区在洞庭东山。山中有庵名紫金,以罗汉塑像名于世。我每访此庵,总是留恋忘返。吸引我的倒不是生动神致的形象,而是这几尊罗汉所宣示千年前我家乡蕴藏着的那一股艺术和科技才能。塑像的作者是唐宋间的两个平凡的民间艺人。据传说他们是夫妇俩,夫塑像,妇配料。不提所塑的像传神欲动,栩栩如生达到了艺术高峰;以配料说,历千百年而色不褪,现代化工技术还是望尘不及。我之所以留恋忘返者乃在有个问题缠住了我——我的家乡怎么会在当时产生这样的人才? 在紫金庵里,我想起了清末常州诗人黄仲则《太白墓》这首诗。这位诗人拜谒李太白的坟墓时也发生了当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才的问题。他在诗中这样说:“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长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作为一代才人的李白没有埋在这墓坟里,他还活着。接着说:“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借君手。……残膏剩粉洒六合,犹作人间万余子。”的确很可怪,据说李白没有喝足酒的时候,精神状态既不利落又不干脆,兀兀如常人。但是三杯下怀,似乎从凡世里解脱了出来,不象是他自己在吟诵,而是有个东西借他的手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仲则体会到,但说不出,于是只能用“鸿”两字来作代号。黄仲则体会到而说不出的这个东西,历史上多少人在捉摸它,说它是一股气,说它是运是劫,说它是天公说它是鸿,都没有抓住要害。用现代语言来说还是个 X。 我看这个 X,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智力资源。智力资源是一代人知识的总和。这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