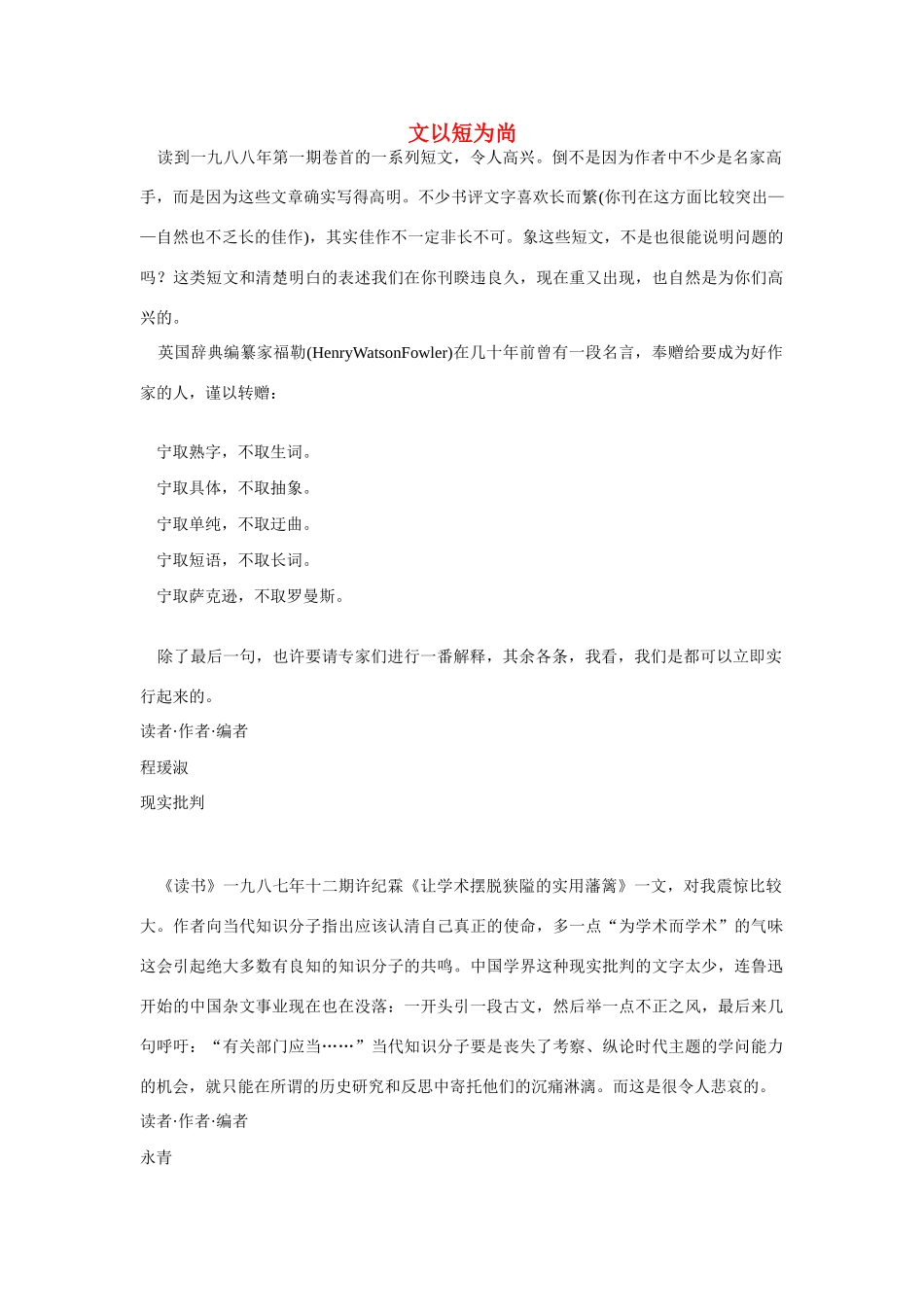文以短为尚 读到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卷首的一系列短文,令人高兴。倒不是因为作者中不少是名家高手,而是因为这些文章确实写得高明。不少书评文字喜欢长而繁(你刊在这方面比较突出——自然也不乏长的佳作),其实佳作不一定非长不可。象这些短文,不是也很能说明问题的吗?这类短文和清楚明白的表述我们在你刊睽违良久,现在重又出现,也自然是为你们高兴的。 英国辞典编纂家福勒(HenryWatsonFowler)在几十年前曾有一段名言,奉赠给要成为好作家的人,谨以转赠: 宁取熟字,不取生词。 宁取具体,不取抽象。 宁取单纯,不取迂曲。 宁取短语,不取长词。 宁取萨克逊,不取罗曼斯。 除了最后一句,也许要请专家们进行一番解释,其余各条,我看,我们是都可以立即实行起来的。读者·作者·编者程瑗淑现实批判 《读书》一九八七年十二期许纪霖《让学术摆脱狭隘的实用藩篱》一文,对我震惊比较大。作者向当代知识分子指出应该认清自己真正的使命,多一点“为学术而学术”的气味这会引起绝大多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中国学界这种现实批判的文字太少,连鲁迅开始的中国杂文事业现在也在没落:一开头引一段古文,然后举一点不正之风,最后来几句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当代知识分子要是丧失了考察、纵论时代主题的学问能力的机会,就只能在所谓的历史研究和反思中寄托他们的沉痛淋漓。而这是很令人悲哀的。读者·作者·编者永青法与科学 读了你刊介绍《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文后,深感对社会现象求取科学解释的必要。我是研究法律的,觉得法现象很多表现出与某些自然现象的类似性。如对各种犯罪的确定,很象几何学中的相似关系。几何学中的相似关系扩展可为“同构”现象,在法现象中,似乎也有一些“同构”存在。在社会中,是否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使法不起作用的“黑洞”存在?它们如何构成?社会里有多少这样的“黑洞”才算正常?另外,法的运行似乎也可理解为一个传导网,如何使法在运行中得到理想的实现?从环境科学中我们也可得到启发:是否需要对法制环境实行保护?政策的大量使用带给法的负面影响是否一种污染?如何消除法环境的污染源? 我想,如果想将科学、法学相结合,那不仅仅是起草一部科技法的事。读者·作者·编者鲜江凌关心自然科学 在家父影响下,我喜欢上了《读书》,从创刊号到现在,是“眼盯”着《读书》过来的。父子之间经常交流对《读书》的看法。自从读了伍晓鹰、张维平的《对话》以后,我觉得这个刊物办得“近”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