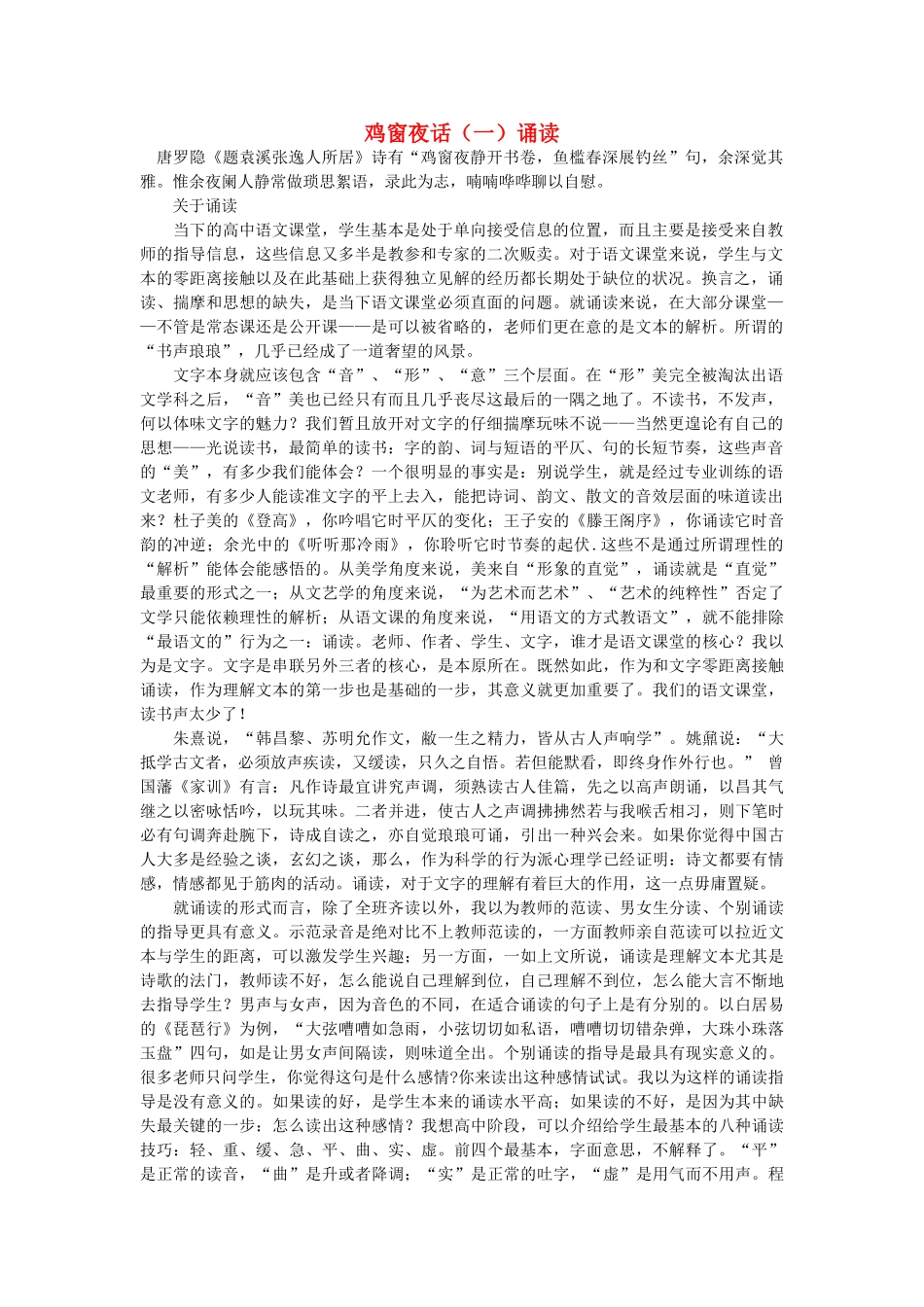鸡窗夜话(一)诵读 唐罗隐《题袁溪张逸人所居》诗有“鸡窗夜静开书卷,鱼槛春深展钓丝”句,余深觉其雅。惟余夜阑人静常做琐思絮语,录此为志,喃喃哗哗聊以自慰。 关于诵读 当下的高中语文课堂,学生基本是处于单向接受信息的位置,而且主要是接受来自教师的指导信息,这些信息又多半是教参和专家的二次贩卖。对于语文课堂来说,学生与文本的零距离接触以及在此基础上获得独立见解的经历都长期处于缺位的状况。换言之,诵读、揣摩和思想的缺失,是当下语文课堂必须直面的问题。就诵读来说,在大部分课堂——不管是常态课还是公开课——是可以被省略的,老师们更在意的是文本的解析。所谓的“书声琅琅”,几乎已经成了一道奢望的风景。 文字本身就应该包含“音”、“形”、“意”三个层面。在“形”美完全被淘汰出语文学科之后,“音”美也已经只有而且几乎丧尽这最后的一隅之地了。不读书,不发声,何以体味文字的魅力?我们暂且放开对文字的仔细揣摩玩味不说——当然更遑论有自己的思想——光说读书,最简单的读书:字的韵、词与短语的平仄、句的长短节奏,这些声音的“美”,有多少我们能体会?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别说学生,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语文老师,有多少人能读准文字的平上去入,能把诗词、韵文、散文的音效层面的味道读出来?杜子美的《登高》,你吟唱它时平仄的变化;王子安的《滕王阁序》,你诵读它时音韵的冲逆;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你聆听它时节奏的起伏.这些不是通过所谓理性的“解析”能体会能感悟的。从美学角度来说,美来自“形象的直觉”,诵读就是“直觉”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从文艺学的角度来说,“为艺术而艺术”、“艺术的纯粹性”否定了文学只能依赖理性的解析;从语文课的角度来说,“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就不能排除“最语文的”行为之一:诵读。老师、作者、学生、文字,谁才是语文课堂的核心?我以为是文字。文字是串联另外三者的核心,是本原所在。既然如此,作为和文字零距离接触诵读,作为理解文本的第一步也是基础的一步,其意义就更加重要了。我们的语文课堂,读书声太少了! 朱熹说,“韩昌黎、苏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从古人声响学”。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须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 曾国藩《家训》有言: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