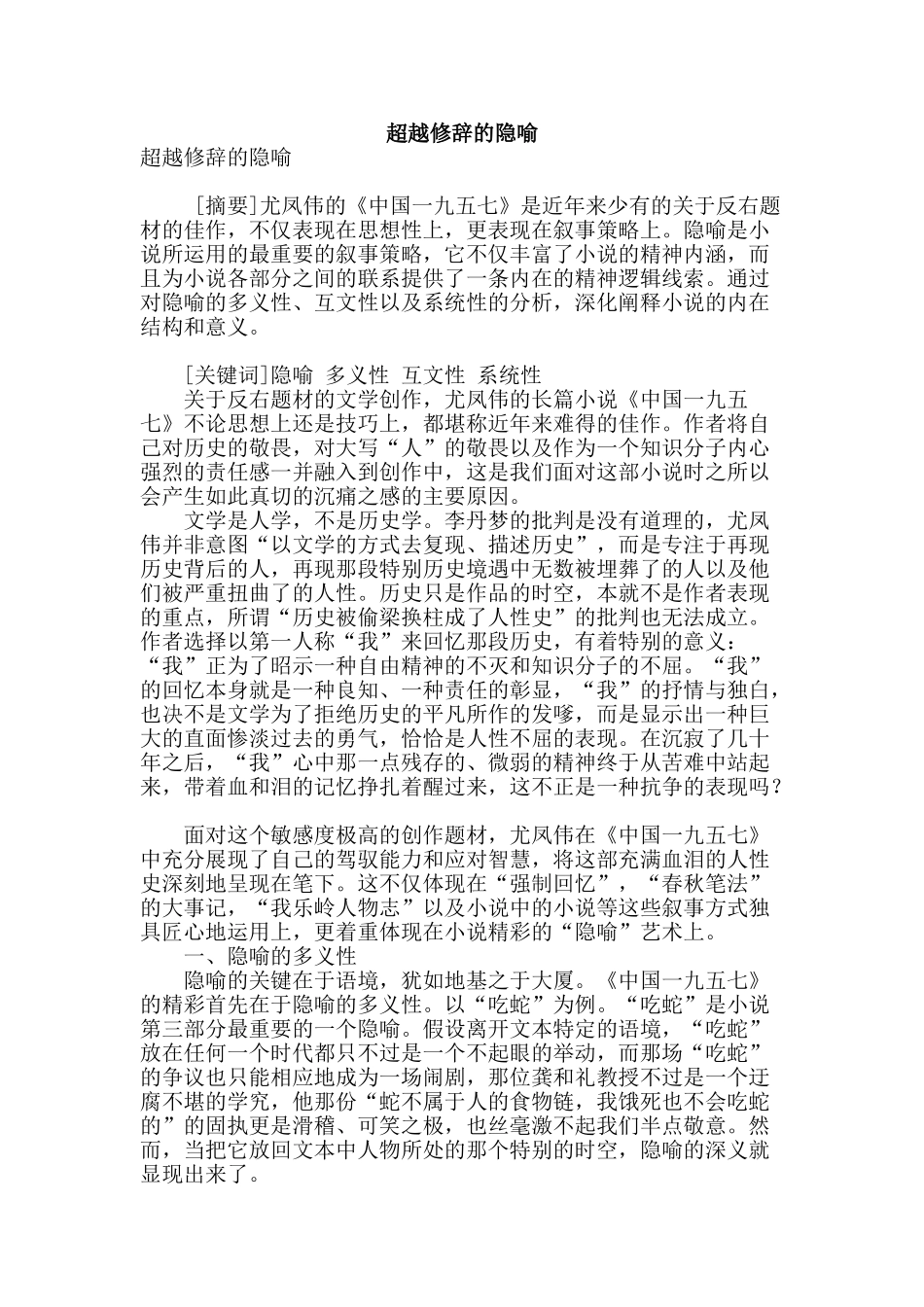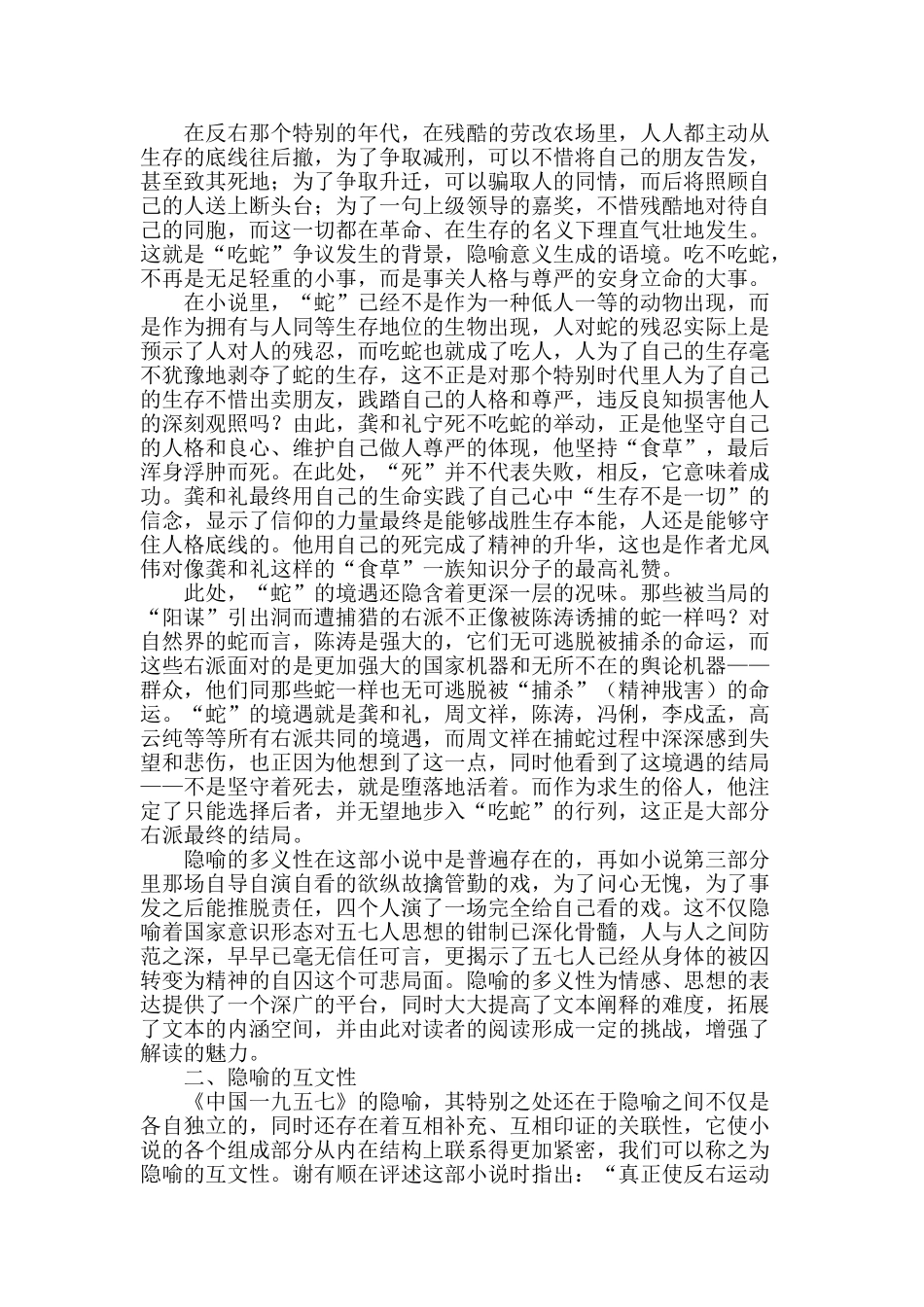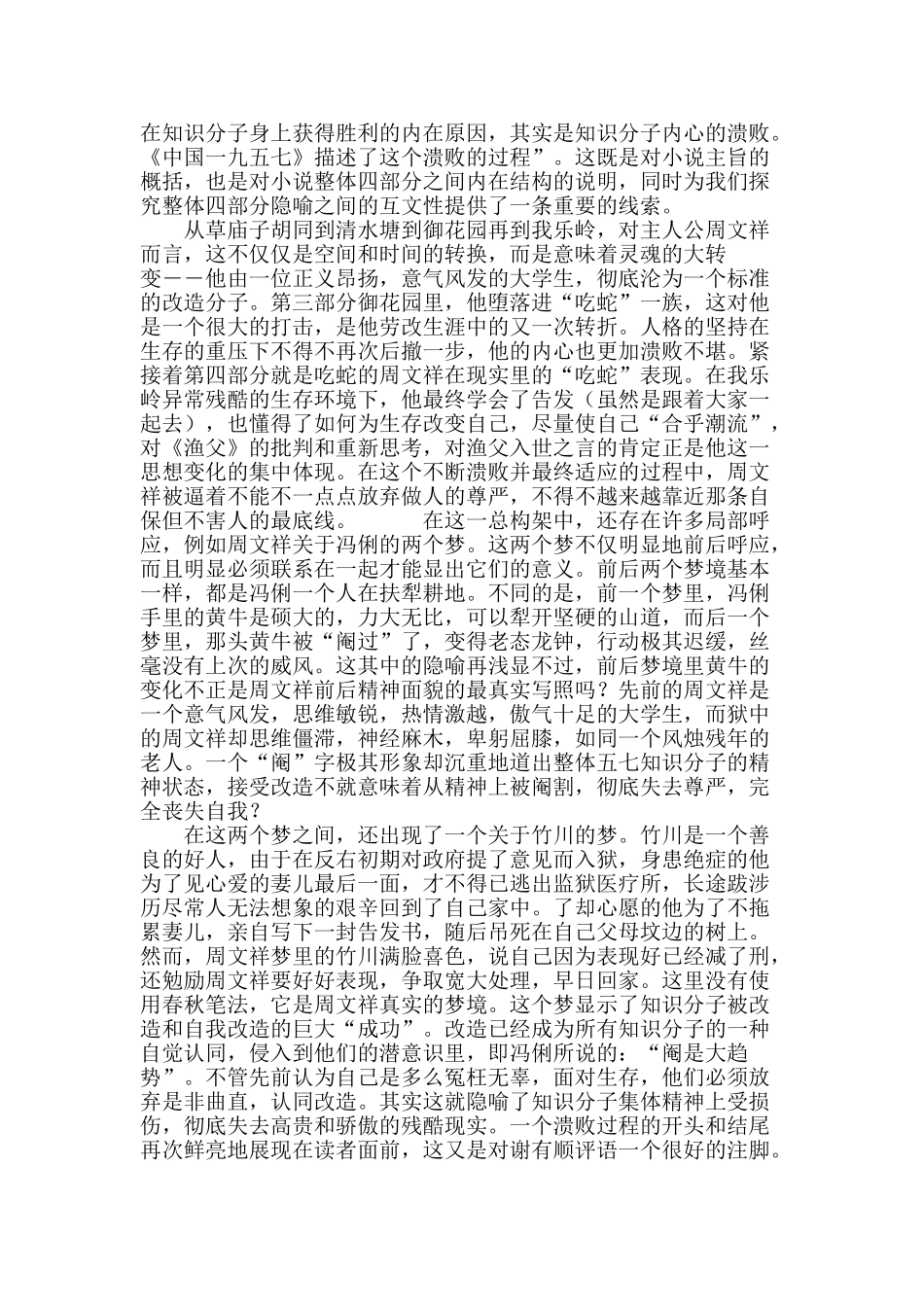超越修辞的隐喻超越修辞的隐喻 [摘要]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是近年来少有的关于反右题材的佳作,不仅表现在思想性上,更表现在叙事策略上。隐喻是小说所运用的最重要的叙事策略,它不仅丰富了小说的精神内涵,而且为小说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条内在的精神逻辑线索。通过对隐喻的多义性、互文性以及系统性的分析,深化阐释小说的内在结构和意义。 [关键词]隐喻 多义性 互文性 系统性 关于反右题材的文学创作,尤凤伟的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不论思想上还是技巧上,都堪称近年来难得的佳作。作者将自己对历史的敬畏,对大写“人”的敬畏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强烈的责任感一并融入到创作中,这是我们面对这部小说时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真切的沉痛之感的主要原因。 文学是人学,不是历史学。李丹梦的批判是没有道理的,尤凤伟并非意图“以文学的方式去复现、描述历史”,而是专注于再现历史背后的人,再现那段特别历史境遇中无数被埋葬了的人以及他们被严重扭曲了的人性。历史只是作品的时空,本就不是作者表现的重点,所谓“历史被偷梁换柱成了人性史”的批判也无法成立。作者选择以第一人称“我”来回忆那段历史,有着特别的意义:“我”正为了昭示一种自由精神的不灭和知识分子的不屈。“我”的回忆本身就是一种良知、一种责任的彰显,“我”的抒情与独白,也决不是文学为了拒绝历史的平凡所作的发嗲,而是显示出一种巨大的直面惨淡过去的勇气,恰恰是人性不屈的表现。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我”心中那一点残存的、微弱的精神终于从苦难中站起来,带着血和泪的记忆挣扎着醒过来,这不正是一种抗争的表现吗? 面对这个敏感度极高的创作题材,尤凤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驾驭能力和应对智慧,将这部充满血泪的人性史深刻地呈现在笔下。这不仅体现在“强制回忆”,“春秋笔法”的大事记,“我乐岭人物志”以及小说中的小说等这些叙事方式独具匠心地运用上,更着重体现在小说精彩的“隐喻”艺术上。 一、隐喻的多义性 隐喻的关键在于语境,犹如地基之于大厦。《中国一九五七》的精彩首先在于隐喻的多义性。以“吃蛇”为例。“吃蛇”是小说第三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隐喻。假设离开文本特定的语境,“吃蛇”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举动,而那场“吃蛇”的争议也只能相应地成为一场闹剧,那位龚和礼教授不过是一个迂腐不堪的学究,他那份“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我饿死也不会吃蛇的”的固执更是滑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