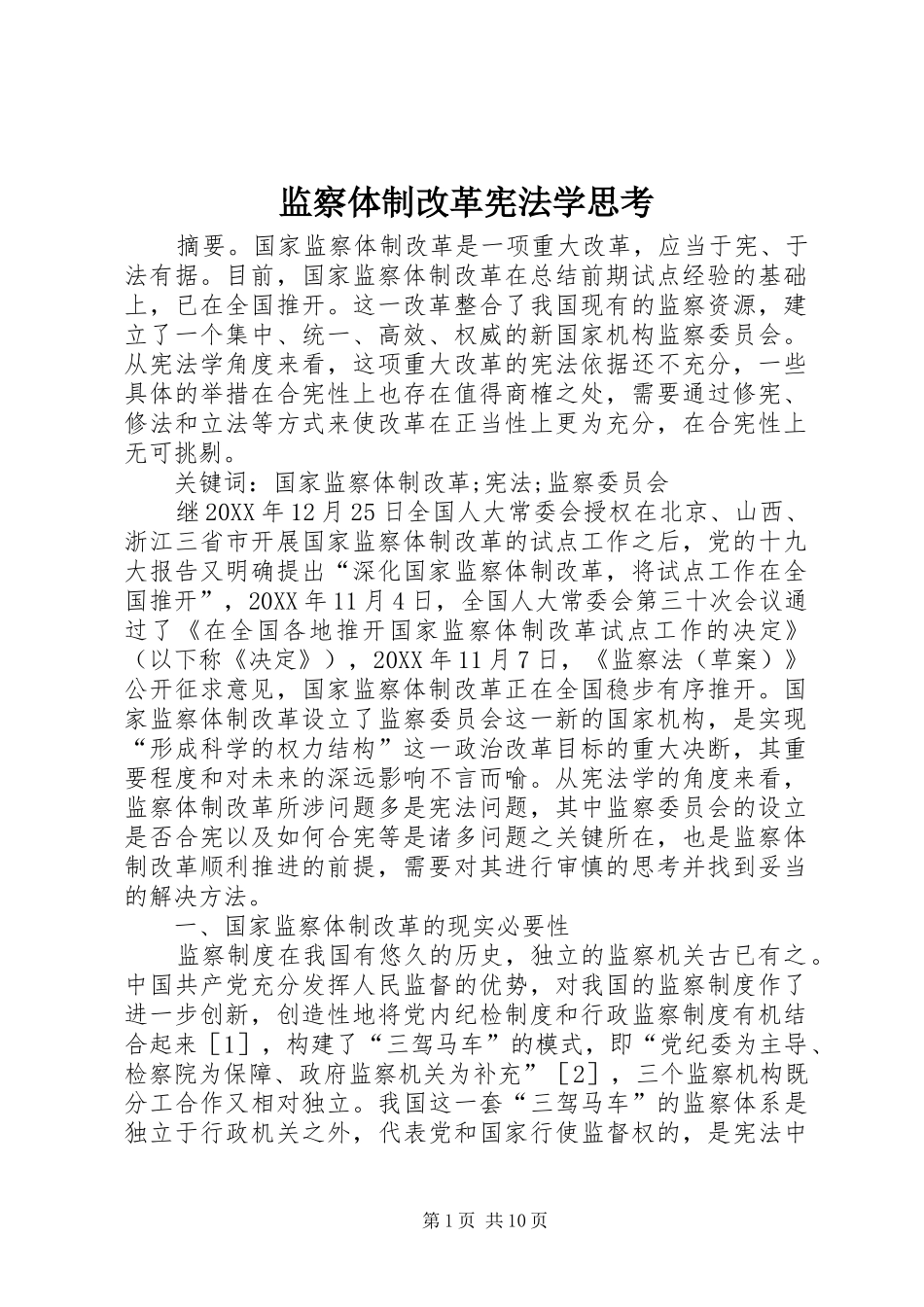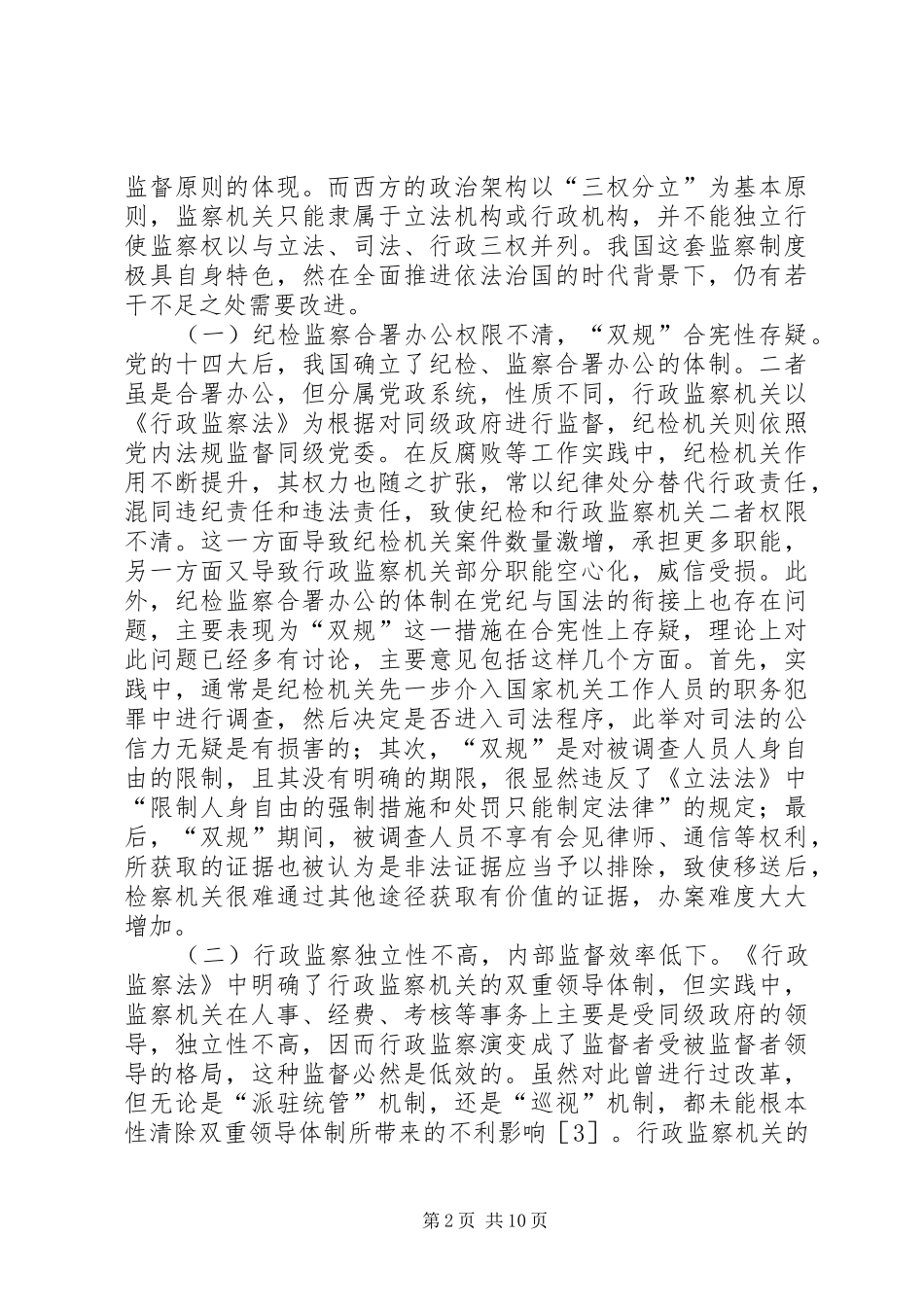监察体制改革宪法学思考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改革,应当于宪、于法有据。目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已在全国推开。这一改革整合了我国现有的监察资源,建立了一个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新国家机构监察委员会。从宪法学角度来看,这项重大改革的宪法依据还不充分,一些具体的举措在合宪性上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需要通过修宪、修法和立法等方式来使改革在正当性上更为充分,在合宪性上无可挑剔。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监察委员会继20XX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北京、山西、浙江三省市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20XX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称《决定》),20XX年11月7日,《监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全国稳步有序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设立了监察委员会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是实现“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这一政治改革目标的重大决断,其重要程度和对未来的深远影响不言而喻。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监察体制改革所涉问题多是宪法问题,其中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是否合宪以及如何合宪等是诸多问题之关键所在,也是监察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需要对其进行审慎的思考并找到妥当的解决方法。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现实必要性监察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独立的监察机关古已有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监督的优势,对我国的监察制度作了进一步创新,创造性地将党内纪检制度和行政监察制度有机结合起来[1],构建了“三驾马车”的模式,即“党纪委为主导、检察院为保障、政府监察机关为补充”[2],三个监察机构既分工合作又相对独立。我国这一套“三驾马车”的监察体系是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是宪法中第1页共10页监督原则的体现。而西方的政治架构以“三权分立”为基本原则,监察机关只能隶属于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并不能独立行使监察权以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我国这套监察制度极具自身特色,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仍有若干不足之处需要改进。(一)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权限不清,“双规”合宪性存疑。党的十四大后,我国确立了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体制。二者虽是合署办公,但分属党政系统,性质不同,行政监察机关以《行政监察法》为根据对同级政府进行监督,纪检机关则依照党内法规监督同级党委。在反腐败等工作实践中,纪检机关作用不断提升,其权力也随之扩张,常以纪律处分替代行政责任,混同违纪责任和违法责任,致使纪检和行政监察机关二者权限不清。这一方面导致纪检机关案件数量激增,承担更多职能,另一方面又导致行政监察机关部分职能空心化,威信受损。此外,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体制在党纪与国法的衔接上也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双规”这一措施在合宪性上存疑,理论上对此问题已经多有讨论,主要意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实践中,通常是纪检机关先一步介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中进行调查,然后决定是否进入司法程序,此举对司法的公信力无疑是有损害的;其次,“双规”是对被调查人员人身自由的限制,且其没有明确的期限,很显然违反了《立法法》中“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最后,“双规”期间,被调查人员不享有会见律师、通信等权利,所获取的证据也被认为是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致使移送后,检察机关很难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有价值的证据,办案难度大大增加。(二)行政监察独立性不高,内部监督效率低下。《行政监察法》中明确了行政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但实践中,监察机关在人事、经费、考核等事务上主要是受同级政府的领导,独立性不高,因而行政监察演变成了监督者受被监督者领导的格局,这种监督必然是低效的。虽然对此曾进行过改革,但无论是“派驻统管”机制,还是“巡视”机制,都未能根本性清除双重领导体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3]。行政监察机关的第2页共10页监察范围受制于其性质和职权,仅限于行政系统内...